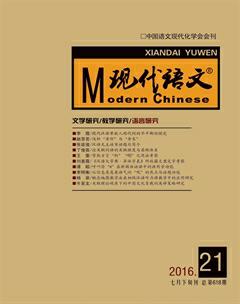《红楼梦》中大同方言补遗五则
摘 要:文章从《红楼梦》中选取了五则与大同方言相关的方言土语,对其从语言学角度予以阐释和标注,以求对书中校注不明甚至错误的地方予以更正。
关键词:红楼梦 大同方言 补遗
在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版《红楼梦》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与大同方言有关的语言表述。可惜的是,这些活泼生动的方言土语并不为人所知晓和发掘,文中有许多地方校注不明甚至错误。本文从中选取五则相关内容,对其从语言学的角度予以阐释,以期受教于方家,有益于文化。
一、“动”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391页):“凤姐儿道:‘……家里唱动戏,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
《红楼梦》第五十七回(791页):“宝钗道:‘惟有妈,说动话就拉上我们。”
上述两例中的“动”字该如何解释?对于前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红楼梦》第343页注释为“唱动戏——唱一次戏,在指不是轻易的、比较繁重的行动次数时常用‘动,音‘tòng”;对后者未作解释。“唱动戏”与“说动话”在语法层面是平行结构,作为助词出现的两处“动”字自然应该同义。“唱戏”或许是“不容易、比较繁重的行动”,但“说话”显然不是,因此老版的注释是错误的。新版为规避质疑一概不作注释,任凭读者猜测想象。其实,“动”字是插在动宾短语中间的一个助词,表示“……的时候”。在这种结构中,宾语和“动”字的位置可以互换:“唱动戏”与“说动话”也可以说成“唱戏动”与“说话动”。这种说法在大同方言中非常普遍,其中加了儿化韵作“动儿”的用法居多,例如:“过动儿年,就能吃上肉了。”“吃饭动儿,才能逮着他。”甚至民歌为表示情人间那种“相见时易别时难”的情愫也会唱道:“胡麻那个开花呀一片片个蓝,来动儿那个容易走动儿难……”查阅《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集的方言词汇,进一步印证了关于“动”的观点:①动了<助>的时候(用于动词或动宾词组之后)。②动咾<助>的时候(用在动词或动宾词组之后,表示动作未进行)。
二、“兴的”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578页):“尤氏笑道:‘你瞧他兴的这样儿!我劝你收着些儿好。太满了就泼出来了。”
人民文学版中此处校注为“兴的——喜欢得、高兴得。”但回到原文语境,事情是这样的:贾母做寿,怕凤姐儿太过劳累,就把花钱叫戏班的差事交给了尤氏。尤氏往凤姐房里商议怎么办生日,凤姐的回答却敷衍了事、怠理不理,这惹得尤氏有些不满,便问凤姐:“……出了钱不算,还要我来操心,你怎么谢我?”凤姐笑道:“你别扯臊,我又没叫你来,谢你什么!你怕操心?你这会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个就是了。”
显然,凤姐言外之意是告诉尤氏不必在她这里邀功请赏。作为一个女强人,脂粉队里的英雄,凤姐根本看不上也不稀罕尤氏这点小奉献小作为。凤姐这样直白却有力的当众回击使得尤氏颇为丢面子,但尤氏怎能示弱,她于是笑道:“你瞧他兴的这样儿!我劝……”
妯娌之间的你来我去,我们看得真切,但校注将“兴的”释作“喜欢得、高兴得”,却让人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语言的交锋,是尤氏不满的宣泄和回击,和“喜欢、高兴”并无什么关系。事实上,“兴的”结构平行于普通话中的“美的”“乐的”等,在这里是含有贬义的“的”字短语,指“人眼光高,对东西不珍惜、不节约、不稀罕、不爱护。”大同方言中仍保留着这个短语,例如:“这孩子兴的连肉都不吃。”“看把他兴的!这么好的姑娘都不要,我看他再去哪里找!”
三、“敁敠”
《红楼梦》第四十九回(656页):“凤姐儿冷眼敁敠岫烟心性为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温厚可疼的人。”
“敁敠”是个双声词(敁:丁兼切;敠:丁括切),在大同方言里是“称量、掂量、思量”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红楼梦》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1982年校注第1版、2008年校注第3版《红楼梦》均未对这个古旧而生僻的词作出解释,读者每每读到这里就不知所云。笔者以为,应该以现代汉语中的“掂掇”一词对其进行注释以便于阅读。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掂掇”词条下有三个义项:
①掂:你~~这块石头有多重。
②斟酌:你~着办吧。
③估计:我~着这么办能行。
四、“蝎蝎螫螫”
《红楼梦》第五十一回(694页):“晴雯忙回身进来,笑道:‘那里就唬死了他?偏你惯会这蝎蝎螫螫老婆汉像的!”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714页):“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
《红楼梦》第六十七回(931页):“且说赵姨娘因见宝钗送了贾环些东西,心中甚是喜欢……忽然想到宝钗系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卖个好儿呢。自己便蝎蝎螫螫的拿着东西,走至王夫人房中……”
“蝎蝎螫螫”中的“螫”字实为“蜇”字的误写,“螫”字中古为施只切、梗摄开口三等入声字,今现代汉语读为[t???51];而“蜇”字中古为陟列切、山摄开口三等入声字,今现代汉语读为[t?55]。蜇,螫也。“螫”字为“蜇”的书面用语,但二者的读音截然不同。根据方言读音,笔者认为“螫”字应该写作“蜇”。《红楼梦》中的俚语村言不胜枚举,独“蝎蝎蜇蜇”摇身变为书面语“蝎蝎螫螫”,这种说法令人难以信服。况且这个词出现于人物的交谈对话之中,实在让人心生疑窦:如果不是雪芹先生的笔误,那就是后人传抄的失误,这也可以理解——两个字字形确实很相似。
大同方言中不仅有“蝎蝎蜇蜇[?ia?30?ia?30t?a?30t?a?30]”,而且有“蝎蜇[?i?31t??31]”,前者应理解为后者的重叠演变式。首先,基于“蝎子蛰人”这个基本的生活认知以及主谓宾结构的整体凝固性,“蝎蜇”放在“的”字结构中成为“蝎蜇的”,转指“被蝎子蛰的人”,相当于大同话中“雷劈的、枪崩的”。那些“被雷劈、被枪崩的人”有坏的共性,“被蝎子蛰的人”就是疼。疼自然要叫嚷,叫嚷就是惊乍、张扬,稍作引申就是“夸大情形、小题大做、大惊小怪”的意思。“蝎蜇”一词在大同方言中使用非常普遍,例如:“她可蝎蜇呢,手上扎了个刺也要去医院做手术!”“蝎蜇啥呢!不就是只鞋板虫嘛?”经重叠演变,表性质的“蝎蜇”变为表情状的“蝎蝎蜇蜇”,性质形容词加以量化,可以说“她可蝎蜇呢”,但表情状的“蝎蝎蜇蜇”由于已经附带主观的情感认知,所以不能再添加“可、最、非常”一类的程度副词,于是表现为《红楼梦》当中做谓语和状语的用法。endprint
对于第一例,1982年校注本第1版《红楼梦》第715页注释为“蝎蝎螫螫老婆汉像——唯恐被蝎子螫了似的缩手缩脚胆小怕事,虽是汉子却婆婆妈妈的样子。”2008年校注本第3版将其更正为“蝎蝎螫螫老婆汉像——形容大惊小怪、为一点小事就咋呼起来。虽是汉子却婆婆妈妈过分小心。”相比1982年校注本,2008年校注本对“蝎蝎蜇蜇”作出了正确解释,但依然将“老婆汉像”释为“婆婆妈妈过分小心”。实际上,“老婆汉像”是紧接于“蝎蝎螫螫”之后的同义具象表述,同样指一惊一乍、小题大作的女性作风。“老婆汉像”就是晴雯揶揄宝玉像个女人一样过于“蝎蝎蜇蜇”。
五、“不/没当家花花的”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339页):“马道婆又道:‘还有一件,若是为父母尊亲长上的,多舍些不妨;若是像老祖宗如今为宝玉,若舍多了倒不好,还怕哥儿禁不起,倒折了福。也不当家花花的,要舍,大则七斤,小则五斤,也就是了。”
《红楼梦》第八十回(1134页):“王一帖笑道:‘没当家花花的,膏药从不拿进这屋里来的。知道哥儿今日必来,头三五天就拿香熏了又熏的。”
前一例中“不当家花花的”与后一例中“没当家花花的”非常相似,可以确定它们其实是一个短语、一个意思。关于后一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红楼梦》第1052页中同样意思的文字表述为:“王一帖笑道:‘不当家花拉的!膏药从不拿进屋里来的。知道二爷今日必来,三五日头里就拿香熏了。”可见,“没当家花花的”是后来红研所校注本对“不当家花拉的”的改动,当在文下注释中标明“没当家”亦作“不当家”“不当价”。这种改动可能出于统一表述或流畅行文的安排,但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殊不知这样一改反而弄巧成拙——使原本可以窥见方言身影的短语一下子变得不伦不类。
“不当家花花的”与“不当家花拉的”这两个短语的核心其实是“不当”一词,但这个“不当”并不是用来表示“不适合,不恰当”(处理~,用词~,~之处)的“不当”。这里的“不当”带有迷信或宗教色彩,表责备、忏悔、劝喻和承当不起之意。至于“家”“价”“花花”“花拉”这些字眼,一概认为是无实意的词尾,而非红研所校注本所述:“花花的”是词尾,“价”却是助词。
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场》:“不当价,如吴语云罪过。”这说明京都燕赵一带曾以“价”字作为“不当”一词无实意的词尾;而如今大同方言中表示“不应该,不应当”义用的四字词语仍是“不当拉花”(又:“不当花拉”“不当花花”),例如:“看那不当拉花的,半个馍馍跌在地上就不拾了。”这说明晋北雁云一带是以“拉花”“花拉”“花花”等双音节短语作为“不当”一词无实意的词尾。由此可以推断,受这两种方言的影响,“不当价”与“不当花花”一糅合截搭就形成了书中所言“不当家花花的”;“不当价”与“不当花拉”一糅合截搭就形成了书中所言“不当家花拉的”。
参考文献:
[1]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
[2]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赵元任著,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张宝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30038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