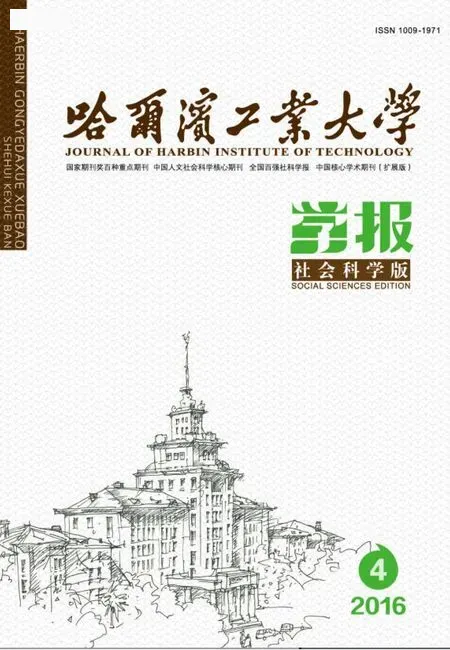农民工群体存在的微观基础:一个解释性的生活方式理论
徐法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农民工群体存在的微观基础:一个解释性的生活方式理论
徐法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一个以“打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农民工群体。虽然社会转型视角和社会运动视角下的研究将中国农民工视为一种暂时的过渡现象,但是中国农民工却存在了三十多年,而且其数量一直在增加。中国农民工群体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呢?生活方式理论可以对中国农民工群体长期存在的微观基础进行具体说明:首先,以各种打工动机为依据,农民工倾向于对打工生活持有接纳的态度;其次,农民工的动机和态度又是由他们的生存状态所形塑的。因此,农民工群体长期存在的微观基础是其生存条件和动机态度的“同构性”和“互构过程”及其产生的接纳态度。生活方式理论在微观层次上对中国农民工群体长期存在的解释,也说明了生活方式理论在描述和规范价值之外所具备的解释价值,从而扩展了生活方式理论的理论内涵和应用范围。
农民工;打工;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理论
一、背景、问题和观点
虽然各个国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点是,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产生了一个以“打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农民工群体[1][2]。虽然社会转型视角和社会运动视角下的学者都倾向于将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出现视为一种过渡现象[3][4][5][6],但是这个群体已经在中国存在了三十多年,而且其数量不断增加[7][8];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两亿七千三百九十五万[9]。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状态并不优越,甚至是非常恶劣。他们大都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建筑业、加工业和服务业工作;他们大都在没有劳动合同和劳动保障的条件下工作;他们的收入水平大都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他们往往都居住在拥挤的工厂宿舍、郊区违规建筑和老城区的旧住宅里;他们的孩子往往不能进入到水平较高的公立学校中学习;他们的消费行为往往与城市居民相隔离[10][11][12]。
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中国农民工群体为什么会长期存在而且不断增加呢?本文力图从生活方式理论出发在微观层面上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访谈资料显示,农民工具有多样化的打工动机,而且这些打工动机是他们进城打工的价值目标;在这些打工动机的基础上,农民工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打工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他们的打工动机和生活态度是由他们的生活条件所形塑的,另一方面,这些打工动机和生活态度又使得他们接受了这些生活条件。因此,农民工群体长期存在的微观基础是农民工生存条件和动机态度的“同构性”和“互构过程”及其产生的接纳态度。
二、文献评析
这一部分将首先对结构制度分析进行评述,然后将对农民工的微观研究进行评析,从而说明为下一部分的生活方式研究提供基础。
(一)结构制度分析及其不足
就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分析而言,由于中国的农民工主要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以及从不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结构分析者强调了城乡二元结构和地区不平衡发展结构的影响。首先,由于所有的农民工都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农民工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分化,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真正地得到解决;而且,这种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体现在基础设施、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13][14][15]。其次,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行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因此中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结构也被认为是中国农民工产生的结构背景[16][17]。而且受阿瑟·刘易斯等人的“二元部门模型”和移民研究的“推拉理论”的影响,这些学者也认为农民工现象是一种过渡现象,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供给的减少而消失[3][18][19]。
由于结构分析仅仅说明了中国农民工产生的结构可能性,却不能具体说明为什么其他国家面临同样的社会结构却没有出现农民工现象。制度分析则更加具体地说明了中国特殊的发展轨迹和制度设置,以解释中国农民工的产生和存在。其中一个主流范式就是“户口范式”[20][21]。在“户口范式”看来,中国农民工的产生源于对中国内部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但是中国农民工的长期存在是由于中国的户口制度还没有完全废除。但是,户口制度绝对不是一个本源性的社会制度,户籍制度本身是一个国家政策,因此必须放在国家工业化战略和国家政策体系中进行考察[20][22][23][24][25]。
与结构分析相比,制度分析更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农民工产生的原因,因此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大量的农民工,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产生。但是,和结构分析一样,制度分析也没有考察中国农民工自己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生存状态的,尤其是没有说明支持他们在恶劣条件下坚持在城市打工的动机和态度。
(二)农民工的动机态度分析及其缺陷
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对于理解他们的打工行为非常重要,因为打工动机是他们进城打工的内在动力。就农民工的打工动机而言,当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永久迁移意愿理论”和“家庭策略理论”的争论上。在“永久迁移意愿理论”看来,由于城市中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社会服务和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因此永久迁移到城市中是农民工的合理选择。而且调查数据也显示,很多农民工都具有永久迁移的意愿[26][27][28][29]。 但是,“永久迁移意愿理论”却遭到了“家庭策略理论”的挑战。这个理论视野下的研究指出很多农民工都只是将打工视为增加家庭收入和规避市场风险的一种策略,并试图用当前的制度安排来解释家庭策略动机的产生[30][31][32]。
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并不同于他们的生活态度,因为动机是一种动力,而态度涉及对当前生活方式的评价和行为取向。就农民工的态度而言,当前的研究探讨了他们对待农村生活的态度、对当前工作的态度、对劳动关系的态度、对城市生活状态的态度以及对社会环境的态度[33][34]。但是,这些针对他们的生存状态的各个侧面的态度是否能说明他们对待整体生存状态的态度呢?此外,现有研究也表明,不同的农民工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很多学者认为,农民工是能吃苦、勤劳做的农民工,他们往往接受了农民工的生活方式[35][36]。也有很多学者指出,随着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利益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他们往往会反对恶劣的工作条件、要求获得合法的收入[6][37][38][39]。
如果说,永久迁移意愿是农民工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那么为什么农民工并没有形成这种意愿呢?他们为什么形成了不同的动机呢?农民工群体内部是不是产生了态度上的分化?如果是,他们的态度分化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三、理论视角
从以上分析说明:(1)当前关于农民工现象的结构制度分析说明了中国农民工群体产生的结构可能性,也能够解释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但是,这种结构制度分析并没有阐释中国农民工对待他们的生存状态的动机态度;(2)当前关于农民工态度的研究虽然说明了农民工对工作条件、生活状态、劳动关系和社会环境的态度,但是并没有直接考察他们对待打工生活方式的态度及其形成机制。
面对这些问题,生活方式理论可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回答,因为这个理论能够将社会行动者的动机态度和生存状态联系起来。王雅林区分出了关于生活方式的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广义上的生活方式是指涵盖劳动生活、政治生活、物质消费生活、闲暇和精神文化生活、交往生活、宗教生活等多个领域;而狭义上的生活方式则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此外他还指出了另一种关于生活方式的理解:由个人情趣、爱好、嗜好、价值取向决定的生活行为的独特表现形式和特殊的生活习惯、风度和气质[40][41]。后来他也指出生活方式研究可以针对不同领域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研究等等[42]。也就是说,生活方式理论具有强大的应用潜力,可以应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可以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上进行研究,可以结合主观和微观进行考察,可以作为理论框架来使用,也可以用作指导社会实践的价值规范。
本文就力图对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方式进行考察,从而揭示这一群体存在的微观基础。布迪厄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批判客观结构主义和主观建构主义的基础上,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惯习”理论,力图找到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一致性。其中,惯习是被结构化的,是客观生活条件的产物;同时又是结构化的力量,能够通过产生客观结构存在的实践活动[43][44]。这种同时“被结构化的”(structured)又能够进行“结构化”(structuring)的惯习所产生的实践活动正是生活方式的本质。因此,布迪厄在《区隔》(Distinction)中写道:“生活方式的排列原则,或者说生活方式的形成(stylization of life)原则是距离现实世界的不同的客观和主观距离,尤其是物质条件的限制性和实践上的紧迫性。就像作为生活方式的一个维度的审美性情一样……我们不能把某种性情定义为客观的,因为所有性情都是被客观性所内化的,是由生存条件所构成的。”[45]由此可见,布迪厄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强调的是客观生存状态与主观动机态度之间的“同构性”;而且这种“同构性”和生活方式的形成也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微观基础。
基于以上所述的生活方式理论,本文力图说明农民工生存状态和动机态度的互构,从而说明农民工群体长期存在的微观基础。图1描述了本文所使用的生活方式理论框架。

图1 生活方式理论框架
四、研究方法
基于以下几个原因,本研究采纳了定性的研究方式:(1)本研究涉及社会行动者(农民工)的主观动机和态度,(2)本研究涉及农民工的客观生存状态和主观生活态度之间的关系机制,(3)本研究涉及过程研究,尤其是农民工的迁移过程、城市生活经历;而定性研究方法的优势也在于它能够在过程当中把握行动意义、社会过程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46][47][48]。
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采用了目的性抽样、半结构化访谈等具体的研究技术。在目的抽样中,本研究使用了最大差异抽样方法(Maxi⁃mum Variation Sampling),以囊括更多类型的农民工。这里所采用的抽样原则包括:第一,迁移距离上包括长距离(省际)、中距离(市际)和短距离(市内)迁移,因为迁移距离会影响农民工的迁移动机和生活状态;第二,目的城市上包括三个层次,包括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因为不同行政层次上的城市在迁移政策和福利制度上存在着差异,而且三个城市中农民工的迁移距离也存在差别;第三,农民工所从事的三个主要产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第四,农民工的家庭状况和年龄,包括未婚、已婚以及有未成年子女、年长(子女已经独立)。就抽样过程而言,为了取得访谈对象的信任并获得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本研究是从研究者的个人社会网络开始的;研究者的一些同学、亲戚、朋友成为了访谈对象。之后又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让访谈对象介绍更多的访谈对象。这样获得的访谈资料不仅更加丰富,而且更加真实。
在半结构化访谈中,本研究只是制作了一个访谈大纲;实际的访谈过程鼓励研究对象更多地描述他们的生活状态和表达他们的内心想法。访谈大纲的内容主要包括他们的打工经历和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动机态度两个方面。另外,为了了解生存状态和动机态度的互动过程,本研究特别注意访谈对象的打工经历。自2012年开始,到目前为止,本研究已经对43名农民工进行了访谈,包括了上述所有类型的农民工。
五、研究发现
本研究的总体发现是,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动机态度之间通过“互构过程”产生了“同构性”,即生存状态形塑着动机态度,而动机态度又让他们接纳了那种生存状态。
(一)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这里所说的生存状态主要是指农民工客观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包括产业特征、城市规模、职业特征、工作条件、居住条件、家庭生活、消费方式等方面的状况。其中,产业特征、职业特征、城市规模、家庭生活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条件、居住条件和消费结构。
就工作条件而言,产业特征是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言,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作条件最为恶劣,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户外工作,而且对体力的要求很高。但是那些技术性的工作人员,比如装修工的工作条件好很多,他们有自己的劳动工具,通常在室内工作,对体力的要求也不高。总体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的工作条件要好很多,比如工厂车间里有标准化的基础设施和工作时间规定。服务业的农民工,比如理发师要求技术高;为了吸引顾客工作环境也很舒适。
就工作稳定性而言,产业特征、家庭生活和职业特征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在建筑业内,农民工的工作稳定度很低;其中建筑公司组织的建筑工人往往可以在某个工地上工作两到三年,而那些个体性的装修工人则更加频繁地变换工作地点。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内,农民工的工作相对而言具有稳定性;除非出现危机情况(比如,因经济危机和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等),他们往往预期能够长期在某个企业工作。其次,一个影响工作稳定性的因素是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的变化。年轻的农民工,由于没有家庭生活的压力以及自己学习工作技能的需要,往往会经常变化工作;而那些有家庭责任的农民工,由于变换工作会给家庭带来很大影响,因此他们变换工作的时候往往非常谨慎。最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职业特征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稳性。那些在某个企业内获得了晋升而成为底层、中层、甚至高层管理者的农民工往往不会轻易地变换工作,因为在其他企业他们可能不会有这么好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待遇。
就居住方式而言,农民工主要有以下集中居住方式:工厂内的宿舍、企业租的宿舍、农民工自租的房子;而且,企业租的宿舍和农民工租的房子都是在老城区或者郊区,居住环境和内部设施都较差。首先,产业特征会影响居住方式,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往往居住在工地上临时搭建的集体宿舍内,这些宿舍内部的设施非常简陋,居住环境(工地)也是非常恶劣;而那些以装修和维修为业的农民工,往往是在郊区租用民房,生活环境相对较好,但是每天都要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制造业的工人往往居住在工厂内部的宿舍里,这里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相对较好,有基本的家具,而且可以去食堂吃饭;而服务业内的农民工一般居住在雇佣者就近租用的民房里,但是往往比较拥挤,在大城市里要四到六个人共居一室。此外,家庭生活也会影响居住方式,那些举家迁移,或者说两个以上的家庭成员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往往会单独租赁房屋居住;但是这样要看城市规模和产业特征,比如城市规模较大,工作地点又不一样的话,农民工的家庭也可能不会住在一起;此外,建筑公司和制造企业往往规定员工必须居住在指定的宿舍里。
就消费结构而言,建筑业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工作,但是总体上是和城市生活相分离的;他们很少去现代化的超市和购物场所,而且他们的生活领域主要限制在工作场所内部和周围;他们的收入往往都投入到农村生活的消费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内的农民工则更多地参与到城市生活中,尤其是在周末,他们会去市中心和现代购物场所去游玩,甚至是购买一些比较高档的消费品。不过,家庭生活是他们消费支出更为关键的影响因素;那些单身的年轻农民工往往将收入用于个人消费,而且也会购买一些较高档的消费品,比如衣服、手机等等;而那些结婚的、孩子上学的农民工,他们往往自己省吃俭用,然后把收入花费在家庭消费、子女教育上。
(二)生存状态与打工动机之间的“同构性”和“互构过程”及其逻辑
就动机而言,本研究的结论基本与之前的研究有些相似,即有些农民工具有永久迁移城市的意愿,而有些仅仅将打工视为增加家庭收入的策略。与之前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虽然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具有城市和乡村两种取向,但是在两种动机取向内部都呈现出了多样性。对于那些有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有些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另外一些农民工则已经有了明确的计划,有些想通过独立经营来实现永久迁移,有些则计划通过在企业内部的晋升来实现永久迁移;对于那些没有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有的是为了满足家庭经济需要而来打工的,而有些是为了学习技能和赢得个人尊重而出来打工的,还有的是为了提高家庭在农村社会网络和社区中的地位而出来打工的。
虽然某一个农民工可能会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机,但是这些动机本身却都是受到农民工生存状态影响的。首先,所有农民工的基本动机就是“赚钱”,这是农民工动机上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将“赚钱”放在第一位,有些是将学习技能放在第一位。那些年轻的、刚刚毕业的、单身农民工没有家庭责任的压力,他们在城市中工作的经历也使他们感到了工作技能的重要性,无论他们以后是要“养家糊口”,还是要定居城市,他们认为他们的“第一要务”是学习技能,提高自己。其次,那些家庭责任比较大的农民工,为了支持孩子的教育,或者为了给子女“盖房子,娶媳妇”,或者是为了给父母养老治病,或者为了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往往都把挣钱放在首位,以满足家庭在农村生活的需要;而且由于他们的家庭支出较大,对于他们来说迁移到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那些有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而言,这种意愿对于某些农民工来说仅仅是一种愿望;而有些农民工却制定了具体的方案。那些体会到城市生活优越性、但是还没有很好的职业发展的农民工逐渐有了永久迁移的意愿,但是他们认为近期还不可能实现这种愿望。这些人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里,而且这些农民工已经在城市中工作了一段时间,熟悉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也有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但是收入水平却不是很高,工作也不是特别稳定;很多人频繁地换工作也是为了找到更能够实现向城市迁移的工作。最后,有些农民工不但有了永久迁移的意愿,而且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在现有政策的框架下实现向城市的迁移。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时间较长,掌握了一些专业的技术而进入到了技术人员行列,或者已经晋升到了管理者阶层,工作比较稳定。即使收入不像建筑业农民工那么高,他们也感到自己的发展前途比较光明。一切使得他们未来的可预测性增加,因此发展出了具体的城市移民计划。
以上对打工动机的分析体现了生存状态与打工动机之间的“同构性”。一方面,理解农民工的打工行为和农民工群体的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考察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因为正是他们的打工动机支持着他们的行为和这个群体的存在。我们可以说,这个农民工群体的存在的主要表现是他们特有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而这种生存状态的再生产是有这个群体的动机所支撑的。另一方面,不同的动机是由他们的生存状态所形塑的,尤其是他们的产业特征、职业特征和家庭生活。也就是说,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这些动机都是由生存状态所构成的,也是他们生活在这种生存状态中的驱动力。
这种“同构性”不仅存在于生活在不同生存状态中的农民工中,而且存在于某一个农民工打工的不同阶段;也就是说,农民工会根据他们生存状态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打工动机;这就是生存状态和打工动机之间的“互构过程”的一个体现。首先,如果他们的家庭生活没有什么变化的话,随着农民工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成为技术人员,或者随着农民工管理技术的提高而成为管理人员,他们就会具有更为强烈的永久迁移意愿。另外,如果他们的工作条件没有变化,随着他们生命周期的变化,比如结婚、子女上学、父母生病等,农民工会降低他们的预期,转而更加注重他们的家庭责任。
这种“互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对“生活可能性”的计算。虽然农民工对当前关于向城市迁移的相关政策不甚了解,但是通过社会网络和榜样,他们也不同程度地知道了实现城市迁移的必要条件。他们会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迁移必要条件进行比较:如果他们感到的迁移可能性越高,他们的意愿也越强烈,也越可能发展出进行城市迁移的具体计划;相反,如果他们感到迁移的可能性很低,他们往往更加关注打工的本来目的,即承担家庭责任和农村消费。
(三)生存状态与生活态度之间的“同构性”和“互构过程”及其逻辑
第一,农民工对待当前工作的态度不同于他们对待打工生活的态度。不接纳当前工作的农民工却可能接受打工的生活方式;接纳当前工作的农民工也可能不接受打工生活。比如,有些在制造业工厂里工作的年轻人,总是感觉工厂里的工作氛围比较压抑,生活上的自由度不大,工作的环境不卫生,而且也没有什么前途,只能机械地进行劳作。也就是说,他们对当前的工作很不满意,具有比较强烈的更换工作的愿望,找一些技术性较高、工作环境较好、有前途的工作。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数量的下降以及法律保障的完善,农民工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可供选择。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很多农民工更换了多次工作,而且即使这些工作一个比一个好,但是他们仍然过着打工生活,仍然认为自己是打工者。与此对当前工作的态度类似,农民工对工作条件的态度、对居住条件的态度、对社会环境的态度、对农村生活的态度、对劳动关系的态度等等都与对打工生活方式的态度存在区别。
第二,就生活态度而言,农民工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打工生活方式,这尤其体现在他们的“打工者”的身份认同上。正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界定为“打工者”,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着打工行为,并在总体上维持着农民工群体的存在。所谓的“打工者”的身份认同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农村居民和城市客人。首先,农民工倾向于将他们自己界定为农村居民,因为他们在农村和城市中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基本权利和消费方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农村当中有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利、在农村中能够建盖自己的房屋、能够享受农村居民所有的社会福利、在农村中有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民工的部分或全部家庭成员都仍然生活在农村中。其次,在城市当中,他们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赚取低于城市居民的工资,即使工资较高他们的工作也不稳定,他们没有稳定的居所也买不起房子。这无疑强化了他们作为农村居民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发展出了“城市客人”的身份认同。即使那些工作更加稳定、职业前途更加光明、家庭成员也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在他们在城市中有资产(“房子”)之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家”在农村。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态度之间也存在着“同构性”。首先,我们可以发现生存状态对农民工生活态度的影响。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条件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打工态度;尤其是,农村和城市生活在生产方式、居住方式和基本权利之间的差别强化了他们“农村居民”、“城市客人”和“打工者”的身份认同。其次,这些态度也都促使农民工接纳了当前的打工生活方式,因此他们起码在一定时间内进行着打工的行为,生活着打工的生活状态,维持着打工的生活方式,构成着农民工群体的存在。
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态度之间也存在“互构过程”,即生存状态的变化会引起打工态度的变化,而这种态度的变化又会影响他们对打工生活状态的行为取向。首先,农民工对打工生活的接纳态度并不相同:有的接纳程度高,并准备长期在城市中打工;有的则想脱离打工的生活,认为打工生活不是长久之计。其次,农民工对打工生活的接纳程度会随着生存状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有时候他们的接纳程度高一些,有时候他们的接纳程度低一些。再次,无论他们的接纳程度是高还是低,大部分农民工都有理由接纳这种生存状态,从而维持这个群体的存在。
这种“互构过程”主要有两个过程:第一个是动机合理化过程,第二个是替代方案计算过程。首先,打工的动机会影响他们对打工生活的接纳程度:那些家庭责任大的、中年农民工,对打工生活的接纳程度较高,准备一直在城市中打工。所以,有些中年农民工在农忙时节还会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这些农民工存在于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虽然他们也想找一些收入更高的工作,但是他们总体上还是接受了打工的生活方式。而那些年轻的、单身的、家庭压力较小的农民工对打工生活的接纳程度较低。他们往往将打工作为一个跳板和手段,作为学习技术和发展社会网络的机会,但是他们的最终归宿可能还是打工生活。也就是说,他们的打工动机会为他们的生活态度提供一种合理化论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农民工充满着自豪感: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民工感觉他们为家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总体而言,农民工总有接纳打工生活的理由。其次,农民工对打工生活的接纳程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对替代方案的认知。这些替代方案包括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回到农村从事商业活动、在城市里开办自己的企业等等。也就是说,他们不再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而是要自己成为企业主。如果他们感觉自己有打工的替代方案,他们对打工的接纳程度就会较低;相反,如果他们感觉自己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就只能接受打工生活;而且他们对替代方案的认知越强烈,他们越不容易接纳打工生活方式。如果他们感到现在就有替代方案,那么他们现在对打工的接纳程度就很低;如果他们感到未来会有替代方案,那么他们虽然对当前打工接纳程度较高,但是以后会对打工的接纳程度较低。
总 结
在批判性地分析关于农民工的结构制度分析和动机态度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生活方式理论出发对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动机态度进行了考察,从而说明这个群体长期存在的微观基础。目的抽样和深度访谈的资料表明:(1)农民工群体的外在特征是他们不同于典型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生存状态,但是在这个群体内部,他们的产业特征、职业特征、工作城市的规模、家庭结构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条件、居住条件和消费结构;(2)虽然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呈现出农村和城市两种取向,但是两种取向都具有多样性;(3)他们的打工动机会与他们的生存状态存在着“同构性”,而且两者在过程中存在着以“生活可能性计算”为基础的“互构”关系;(4)在多样化的打工动机的基础上,农民工都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打工的生活方式;(5)农民工对待打工生活的态度与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存在着“同构性”,而且两者在过程中存在着以“动机合理化”和“替代方案计算”为基础的“互构”关系。这些发现对于在微观层次上解释中国农民工群体的长期存在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用生活方式理论来解释某一个社会群体长期存在的微观基础,因此本文中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理论,也可以是一个解释性理论。当前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生活方式的描述价值和规范价值。描述性生活方式分析体现为生活方式往往被视为受宏观结构制度和微观动机态度影响的一种现象,因此生活方式就常被用来描述和表示结构制度和动机态度的类型和变迁[49]。规范性生活方式分析体现为某种生活方式往往被视为美好社会的象征和指标,因此生活方式常被用来指导研究问题的提出和解释,以及被用作公共政策的指导方向和评估标准[50]。但是,描述性和规范性的生活方式研究并没有充分挖掘生活方式理论的内涵和应用范围。本文则通过对农民工群体生活方式的分析来解释这个群体数量的不断增加和长期存在,因此明确了生活方式理论的解释力,扩展了生活方式的理论内涵和应用范围。
[1]MENG X,CHRIS M.The Great Migration in China and Indonesia:Trends and Institutions[M]/MENG X,CHRIS M,LI S,TADJUDDIN A E.(Eds.)The Great Transformation: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and In⁃donesia.Northampton:Edward Elgar,2010:1-19.
[2]SMART J,REETA C T,MOSTAEM B.Labor Migration,Citizenship,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and India[M]/ BESHAROV D J,BAEHLER K.(Eds.)Chinese Social Policy in a Time of Transition.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60-179.
[3]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07,(4):4-12.
[4]CAI F,WANG M.A Counterfactual of Unlimited Surplus Labor in Rural China[J].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2008,16(1):51-65.
[5]CHAN C K.Strike and Changing Workplace Relations inA Chinese Global Factory[J].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2009,40(1):60-77.
[6]CHAN C K.The Challenge of Labor in China:Strikes and the Changing Labo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
[7]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J].广州大学学报,2010,(4):17-24.
[8]KNIGHT J,DENG Q,LI S.The Puzzle or Migrant Labor Shortage and Rural Labor Surplus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2(4):585-600.
[9]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 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 t20150429_797821.html,2015-04-29.
[10]WU J.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China’s Differential Citizenship: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M]/ WHYTE M K.(ed.)One Country,Two Societies:Rural -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55-81.
[11]WANF F.Organizing through Division and Exclusion:China’s Hukou System[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2]WANG F,ZUO X,RUAN D.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Socialism[J].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2002,36(2):520-545.
[13]WHYTE M K.The Paradoxes of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M]/WHYTE M K.(ed.)One Country,Two Societies: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1-25.
[14]LARUS E F.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M].Boulder,C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12.
[15]SECULAR T,YUE X,GUSTAFSSON B A,LI S.How Large Is China’s Rural-Urban Income Gap?[M]/ WHYTE M K.(ed.)One Country,Two Societies: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85-104.
[16]GALLAGHER M E.Contagious Capitalism: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17]LONG G,NG M K.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ra-Pro⁃vincial Disparities in Post-reform China: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J].Geoforum,2001,32:215-234.
[18]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9]蔡昉.后刘易斯拐点[J].中国改革,2011,(1):138-140.
[20]FAN C C.China on the Move:Migration,the State,and the Household[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8.
[21]CHAN K W,BUCKINGHAM W.Is China Abolishing the Hukou System?[J].The China Quarterly,2008,195:582-606.
[22]李强,唐壮.城市中的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J].社会学研究,2002,(6):13-25.
[23]ZHAN S.What Determines Migrant Workers’Life Cha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Hukou,Social Exclu⁃sion,and the Market[J].Modern China,2011,37 (3):243-285.
[24]徐法寅.中国农民工研究的四种范式及评析——作为移民、准市民、工人和劳动者的农民工[J].南方人口,2015,(2):31-42.
[25]CHAN K W.The Chinese Hukou System at 50[J].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9,50(2):197-221.
[26]HARE D.Push Versus Pull Factors in Migration Out⁃flows and Returns: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Status and Spell Duration Among China's Rural Population[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9,35(3):45-72.
[27]LI S.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Scenario,Chal⁃lenges and Public Policy[Z].Working Paper No.89,Policy Integration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Geneva,2008.
[28]叶鹏飞.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2011,31(2):153-69.
[29]熊波,石人炳.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发展,2009,15(2):20-26.
[30]FAN C C,WANG W W.The Household as Security:Strategie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M]/ SMITH R,NIELSEN I.(Eds.)Migr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China.New Jersey,NY:World Scientific,2008:205-243.
[31]ZHU Y.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Beyond the Hukou Reform [J].Habitat International,2007,31(1):65-76.
[32]LEE L,MENG X.Why Don’t More Chinese Migrate from the Countryside?[M]/MENG X,MANNING C. (Eds.)The Great Migration: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and Indonesia.Northampton,MA:Edward Elgar,2010:23-45.
[33]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4]LI P,LI W.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Attitud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J].China&World Econo⁃my,2007,15(4):1-16.
[35]LOYALK M.Eating Bitterness:Stori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China’s Great Urban Migration[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
[36]PUN N.Becoming Dagongmei: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J].The China Journal,1999,42:1-19.
[37]LEE C K.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38]HANNAN K.China:Migrant Workers Want Decent Work[J].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8,26(2):60-81.
[39]CHAN C K,PUN N.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J].The China Quarterly,2009,198:287-303.
[40]王雅林.生活方式研究评述[J].社会学研究,1995,(4):41-48.
[41]王雅林.生活方式研究的社会理论基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的再诠释[J].南京社会科学,2006,(9):8-14.
[42]王雅林.生活方式研究的现时代意义:生活方式研究在我国开展30年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学评论,2013,(1):22-35.
[43]BOURDIEU P,WACQUANT L J D.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2.
[44]BOURDIEU P.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45]BOURDIEU P.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376.
[46]罗伯特·殷.案例研究:涉及与方法[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47]MAXWELL J A.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An Inter⁃active Approach[M].Thousand Oak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2005.
[48]MERRIAM S,ASSOCIATES.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ractice:Examples for Discussion and Analysis[M]. San Francisco,California:Jossey-Bass,2002.
[49]麦嘉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50]王雅林.生活范畴及其社会建构的意义[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12.
The Micro-Mechanism of the Long-Term Existence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Lifestyle Theory
XU Fa⁃y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ntries,in the past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ve produced a group of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characterized by their dagong lifes⁃tyle.Thoug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and the social movement perspective consider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s a transient phenomenon,this group of people has exi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nd its number has been increasing continuously.Lifestyle theory can explain the long-term existence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t the micro level.First,based on their motivations,Chinese migrant workers tend to accept the dagong lifestyle.Second,Chinese migrant workers'motiva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dagong lifestyle are shaped by their living conditions.Therefore,the lifestyle theory indicates that the mi⁃cro-mechanism of the long-term existence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is the mutual constitution between their motivations and attitudes on the one hand,and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on the other.Finally,the explanation of the long-term existence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lso illustrat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lifestyle theo⁃ry,and thus extends the theoretical content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 of the lifestyle theory.
Chinese migrant workers;Dagong;lifestyle;lifestyle theory.
C913
A
1009-1971(2016)04-0055-09
[责任编辑:唐魁玉]
2016-04-12
徐法寅(1982—),男,山东聊城人,助理研究员,从事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