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的通透和温暖
王晓莉
看杰罗姆的《闲人痴想录》,我们常会发出一种会心之笑。这笑是突然的,甚至可说是毫无防备地就来到我们的脸上、心里—这很是难得。你因此对这笑也就更为珍惜了—因为,当流连于这世上的浩繁卷帙里时,我们常感到,令我们沉郁的书多,令我们凝思的书多,甚至令我们长夜暗哭的书也多,而那令我们开心、真正为之一展欢颜的书,却少之又少。
《闲人痴想录》里,却处处可捡拾这样的喜悦。“一顿美餐使男人温情的一面袒露无遗。在腹中美食的温和影响下,阴郁乖僻的人会变得兴高采烈,喋喋不休;迂腐古板的家伙,一天的其他时间里好像只靠醋和泻盐活着,饱餐一顿之后,他们皱纹密布的脸上才会荡漾出微笑。他们还轻轻拍着小孩们的脑袋,含糊其辞地表示要给他们六便士。”—杰罗姆用他这样特有的幽默让读者眉飞色舞起来。我们读其书,就是与一个通身洋溢着幽默因子的家伙对坐,他有点铁成金的本事。言谈所到之处,他不让你笑不算完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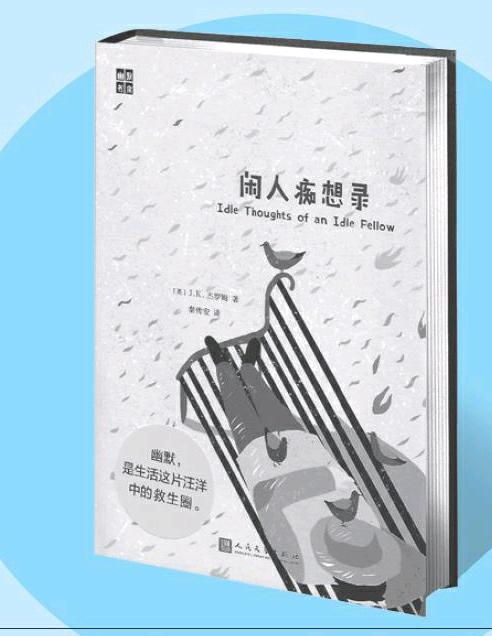
像我这样喜爱《闲人痴想录》的读者,隔着遥远的一百年,不免会要设想作者杰罗姆是怎样一种人。无疑,他绝非晨起之后穿着华丽的睡衣站在临窗处对着下面的街景指点一二的贵族,他也一定不是戴了夹鼻眼镜幽闭室内独自面向书墙的那类写作者,他是—还是他自己的话来得最真实:“我恐怕更像个爱尔兰佬,看到人头攒动,就忍不住吩咐小女儿去打听打听:那儿是否在打架,—‘如果真是在打架的话,老爸倒很愿意去凑个热闹。”
哈,原来是个爱“凑个热闹”的人。
正是这喜欢“凑个热闹”,使杰罗姆成为人世“观察家”,他不带显微镜或放大镜,却对世态人情种种都有着精细的观察。他几乎无所不写:衣食、吃喝、猫猫狗狗,还有出租房间里带不带家具,这些极为具体、俗世的事情,杰罗姆简直是手到擒来,涉笔成趣;而对于羞涩、忧郁、虚荣这些人性的种种幽隐之处,杰罗姆也是掘地三尺,洞烛分明。
我热爱的杰罗姆的品质之一,在于通透。杰罗姆的文字总是透露出一种最纯正的趣味。说它“纯正”,是因为它的来源非常普遍,普遍到广大,普遍到可以被所有人忽视却不成为罪过。它正是来源于:常识。杰罗姆注重常识,不吝笔墨,翻看《闲人痴想录》,我们常会觉得某段、某句话似曾相识,甚至会想:咦,怎么像我说过的,怎么我也这么想过?这就是常识的魅力。此时我们反倒觉得杰罗姆的常识的可贵了。这“常识”使杰罗姆通透如苏州园林里常见的那种“漏窗”,从甲地可望见隔墙的乙地,从乙地又可望见隔墙的丙地……
自然,历来的文人中并不乏见识“通透”之人。但我以为,世事通透之后,人也好比站立于危崖边,只有两条路可走了。一是指向了广大的虚无,卡夫卡、佩索阿,都是这一类翘楚人物,他们越走越远,世人远远瞻望到的是他们清冷而永恒的背影;而另一条路,却是如杰罗姆般复返喧嚷尘世,让市声作为他写作的背景音。尽管窗外熙来攘往,他内心却是相当的清明—他毕竟是从“虚无”的危崖边走过一遭的。正如我们于《积极生活》和《虚荣》里所看见的,杰罗姆无疑是彻底地看清了人性虚荣、野心勃勃的弱点,但他仍然肯定了这恰恰是人类生活向前发展的某种最强大的动力,因而他不无幽默地鼓励人们要“将虚荣进行到底”。
这类通透是温暖的,听得见隐约人声,也有蒙尘的光芒。因而是更与我们可亲的。亲到你不知不觉竟将他当作了邻居大叔,或者堂表兄弟。这倒不是读者如我的一厢情愿—你去看看道尽无钱之人生活困窘之态的《口袋空空》一文就知道了。在《口袋空空》的结尾,杰罗姆大倒苦水之后,调皮地开口向读者借钱,并且留下了自己的地址—一个与人世多么无忌、无隔阂的温暖的地址啊。
假如说快乐、有趣味、积极生活这些品质是处于人生的高音部的话,那么,忧郁、伤感、悲哀等种种情绪与思想,则于人生的低音部中常常可见可感—事实上,这低音部,正是前面高音部的巨大背景,二者且时常相伴相生。对此,杰罗姆为我们呈现了他的另一类通透认识。在文字里,他总是把“忧郁”“懊恼”充满钟爱地称为“女神”。在《忧郁的乐趣》里,他说:“……世界属于忧郁女神。她是一位沉思的、眼睛深陷的少女,她不喜欢白日耀眼的阳光。”又说:“暗幕四垂,世界不再仅仅是个肮脏的工场,也是一座庄严的神殿。”是啊,对生死无常产生的忧郁,以及对时光汩汩流逝永不再来而生的悲伤,有时就像净化水,洗去种种庸俗无聊、争执吵闹,它虽然会使面包、奶酪,哦,甚至还有接吻,使这一切都变得渺小琐碎,但是,它也会使人生呈现出一种“庄严的夜晚”式的景象。在那样的夜,我们总是默默无语,望向深不可测的苍穹,心底会涌起天地同在、古今同一的情绪。那一刻,我们将自己完全地交付给了莽莽苍苍的天地自然,我们终于变成了“无我”。
与他惯常所用的插科打诨、幽默生趣的方式相反,杰罗姆以一种冷峻的低调子如此告诉我们:这就是悲伤的重大、不可忽视的意义。当认识到此,我们—作为“人”,我们庄严与神圣的一面显现出来,我们人生的分量正是由此增加增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