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知者”伍棠棣
文_储朝晖 编辑_周春伦
教育“行知者”伍棠棣
文_储朝晖 编辑_周春伦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长,《教育史研究》副主编。著有《中国教育再造》《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教育改革行知录》《多维视野中的生活教育》《中国教育六十年纪事与启思》(上下册)《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等等。)
和伍棠棣先生同时代的人,知道他的大概并不算多,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他和李伯黍、吴福元先生合编的《心理学》教材。伍棠棣先生是我国较早的一批心理学专家之一。
除去这一身份,他将毕生大部分精力投注在教育教学研究上,在几乎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26年如一日地扎根在北京景山学校,系统听课,深度参与小学语文实验教材编写工作,提出了不少长远育人的前瞻性思考。
伍棠棣先生一生为人朴素、平易,其严谨求实、行知结合的研究态度,令人感佩。这样一位教育者,看似走在人群中央,却被时代洪流置于边缘,际遇让人唏嘘。
2016年6月,即是伍棠棣先生逝世一周年,以此纪念。
著名心理学专家伍棠棣先生于2015年6月16日在北京去世。回想第一次见到伍老师,他如此平易近人,专门从自家居室走约500米到大院门口接我,如果不是事前就知道这就是要见面的伍老师,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通晓英语、俄语、德语,翻译出版过《普通心理学》《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和自然基础》,主编出版过《关于建立我国语文教学心理学问题》《苏联教育心理学简史》等著作的心理学专家。在对伍先生的仙逝深感悲痛的时候,不能不回想他在中国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一本影响广泛的教材
1980年后,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不少人都学习过伍棠棣、李伯黍和吴福元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2月首次出版的高等师范院校公共必修课《心理学》教材。
本人1981年入学后所学的心理学教材就是这本,这也是我接触的第一本较为简明而又系统的入门教科书。当时,在图书馆所能借到的是几本苏联翻译过来的书,或许由于翻译水平不高,或许原著就不是高质量的作品,看了总有些隔膜,或是囫囵吞枣,看伍老师的《心理学》就感到浅近亲切。当时,学校阅览室几乎就看不到专业的心理学期刊,我只好自己抠着零花钱订了《大众心理学》和《心理学报》,一本比较通俗,一本比较学术,上面的文章较多的是讨论专题,伍老师的《心理学》是读这些期刊的很好铺垫。
据该书前言介绍,它是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学院心理学教研室和上海师范学院心理学教研组负责组织,有哈尔滨师范学院、吉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人员参加编写的中国第一部高校公共心理学教材,主要供高等学校学生学习心理学公共必修课时使用。这本教材初版以后,受到使用者的好评,截至2002年,累计印刷24次,印数达120万余册。
由于该书是心理学科在文化大革命后从多年被批判的“伪科学”刚刚恢复名誉的时候编写的,也是高师院校心理学复课后最先编出的一本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有开创之功。编写这本《心理学》本身也是一次思想解放,使长期停业、改行的高师院校心理学教师和非教育、心理专业的学生都获得很多帮助,该书的编写体例为此后各科教材所借鉴。
该书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由于编者对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很熟悉,全书结构简明,能深入浅出地说清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每章后附有练习题,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此后,不少人聆听过伍老师的课、报告,不少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还得到过他亲切的关爱和指导。伍棠棣,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里学习心理学的人首先会联想到的一个人名。

伍棠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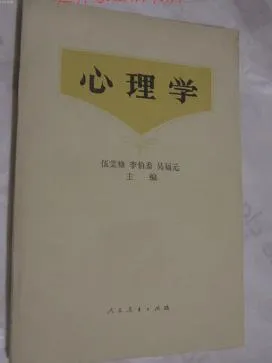
颠沛造次必于是
伍棠棣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平乐县安良村。对他的童少年生活,外人知之甚少,儿女们也说很少和他谈起,仅知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心理教研室年轻有为的心理学专家了,曾以专家的身份和毛泽东等人聚会并合影。
现在能找到有关伍老师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是1941年初,伍棠棣在桂林《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面发表诗作《午夜》。桂林《大公报》原本就是抗战的产物,是抗战中从外地迁入桂林,伍棠棣在抗日救亡最艰难危急的日子里怀抱理想,后参加华南分局土地改革工作队。
1951年,伍棠棣从土改工作队回广州中山大学工作时,得悉清华大学巴普罗夫学说研究班招生的消息,伍棠棣在未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汇报的情况下就急忙赶来北京报考,由此落下未得学校领导同意而面临严重处分的困局,不得不“非常后悔、痛心,认真写了检讨寄给学校”。“学校对事情做了调查和核实,认为检讨是真诚的,认识也比较好,决定此事不再立案处理”,并复信希望伍棠棣吸取教训,加强组织纪律性的修养和锻炼,争取新的进步。
受这一事件的影响,伍棠棣中断了与中山大学的缘分,于1951年到北师大工作。在北师大期间,伍棠棣谨记前车之鉴,小心翼翼做人。
1955年他服从组织安排由北京师范大学调往正在筹建的教育行政学院任心理教研室主任,1960年因教育行政学院停办调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
“文革”开始后,伍棠棣先后到北京广安门机床厂钳工学徒一年的劳动锻炼,在心理学多年被批判的学术逆境中,伍棠棣又与教育部职员一起下放到凤阳殷涧大青山“五七干校”忍受煎熬。后经五七干校下放到他的原籍广西,“文革”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1982年回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虽已超过60岁,研究的志趣和热情却不减。

伍棠棣给接受培训的教师讲课
解放后的释放
1986—1987年,伍棠棣和胡克英一起被派参加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小学教育改革研究班的组建工作,分别主持心理学课和教育学课的讲授,指导学员的课题研究,共同主编《小学教育改革研究丛书》。这对两位老师来说都是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大好机会,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付出的辛劳是巨大的,收获也是丰硕的。在一年的时间里,两人都很少离开过研究班在昌平的校园。在教学中,两位从1951年在北师大就开始一直共事30多年的老朋友相互沟通,交流在心理学与教育学这两门课的教学改革问题上的不同理解,鼓励学员去研讨。他们同学员普遍建立了亲密的挚友情谊。
从现在留下的一张伍老师讲课照片上,可以看到他用娟秀字体板书的提纲:“一、单一的因果链与多元的因果网络;二、结果、过程与反馈;三、“双基”教学与创造能力的培养。”从内容上似乎看不出是多少年以前的讲课提纲,因为所讲的问题至今不落后。
在心理学课讲授中,伍棠棣着重触及的几个问题是:1、主体间性。从心理学方面看,一般来说,主体就是有意识有语言有目的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指导的主体,两方以教材为中介,进行双边活动,主动地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在教学活动中,应该把主体与主体之间这种特性运用好、发挥好、发展好。可是多年来,教育理论界流行一种提法,说“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把学生一方与教师一方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学生是主体,教师不能是主体,似乎教师只能是起些指导作用的“机器人”。这显然是不确切的,甚至是有害的。2、双归类:在教学活动中不仅要注意指导学生学习进行逻辑归类,还要注意指导他们进行情感归类。这方面伍棠棣在多年前曾发表专文讨论过,这问题很复杂,他希望学员能重视在这方面创造出新的经验来。3、三位一体的协同作用:在教学活动中常常从单方面去注意情感、认知、动机的问题,这是不够的,还应该重视它们的协同作用。总结班级工作的实际经验,看到在班级集体的影响下,学生道德品质形成中情感、认知、行动意志的协同作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持之以恒。”应该把“群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结合起来,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上一步一步扎实地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推向前进。
伍棠棣和胡克英两人合作的成果——由胡克英、伍棠棣主编的《给小学校长工作的建议》《小学管理改革的研究》《小学体育卫生保健》三本著作1988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伍老师还经常回复各地老师慕名写来的求教信,《湖南教育》1986年第4期就发表了这样一封信,伍老师在信中谈到了开展语文教学心理学研究的意义,并对怎样进行这种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还透露了一些小学教育研究、教改实验的信息。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湖南语文界同志们的拳拳情愫,体现了一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虚怀若谷的襟怀。
2006年后,我几次到伍老师家里。落座后,伍老师依然像做讲座一样,滔滔不绝地讲教育上的问题、心理学上的问题,讲过去教育怎样蛮干而留下后果,讲当时树起来的所谓的教育典型的真实情况,还讲了一些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政绩,硬拉包括他在内的教育专家为他们所谓的教育经验背书,也讲些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巧妙应对,以保住自己的学人人格,不欺骗老百姓,尽可能让教育少受损失。
扎根一线做研究
伍棠棣一生的经历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长期扎根教学一线做研究。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伍老师就到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小的一年级跟班系统听课三年,在这个过程中,他深深体会到研究与教学结合的重要性。他说了一个表明这种重要性的故事——吴树英老师的两个馒头。
吴老师发现班上有的学生上课时坐立不安,调查后发现,有些孩子时常将买早点的几分钱弄丢,只好饿着肚皮来上学。于是此后,她每天早上都要带两个馒头来放在教室前面,告诉学生谁没吃早饭的可以拿着吃。伍棠棣老师得知此事后就问吴树英老师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吴老师反问伍老师:“这不是您教给我的么?您教我们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学生饿着肚子还能有听课学习的动机吗?”伍老师由此进一步意识到教育研究与一线教学相结合的重要性,也对吴老师如此以爱心和行动遵循教育规律产生由衷的敬意。
1981年以后的20多年里,伍老师一直在北京景山学校长期蹲点,系统听课,参加学校语文教学改革实验研究活动和实验教材第四、五代的具体编写工作及课堂教学的研究、总结工作,在教材研讨会上多次作报告。周淑溪老师回忆:“1982年伍老师到我校听课,听马淑珍老师的课最多,几乎堂堂不落,很快就进入到教材组,参加教材组的活动。他德高望重,对景山的语文教改实验事业26年如一日。”

伍棠棣修改储朝晖文稿手迹
从此他研究语文教学心理问题,先后对五年制小学语文实验课本进行过五次大的修改。伍老师一直是该教材的顾问。其中,前四代教材,伍老师既是编写组成员又负责审稿。教材组的老师们都说:“尤其是三、四、五套教材,伍老师费了不少心。”
当我从伍老师处拿到这些教材翻阅时,看到其中一些书已陈旧、破烂,中间夹了不少读书卡片和纸条,留下不少他对目录、文字、图案、标点的修改意见,圈圈点点,勾勾画画,铅笔、钢笔、圆珠笔的笔迹都有,说明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多次反复琢磨。其中,第四代教材的第七册《赵州桥》一文,修改批阅的文字与课本原文相互镶嵌,字数竟相差无几。在每一套书的生字表中,伍老师对前后重复的也做出标注。无怪乎景山学校的师生们对他的评价是:“1981年以来,他对北京景山学校语文教材的编写、教学改革实验以及教师水平的提高给予了有效的指导,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景山学校的语文教改实验效果好,收获也大。但伍老师自己却认为随着实验一代一代的发展,需要改正、提高、完善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他认为需要减轻学生负担,必须重新设计降低要求的作业,进一步完善实验教材,在总结过去几代实验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订出新一轮的实验方案,选择一些学校作为实验点。
1993年景山学校迁至新址,教材组也在这次搬迁中撤消了,刘曼华老师感到这对伍老师感情上有较大的伤害。八年之后,学校恢复教材组,大家又把伍老师请回来了,伍老师不仅没有任何怨言,令大家感到震惊的是,他仍然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从背后看他走路的步伐,哪像是八十岁的老人,宛如一个青年人!
2006年我到景山学校语文教材组了解伍老师的情况时,刘曼华老师指着一张办公桌对我说:“您就坐伍老师坐的桌子吧!”周淑溪老师伸手接过我的包放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说:“这也是伍老师经常放包的地方。”长期做实地调查的经验使我从这简单的话语中悟出伍老师与景山学校的关系之深刻与密切,无怪乎刘曼华老师用“很深的情结”来形容。
“既教文,又教人”
与一些人做研究将眼睛盯在文字成果发表上不同,伍老师将眼睛盯在学生的成长上,从孩子的长远发展着眼,研究要有利于、服务于学生的成长。他常对年轻教师说:要天天跟孩子接触,先跟孩子大量接触,这样研究问题才不会只是从上面看下来,然后才能做研究、编教材。
刘长明老师深切体会到伍老师的学识是渊博的,他常常是站在一个理论高度,从较深的层面、从别人没有想到的角度分析问题和发表意见。刘老师讲了这样一件事:“在讨论十册选文时,大家对陈淼的《滑冰》一文是否入选意见不一。这时老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细致地分析了课文内容,品味了词句,最后十分明确地提出:‘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意境很高,入选课本对学生会产生极大的教育作用,会教学生如何做人,做一个虚心向别人学习的人!’一席话,使我们眼前豁然亮了。”不局限于文章分析文章,而从培养人的角度,从关注孩子发展的角度分析文章,使教材组的老师们开了眼界。
以学生成长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还体现在教材编辑的过程中。1999年起,教材组在编写教材的同时搞了一个实验班,在这个班里用这套教材教学,看学生怎么学,教师有什么反应。在教材进行一线实验时,年轻老师做课,伍老师无论风霜雨雪都要亲自赶来参加。虽然尽可能挤出一切时间到课堂,但他自己还经常说起没有深入课堂是一个遗憾。他特别爱孩子,见到孩子的作业就如获至宝,拿到手后就急不可耐地看,然后分析、发表意见。八十多岁还经常和老师们说:“你们把学生写的作文、日记拿给我看看。”黄岚老师将一些三年级学生的习作交给伍老师,伍老师不仅仔细地阅读过每一篇,还为每一篇写了深入、细致、充满人情味的评语,然后发还给学生;叶晓静老师将一、二年级的写话作业拿给伍老师,过了一段时间,伍老师将每一篇都以与孩子对话的方式写了批语,孩子们能与伍老师在作业中“对话”感到很兴奋,不少家长得知后也极为感动。
伍老师瞄准学生的成长并非纯粹出于情感,而是有其理论基础的,他对教材组的人说,教材一定要将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起来,集中识字、名篇阅读是伍老师参与景山教材编写提出的两大举措,当时很多人反对,认为小孩子怎么能读懂名篇,甚至有人上纲上线说这是复古,伍老师坚持认为孩子能否读懂名篇的关键是教师。他主张:第一,语文教学要既教文,又教人,要注重语文的熏陶感染功能,要注重选文的文品和人品;第二,要重视文章的意境;第三,要重视孩子的接受程度,依据其最近发展区安排教学内容。这三点成为景山教材的灵魂,这一灵魂又是安根在孩子的成长与发展上。

伍棠棣在小学语文景山教材实验研讨会上作报告
“可爱的小老头”
景山学校语文教材组是一个团队,伍老师是这个团队中的长者,各位老师都将伍老师当作老师,却不把他当“教授”。宋以平老师说:“伍老师虽然年岁比我们大那么多,但他对小辈特别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年龄的阻隔,老有童心,与学生之间没有距离感。”很多人都记得,1982年伍老师刚到景山学校时,骑着自行车,穿着黄军裤,自己带饭盒,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不认识的人还以为他是学校门卫。
在这个团队里,大家有什么说什么,有时为了某一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在生活、思想上大家打成一片。叶晓静老师亲切地称伍老师是“可爱的小老头”。
伍老师非常关注团队和教师的成长,他常说教师是教材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一定要多读书,教师不能光教,一定要学习、做研究、提高专业素养。为使这些落到实处,伍老师对各位老师实施“条子指导术”。发现什么问题,就给那位老师写个小纸条,如语感、选材、体例……从大问题到极为细小具体的问题,他都写在条子里送给各位老师。他发现好的文章和资料,就会自己掏腰包到复印店复印后给大家每人送一份,当各位老师看到他复印的钱钟书的《通感》时,发现不仅有原文,还有伍老师在原文边上做的密密麻麻的批注,说明这并非他随意推荐给大家的,而是经过认真阅读,这不是任何一位教授都可以做得到的。
在这个团队里,照理说应该年轻人关照他,而每次见面他总是先说出关照年轻人的话。1985年周淑溪老师的脚骨折,教材组就将会议安排在周老师的家中,伍老师也骑着自行车赶了很远的路去了。遇到什么问题,他还骑车到周老师家里和她分析、解答。周老师为此感到过意不去。
伍老师是团队的顾问,对团队的要求很严格,1985年教材编写组经过五年的实验,写了一百余篇文章,大家均认为材料不错,准备出书,但伍老师认为理论上没有提升,最后还是没有出书。
虽然伍老师在这个团队中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甚至没有任何名义上的头衔,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这些。但他是大家公认的智者、长者,他给予大家知识、智慧、情感、意志的力量与方向。刘曼华老师在这个团队中与伍老师共事时间最长,她说伍老师是这个团队的专家、老师、同志、战友、兄长。
与伍老师相处过的人无不深深钦佩他对教育研究事业的执着,他经常告诉年轻教师自己年轻时是如何度过的,“不追求名和利,要真正做一件事。”他信奉这一信念,并身体力行。
和伍老师在一起聊时,他常先夸奖一句:“你的功底很好,要发挥出来。”然后说哪些研究值得做,哪些研究不值得做;怎样才能找到真问题,怎样可能走弯路;在教科所做研究有什么优势,又有哪些局限。有几次他是从医院给我打电话,问我现在在做什么研究。
刘长明在讲述他第一次见到伍老师时的情景时说:“只记得他讲到激动时,手舞足蹈,不只是坐在台上,而是多次走到老师中间,用眼神和肢体动作与老师亲切交流。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对教育科研如此热爱的人,我有些震惊。”
伍老师的钻研精神很强,遇到问题不会轻易满足于找个答案,而是要到图书馆查资料,细心研究后再给以答复,他为此跑了很多图书馆,一直到八十多岁的高龄还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在景山学校期间,他坚持写名为《景山日出》的研究日记,后来恢复教材组以后他又以《教材的复苏》为名写研究日记,他对景山学校、对景山教材倾注的心血是难以计量的。有一次,教材组考虑到伍老师年岁大,约定一起到他家看望他,顺带谈一谈教材中的问题。进了家门才发现伍老师已经准备好了一大堆资料,一大堆纸片,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将每个人安排到可以做笔记的地方坐下,然后伍老师就将多日思考的有关教材修改的问题满怀激情地向大家说开了,原本打算说15分钟,不料一说就一小时15分也说不完。
事实上,伍老师并不只是以如此充分的准备来对待这一次谈话,而是以全身心投入的态度对待每一项工作和每一次活动,对待研究,对待事业。他常对青年人殷切地说:“任重道远,要静下心来,多读书,多思考,认认真真搞好教学研究。”
孙秀峰老师说:“只有像伍老师这样对事业追求一辈子,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大师。”
90岁后,伍老师还在伏案工作,还让后辈买当时只出版了2000册的一本英文著作,认真研读,别人听说了都很惊奇。
2006年12月25日,伍老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得悉教育部在筛选各地中小学实验学校,在加强对实验学校的领导、严格对实验学校实验教材的审批的情况下,景山学校的实验教材依然获得通过,写了以下文字:
我们衷心感谢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了我们的第五代教材,对教材的特点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还提出了需要改正的错误……我不久就要出院了,身体还好,请领导和同志们放心。在此我请所领导朱小蔓同志和北京景山学校范校长、老贺、刘曼华同志继续支持我参加北京景山学校这个项目新一轮的具体实验研究活动工作和学习。
不知道伍老师的人看了这文字似乎是年轻力壮的人的请战报告。
最后的孤独
几乎每一位与伍老师接触过的人,都在使用激动、奇怪、意外、感动、激励之类的词向我讲述着伍老师的往事。当大家冷静下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教授花这么多时间来关心、研究一所学校的语文教学?不少人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这是一种研究风格,一种工作视野,一种人格。
参加过伍老师的遗体告别,我不能不说感慨了,在积水潭医院狭小的遗体告别室里,仅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徐书记、离退休工作处吕处长、一位曾经和伍老师共过事的退休教师和我4人,其余都是他的子女,总感到有些不协调。恰巧就在那前后,有位北师大的70多岁的老师去世,与那场面的宏大相比,伍老师的离去确实被冷落了!或许跟他95岁高龄,现在尚健在的同事、学生不多相关,但又不能只看到这一点。我在回来的路上问为什么景山学校没有一个人来?但反过来一想,若按照伍老师的风格,为什么景山学校应该有人来呢?
由于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词,这里就称之为伍棠棣现象吧。这一现象的特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完全没有名利动机的研究。景山教材开始时是不署名的,谈不上名,后来才开始署名,但与所付出的辛劳和所承担的责任相比,这个名真是来之不易。至于利,除了1999至2002年景山学校给伍老师发了少许补助,在其余的20多年里,伍老师从未因为参与研究而拿到一分钱。刘曼华老师一直心怀愧疚的是,1985年他们所编的教材在东城区评比中获奖,拿了些奖金,每位教师分了三块七毛五分钱,由于当时以为伍老师的编制不在景山学校,脑子里就没有想到伍老师,也就没有给他这份钱。伍老师却从未因几十年没有拿到报酬而停止他的研究工作,放弃与景山学校的合作,他感到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发生的只是他对问题的探究和学生的成长。
二是高标准严要求的研究。有人问伍老师为什么几十年不写文章?他说:潘菽老师曾讲过两点:一不要自己抄自己,抄别人的不对,抄自己的也不对,有发展的时候才能写文章;二不要到学校里去找个别的例子写文章,不要把老师的成果当成自己的成果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对研究他追求的是草根、原创、完美,标准很高。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当下的不少人,包括一些做教学研究的人,不难发现合格的并不多。

从美国寄给伍棠棣先生的信
三是严格遵循学术自由、平等探索的研究原则。大家在一起讨论问题时争得面红耳赤,不分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但并不因此损伤友情与亲情,刘曼华老师说形成这样一种研究氛围与伍老师有很大的关系,他是这个团队中的专家,但从不以势压人,他认为大家都是研究者、探究者。刘曼华老师也表达了她的遗憾:伍老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但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很孤独、很孤立。他工作所在单位没有给他配助手,使很多优秀的东西没有转化为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成果,他年岁大了,很可能因此失传。
现在,不是可能失传,而是可以断定已经失传。为何专业水平比较高的伍老师积累起来的学术资源未能被他工作了36年的单位的青年人传承下来呢?深入思考伍棠棣现象,还不是一个小而具体的问题,而是一个教育研究管理与评价体制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