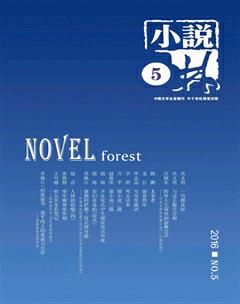哈尔滨水彩笔记
父亲王焕堤既画水彩画,又写回忆文字。水彩跟文字互补,是父亲多年辛勤写生劳作的精选。
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兴致所至,上街画画。父亲画水彩写生入了迷。在菜市中画,在杂院中画,在垃圾堆、厕所边也画。落了雨,色彩淌下来,那就淌下来。水结了冰,等着解冻,然后接着画。
写生的奥义是“生”。生是生命,也是生活,生动,生息,生生。水彩写生就是有这么一股特别的生机,传递“在场”的韵味。看这些水彩画,相信你也能感受到画家就在现场。画家不断与环境、与时间互动,抓取变化,将阴晴雨雪、喜怒哀乐,将感觉、直觉、心情、不可测的种种情形,全部封存在画面之中。
水彩写生,好比不化妆的邻居,素颜、清淡、真实。相比之下,画室里创作的作品,仿佛粉墨登场的演员——精心打扮,完成度更高,匠心独具,却“机心太盛”。
作为一门匆忙的艺术,水彩写生需要快速完成,写生画面上凝固了动态的痕迹,令人回味的是“进行中”而非“完成”的味道,水彩写生的缺陷裸露在外。一笔下去,坏了,也就坏了。画错了,将错就错,追求不可预计的趣味。
看一眼景色,看一眼画。写生是与风景对话,也是人与景的对照。写生作品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性情。
水彩写生包含错误与遗憾,艺术的美感也就在于此。不可预测,不可逆转,亦如人生。
水彩写生,是直觉的,把自己敞开给世界,让光线和色彩,直接冲进来。
写作,是反思的,在纸面上掂量、算计、组合。一个字,一个词,如何恰当。
水彩写生,将即时即刻的痕迹存留下来,几乎完全无法修改;向着记忆深处走去的写作,探索自我的历史,涂涂抹抹,欲说还休。
父亲一个人身兼两职,这对组合真有意思。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才能咂摸出滋味儿。城与人,相互塑造。
每年我跟父亲到哈尔滨老街道中兜兜转转,闲谈一些过去的往事,也渐渐理解了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感情。我感到哈尔滨更陌生了。旧日的哈尔滨好像消失在雨雾中的摩电车,只能听见铃铛响,车子已不见踪影。
从前吃顿肉都像过节,户外厕所冬天屎尿堆成山,楼板踩上去嘎吱响。如今,这样的大杂院越来越少,人与物渐渐消失了。可是,凡濒临消失之物,才显出好。
水彩画中的哈尔滨,是一座历史之城,也是作者的自我之城。城市生成了画家的记忆,街道充满了旧日的痕迹。旧日子浸透了灰尘和油渍,越来越远,却愈发有滋有味。
父亲的文字,仿佛旧棉布一般朴素、洗练;他的水彩写生,却洋溢着丁香花一般浓郁的抒情味道。文字轻描淡写,干净利落,谨慎节制,欲言又止;写生画面却充盈梦幻气息。在水雾氤氲中,在色彩交融中,世事变迁的穷街陋巷,重新闪着光。
文如其人,画如其人。哈尔滨不仅仅是父亲所描绘的对象,同样也是自我的象征,描绘自身的两部分——自我节制与抒情的冲突。
用画笔与文字追溯一座城,同时也是一个老哈尔滨人的“自我完成”。
水彩写生搭建“空间之城”,是对哈尔滨老街巷的探索,是谓“看得见的城市”。
而语词搭建“叙事之城”,则是对哈尔滨时间的探索,这些私人的小历史,构成“看不见的城市”。
画笔与回忆,为正在坍塌的城市时空重新镀上金光。前尘旧梦,浅尝辄止,意犹未尽。如同白酒一盅配小菜一碟。带我神游美好的“凝固瞬息”。
作者简介:王可越,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博士。美国波士顿艾默生学院访问学者。从事媒体艺术研究及创新方法教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