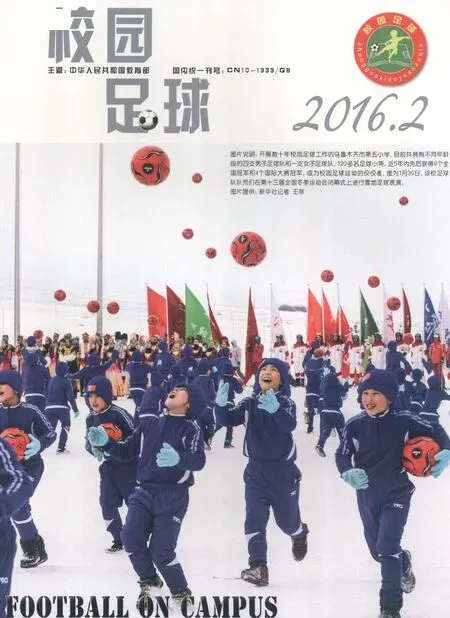给足球人才库装四个“补丁”
——校园足球系列调研报道之六
新华社记者 王浩宇
给足球人才库装四个“补丁”
——校园足球系列调研报道之六
新华社记者 王浩宇
好比“拉玛西亚”之于巴塞罗那队,校园足球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被赋予了夯实足球人才根基的角色。然而,目前校园足球人才培养和流动机制却存在着一些阻碍人才成长的弊端。与其频频感叹“中国何时有梅西”,倒不如先给咱们的“足球人才库”安装一些管用的“补丁”,进行漏洞修复。
足球特色校不是“校队”特色校
足球特色学校的建设是《方案》中唯一有明确时间表的内容(2020年达到2万所,2025年达到5万所)。所谓的特色学校,并不是传统概念上的“校校有球队”,而是“校校每周有一节足球课,绝大多数孩子都有机会踢足球”。但从新华社校园足球调研组各地采访的情况来看,组织校队夺取好成绩依然是很多特色校的追求。对此,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态度极为鲜明。他说:“只组织一个校队,一个学校只有十几个孩子在踢球;拿几个冠军,而其他孩子跟足球没什么关系,这是不行的。既然作为特色学校,就真的要全员踢球。”

记者曾听北京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青少年足球专家张路多次说过,多年前北京的青少年足球就是重锦标,各中小学组校队、争冠军,竞相挖人,尖子球员慢慢集中到几所足球强校,打来打去就这么几所学校。其他学校一看没法玩了,就失去了发展足球的兴趣,结果造成足球人才的断档,教训深刻。张路本人曾多次疾呼,青少年足球再这样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在记者采访过的学校中,有些学校处理得比较得当,比如武汉的万松园路小学和大连的东北路小学,都是既有专业教练带的校队,也有普通学生参加的足球课。大连市教育局今年向全市中小学发布了足球特色校的评选办法,并综合设立了足球训练、保障措施、课程建设、文化建设等7项评分指标。至于学校球队在省、市、区级的比赛成绩,仅作为附加分,且不重复计算。“从体育部门抓校园足球变成由教育部门牵头,评估的主要指标还是有变化的。和比赛成绩相比,我们更重视育人和文化教育。”大连市教育局副局长杨跃权说。
新型足校要避免“穿新鞋走老路”
《方案》中提出要建设新型足球学校,这个“新”到底应该体现在哪里?过去的足球学校多采取“三脱离”的封闭式集中管理,即脱离学校、脱离社会、脱离家庭。大连阿尔滨俱乐部的董事长赵明阳希望新型足球学校不要再延续这个模式,“我不赞成让孩子过早离开父母集中在一起训练,那样孩子享受不到家庭的亲情和温暖,容易孤僻,身心不健康,又怎么能成为一名好球员。”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单吉仁说:“我们非常赞成新型足球学校是文化教育和足球有机融合,文化课不能缺失,并把体育融入到文化中。踢球的孩子跟普通学生一起上课一起活动,业余时间再来训练。”
建立青训补偿制度
在中国职业足球日渐红火的背景下,球星仍然属于“稀缺商品”,而好苗子则成为各职业俱乐部竞相物色的目标。从足球传统校“挖人”已成为一种日趋普遍的现象,往往是球探或经纪人看上某个学校的足球苗子后不通过校方,私下跟家长谈妥条件就拉学生去了俱乐部。被誉为“足球黄埔军校”的大连市东北路小学的校长王作开就对记者抱怨,他们学校的一些学生球员被俱乐部挖走他们甚至事先都不知道,即便知道了也没有办法阻止,因为家长愿意,学校多年来的培养全打了水漂。大连市第二十一中学也是传统足球特色学校,因而也常常遭遇本地或外地俱乐部前来挖人。校长王慧说:“职业足球淘汰率很高,一部分孩子进入俱乐部后却被淘汰了,家长钱没少花,孩子学习也荒废了,没有完成义务教育,这是对孩子的严重不负责任。”
如何避免学校在培养了足球苗子后却人财两空,国际足坛流行的青训补偿金或许可为“他山之石”。巴西不缺足球人才,但也没有忽视保护培养方的利益。巴西在青训补偿方面规定:俱乐部可与14~16岁的小球员签订培训合同,16岁以后可签订职业合同,其他俱乐部想要挖人,需要付出200至1000倍的培养赔偿费,并且会被禁止参加同年龄段的所有比赛。
而中国在青训培养补偿方面远没有形成制度,无序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培养足球苗子的积极性。武汉市足协秘书长付翔说:“现在到处都在挖人,大家慢慢就会产生惰性,不注重培养,而培养的一方老是被挖且没有补偿,后备人才培养就越来越没人搞。而对照国外,有许多国家都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执行:培养出一个梅西,最初培养他的教练和俱乐部都能受益一辈子。”大连市体育局局长张运东以文艺界为例说:“就像演小品,钱都让演员赚了,创作人员不干了,没人搞创作自然就没有好节目。我们现在球员转会市场的钱都让球探、经纪人、俱乐部赚了,踏踏实实搞人才培养的人势必缺乏积极性。”
建立“人才数据库”势在必行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校园足球的育人机制也不能缺乏数据的支持。赵明阳建议搞校园足球应从小学起就建立孩子踢球的档案,他说:“档案跟着球员一辈子,可以避免年龄造假,也好让大家通过数据发现人才,让真正的人才不被荒废掉。此外,数据库做好了一查就知道这个球员是在哪里培养的,培养了多少年,培养他用了多少钱,将来转会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依据给学校支付培养费。”
湖北省教育厅目前已先行一步,正在建立校园足球人才数据库,选拔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登记注册。在赵明阳看来,这种大数据采集和运行维护应该由国家层面牵头去做,更要长年累月地坚持。他强调,“再不做,就晚了!”
近一年来,在国内校园足球的发展大潮中,请进来、走出去的合作项目已经层出不穷,但如何才能给中国校园足球带来“真经”?简单的“拿来主义”显然是不行的。两年多来为全国9个省市培训了275名大、中、小学体育老师的“中英校园足球项目”,目前对于国内绝大多数体育老师来说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
实际上,国内目前各类面向校园足球老师的培训可谓林林总总,但多数培训项目形象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名额有限总是常态,广大基层体育老师强烈的求知欲望,依然很难得到满足。此外,国内校园足球在火爆的表象之下,仍有很多基础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上海市中学生体育协会会长、特级教师徐阿根表示,“校园足球一定要认清自己的定位,不能‘一头热’,真正的足球教育要面向所有的孩子。”
所谓的“一头热”这一年来已经表露无遗,如国内出现的许多引发争议的现象:足球操的横空出世,一些没有条件的学校硬着头皮搞足球,一些商家的活动千方百计要与校园足球挂钩等;国外也有不少企业看到了中国校园足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