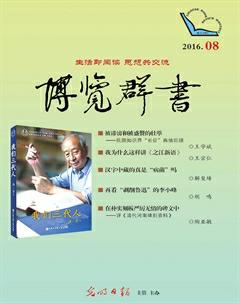跟随帕特南一起探案“追凶”
侯婉薇
曾经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人买回《独自打保龄》一书,想要拿它来当学习保龄球的书籍,但翻开来看才知道它与保龄球毫无关系。这个故事也许有些许夸张和幽默的成分,但是突显了社会科学领域这样一个非常少见甚至有些另类的有趣书名。这本书的特色当然不仅在于有趣的书名,我在阅读这本书时竟意外邂逅了政治学界的福尔摩斯。这一经历更令我这个侦探迷异常惊喜。于是,我阅读这本书的体验就变成了一次跟随作者“福尔摩斯”罗伯特·帕特南(文中我宁愿称他为“帕特南探长”)一起探案“追凶”的过程。
案由:最近数十年美国社会公民参与持续减少
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游历美国,美国人对公民结社的偏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我认为,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莫过于美国的智力活动和道德方面的结社。”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人热衷结社的这一偏好是使美国民主运作良好的能力的关键。美国人用“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学说来反对个人主义,而这种利益又使他们习惯于结社和合作。享有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是美国能够出现各种社团的基础,更使美国人从结社中了解了自己的使命。于是,自《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以来,民主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理解民主社会及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考维度,而对美国公民组织与民主间关系的分析也一直是普遍的民主与公民社会关系分析的核心。正是从这里出发,罗伯特·帕特南探长开始了他的美国社会再发现之旅,而他重新发现美国的过程更像是一次扣人心弦的探案过程。
二战后一段时期,美国不同世代表现出持续的公民参与热情。“富有公民精神的二战一代,……不仅要在国家最高职位上履行好义务,也要在全国的小城镇里恪尽职守。”“到1965年,美国人对公共生活的热情开始明显增加。”当“婴儿潮”一代开始上大学时,公民活动在年青一代中也深受欢迎。在《论美国的民主》出版170年后,帕特南探长仍感叹“美国人建立组织的创造性真是不可限量”。这种“创造性”可由1968年至1997年30年间美国社团组织及参与人数的增加得以管窥。在这30年间,美国全国范围的非营利社团几乎翻了一番,参与人数由1968年的10299人增加至1997年的22901人。然而,在社团表面繁荣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公民结社传统的深刻变化。社团越来越成为团体会员的组织,有的社团甚至完全没有个人会员。结果是,社团组织的增加往往伴随着基层参与的减少。“对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有名无实的会员,而是积极投入的会员。”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尽管“很多美国人继续声称我们是各种各样社团组织的‘会员,但大多数美国人不再在社区组织上花费太多时间”,因此可以说,“美国人已经在远离人群,远离的是不仅政治生活,更普遍的是有组织的社区生活”。
“谁杀死了公民参与?”帕特南探长的探案由此开始。
案情分析与推理:谁是真凶?
这是一桩错综复杂的谜案。帕特南探长重新发现美国的过程完全是一次需要全神贯注才跟得上他的思路的探案过程,其中复杂、严谨的推理就是令人屏息的侦探推理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公民参与持续减少,并且已经影响到美国社会的所有层面。帕特南探长称之为“一个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所发生的神秘事件”。为此,他为自己设定了解答这一谜题的明确目标——找出真凶!
到底是哪些因素(原因)导致了公民参与减少这一现象,人们可以想到的原因各种各样,帕特南探长在探案过程中把这些原因列为这一谜案的凶嫌逐一排查:
忙碌和时间压力;经济难关;妇女加入劳动大军,以及夫妻双职工家庭的压力;居住地频繁变动;郊区化及其扩展;电视、电子革命和其他科技革命;美国经济结构和规模的变化,如连锁店、分公司和服务业的崛起,或者全球化的趋势;婚姻和家庭联系的断裂;福利国家的增长;民权革命;20世纪60年代的系列事件(其中大多数事件实际上发生在70年代,如越战、水门事件等)
帕特南探长对上述每一个(组)嫌疑对象都进行了严肃、缜密的分析,得出了与案件相关的具体结论。他所做的每一个重要结论都是基于一个以上的独立证据,每个证据都源自各种可信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他既列出有利的证据,也不回避不利证据,并通过努力驳斥不利证据以证明结论。
对于“忙碌和时间压力、经济难关、妇女加入劳动大军以及夫妻双职工家庭的压力”这组嫌疑对象,他的分析结论是:现有的证据表明,工作忙碌、经济拮据、夫妻双职工家庭产生的压力只是“很少地解释了社会联系的衰减”。非常明显的事实是,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儿童公民参与下降时,他们的母亲依然是全职母亲,而在平静的50年代、繁荣的60年代以及不景气的70年代成年的人,其参与下降的程度都是一样的。
关于“居住地的频繁变动”,在充分的数据分析和推论基础上,帕特南探长指出,过去50年来美国与居住地相关的流动性根本没有增强,“居住流动性完全可以免于指控”,更谈不上是这桩谜案的主凶。但是,与此相关的战后几十年来美国城市的不断扩张,却对公民参与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原因在于:其一,城市扩张耗去了人们的时间;其二,城市扩张同社会分割的增长相关联,……对于沟通性社会资本而言,城市扩张是非常有害的;其三,最为微妙却有可能影响最大的是,城市扩张破坏了社区的“边界”。“那种似乎促进参与的社区——小型的和相对独立的社区——正在变得越来越少。”30年后人们日常生活的物理分裂对于公民参与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抑制效果。居住在大城市造成了一种“扩张性的公民损失”,大约占到大多数公民参与形式的20%。与时间和金钱压力一样,它可以部分解释美国公民的不参与,但它对这一减少的影响仅仅只是一小部分。
至此,对嫌疑人的追查并未结束。
接下来要排查的就是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至深的电视及电视娱乐。看电视(尤其是对电视娱乐的依赖)和公民参与的减少密切相关,似已成为人们的一个普遍认识。但是,“相关性并不证明因果关系”。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一开始就处于隔离群体中的人会把电视看作最有吸引力的休闲方式而被其吸引。于是,在看电视与公民参与之间完全是另一种因果逻辑联系。帕特南探长还是一个心理分析大师。他认为,看电视之所以和公共交往的减少密切相关,一个原因就是这一媒体本身产生的心理效果。特别是,在使我们知道了一切可以想象到的社会和私人问题的同时,电视也使我们不喜欢就这些问题做任何事。与此同时,电视节目所传递的信息(特定的节目内容,甚至包括电视广告),也部分地造成了明显的反公共效果,并可能促进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生长。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动方式,电子通信和舆论的崛起使人们的休闲方式日趋私人化和被动。具体而言,在20世纪末美国人看电视时间更长,更具习惯性,更普遍,更经常是单独看,而且更多地看那些尤其会造成公民参与减少的节目(如娱乐而非新闻)。这些趋势的发生刚好与社会联系的全国性减少相契合。不仅如此,正是那些最明显地依赖电视娱乐的美国人更倾向于从公共和社会生活中离去。
如此看来,我们似乎完全可以认定电视以及相关影响应该是导致公民参与减少的主要因素。但是,帕特南探长的推理并未结束。在他看来,过多使用这些新娱乐形式的人总是形单影只、被动消极,同他们的社区分离,但我们无法完全证明,如果没有电视他们将会变得更喜欢社交。无论如何,案情分析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我们正在解开的这桩关于公民参与的谜案中,电视和类似的电子产品都至少是个从犯,甚至很有可能是主犯。”
追查造成公民参与减少的元凶的工作富有成效,而追查真凶的努力仍在继续。
“在全社会没有一个角落对这种反公共主义的流行病免疫”的大背景中,年龄似乎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外。遗憾的是,虽然有关年龄的一些特征是解开公民参与减少这一谜题的关键,但这些线索却是极为模糊不清的,因为它同时与两种非常不同的解释有关:生命周期的影响意味着每个人都变了,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未变;代际影响则意味着社会变了,而每个人没有变。在代际意义上,帕特南探长援引的数据表明,在1910至1940年期间出生的人,总体上都更多参与社区事务,更让人信任。其中,在1925至1930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是热心公共事务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公共领域也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但是,战后出生的几代人则好像“被反公共的X光照过,使他们永久性并日益倾向于减少和社区的联系。”这里,帕特南探长面对的问题变成了“为什么这种神秘的X光的作用要经历这么长时间才显现”。帕特南探长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任何一代人要在成年人口中占据多数都需要这么长时间。此外,战后大学招生的扩张抵消了本会更早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参与的灾难性减少,从而使得这种代际影响的效果延后几十年才显现。
战后“婴儿潮”一代拥有宽容、愤世嫉俗以及懒散等复杂的行为特征,更被舆论分析者称为“自由人”。他们的整体思维与态度已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成本——他们对社区生活的志愿贡献减少、慈善捐助减少、信任减少,责任分担也在减少。晚于“婴儿潮”一代出生的被称为“X一代”的人群则比他们的先辈在同一年龄段时更为物质主义。尽管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代际更替是解释公民参与减少的一个关键因素,但严谨的帕特南探长的探索并未终结于此。相反,他进一步分析了代际因素对不同形式参与的不同影响。具体而言,去教堂、投票、政治兴趣、竞选活动、协会参与、社会信任的减少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代际更替。与此不同,诸如打扑克牌、在家娱乐等各种非正式社交的减少,则应主要归因于全社会范围的改变,原因是所有年龄和辈分的人都倾向于脱离这些活动。此外,其他形式的参与如社团聚会、与家人和朋友聚餐、走访邻居、打保龄球、野餐、访友、寄贺卡等减少的原因则比较复杂,需要从社会范围的改变和代际更替两方面寻找原因。最后,帕特南探长得出结论,“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总减少的几乎一半可以归因于代际差异”。
但是帕特南探长并不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充分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二战后成年的美国人与其父辈甚至兄弟姐妹如此不同?帕特南探长的努力取得了成果。他发现,在1945年达到高潮的战时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加强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热心。美国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了它的直接影响,因而出现了全国性的爱国主义和地方性的公共活动高峰。可以说,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灾难所导致的社会习惯和价值观的变化是最近几十年公民参与变化的主要原因。
结案:什么杀死了公民参与?
案情分析和推理至此,似乎可以结案了,但敏感的帕特南探长分明感受到了来自其他不同解释的挑战。他需要回应这样的挑战,从而使其案件分析结论更为令人信服。于是,他又逐一驳斥了传统家庭结构崩溃、民权运动(特别是白人从公共事务中脱身的“白人逃亡”)等对公民参与的影响,因为这些因素与公民参与减少之间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对于人们更为关注的政府扩大和福利国家发展对于公民参与减少的影响这一更为广泛的话题,因其涉及政治学领域有关国家职能的基本问题,帕特南探长进行了应予以重视的评论。在他看来,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已经对社会资本造成了破坏,如在50年代和60年代对贫民窟的清理就因扰乱了既有的社区联系而使社会资本被削弱。(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是,要判断政府政策是否造成了保龄球队、家庭聚餐以及文学社的减少,却要困难得多。“国家干预对私人力量的‘挤出破坏了公民社会”的命题不仅证据不足,事实上也与1947年到1998年间美国的实际情况不符。
接着,帕特南探长进行了结案陈词。他认为,时间和经济压力对于过去几十年美国社会和社区参与的减少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只有不足10%的减少可归因于这些因素;市郊化、上下班和城市扩张也起到了助推作用,但同样也只能解释10%的参与减少;电子娱乐(主要是电视)实质性地影响了人们的休闲方式,25%的参与减少可归因于此;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代际更替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因素,尽管它对较为公共性的参与形式影响较大,而对私人的非正式社交影响相对小一些,但仍可以解释50%的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减少。
找到了杀死公民参与的元凶,应该到了可以结案的时候了。但是,帕特南探长就像自称为“咨询侦探”的福尔摩斯一样,对于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既然社会资本衰落已经成为现实,那么这种状况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影响?这时的帕特南探长就是一位“咨询侦探”。虽然存在不好的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阴暗面,但总体上社会资本能够让公民更加轻松地解决集体问题,特别是人们谈论甚多却仍然难以摆脱的集体行动困境,人们的信任可以大大降低商业和社会交往的成本,社会资本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可以使人们培养并维持一种有益于自身与社会的性格特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增强了人们更善良、更包容的自我本性,而民主制度的绩效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本。既然社会资本有益于社会和公民个人,也有助于民主政治,对于帕特南探长这样一位“咨询侦探”来说,找到“我们该怎么办”的路径才可以放心结案。
他还需要继续探案。对于社会资本的重建,他提议还要回到探询美国社会资本旅程的起点—政治与政府,而走出三个认识误区是重建社会资本的关键。这三个认识误区表现为三个错误争论。第一个错误争论是,重建社会资本应该“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第二个错误争论是,政府是问题本身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个错误争论则是,重建信任是需要改变机构还是改变个人。对于这三个错误争论,帕特南探长的回答简洁而明确。在他看来,国家的角色和地方的角色在重建美国社区方面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政府虽然要对社会资本流失承担部分责任,但没有政府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对于第三个错误争论的答案,帕特南探长的回答是,既需要改变机构,也需要个人作出改变。
社会资本与“独自打保龄”
“探案”结束,帕特南探长的角色似乎也应还原为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和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教授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是社会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相互信赖的规范。“社会资本”概念并非帕特南首创,在他之前的整个20世纪已有6位研究者分别独立使用了这一概念。但是,真正使“社会资本”概念为人们所广泛关注和熟悉的正是帕特南。帕特南于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不仅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声誉,更使“社会资本”一词成为引发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城市规划、建筑学诸学科共同兴趣的一个概念。
不管是出于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影响或是其他原因,政治学与经济学分享了许多共同概念甚至方法。尽管如此,作为经济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当我第一次听到“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时还是兴趣盎然,倍感新鲜。
罗伯特·帕特南教授于1941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青少年时期就参加了一个竞争性的保龄球社团。在社会资本浓厚的那个年代,保龄球社团的经历应是给他留下了深刻而温馨的记忆。这是我对帕特南探长《独自打保龄》这个有趣书名的来历所作的一次“探案”尝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