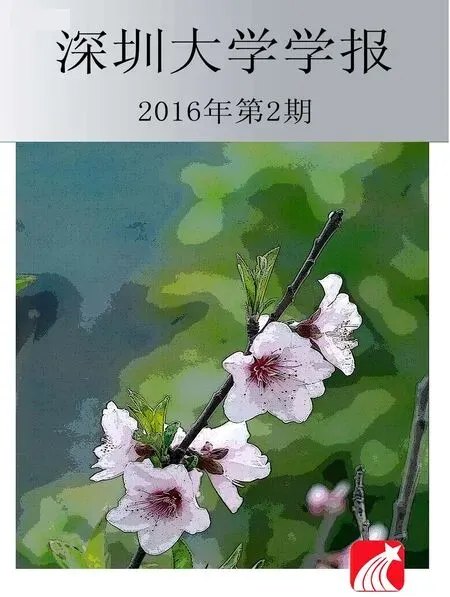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散工的现实状况与学理分析
周建新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散工的现实状况与学理分析
周建新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深圳518060)
散工主要指城市外来工中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散工现象的出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打工潮”。随着90年代以后产业结构的转型,就业压力的增大,散工队伍日益扩大,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基于对当前中国大陆经济最具活力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散工在人口学特征、工作和收入、生活起居、社会关系、社会保障和救助等方面的实证分析,表明该地区散工呈现出经济贫困、身份地位边缘化、择业和日常行为的“自由性”、社会关系的同质性和内敛性,以及潜在危险性等群体性特征。重视和解决散工问题应该从社会结构、适应问题、非正式关系等多方面入手。
外来工;散工;贫困文化
一、关于“散工”问题的研究
“散工”进入中国大陆的学术话语系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散工”这一外来工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1]。1994年,周大鸣教授率先在国内对外来散工进行了调查分析,明确阐述了散工的定义,描述了一个散工聚居和村落生活的概貌,接着分析问卷调查资料,对散工的性别和年龄构成、婚姻和家庭状况、文化程度、从事的工种、来源和动因、工作和生活情况、非正式组织以及社会关系等作了较详尽的描述,最后就散工调查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外来工其实并不是单一性的人群共同体,他们之间是有分层和区别的,因此呼吁改变对待散工不公平的态度和妥善处理散工所引起的社会问题[2]。
此后一些大陆学者的研究也对散工问题有所涉猎,如李培林关于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的研究[3];甘满堂有关城市街头外来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现象的研究[4]。海外对散工的关注主要体现在香港学者的研究中,如香港城市大学的黄洪、李剑明等分析了边缘劳工的具体生活处境、职业变动的因素以及边缘劳工对政府及有关政策的观感,并为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可推行的政策措施方面的建议[5]。国外方面,主要有学者从社会排斥的角度关注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但也间有以“边缘劳工”或“散工”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发表,前者如Bruce S. Harvey和Rudolph L.Kagerer对美国乔治亚州的家禽饲养工人的研究,关注了他们选择工作或者是辞职领取失业保险和救济的决策背后的驱动因素[6]。后者如Noel Gaston和David Timcke对澳大利亚青年散工的研究,考察了影响他们从散工转变为正式劳工的短期和长期因素[7]。这些成果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比较研究意义。
2002年3月,受加拿大科瑞澳公司上海代表处的委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曾对珠江三角洲部分城市的散工基本状况、工作、生活、社会关系、将来计划等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随着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外来工来到珠江三角洲。同时,随着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那些文化程度偏低的外来工很可能被“裁减”,他们将加入到散工的队伍之中,因此,散工队伍将越来越大,如果不加以积极引导和有效管理,将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珠江三角洲的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8][9]。
目前,散工现象在城市已然比较普遍,社会也开始习惯了这个群体的存在,但散工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例如对散工的界定、文化特性、群体认同、女性散工、散工的社会保障、散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于某个特定地区(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散工的现状描述和特征归纳,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简单的政策建议;研究样本也存在着量小、分散的缺陷。因此,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加大理论分析,将研究范围扩大至东南沿海地区,试图透过大量的个案访谈和问卷资料,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对散工进行深入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二、散工群体的产生和构成
“散工”现象的出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打工潮”。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经过数年的实践,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经济特区中的一些城市吸引了巨额的外资,创办了大量的“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需求大量的劳动力。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把中国内地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他们纷纷南下广东、福建等地区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这种“求过于供”的劳动力市场,让南下的外来工常常一到车站、码头就被前来招工的厂家、公司“抢去”了。那时,只要年轻,能识字,要找一份工作实在是一件不难的事情。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这些地区的中心城市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受到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影响,外来工高度聚集的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如制造业、电子厂、玩具厂、鞋厂的订单大大减少,这些企业的工人大量被辞退。而这期间由于正式劳动部门、中介机构发育不充分,涵盖范围有限,外来工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开始突出。而且中国农村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性衰退”,加之业已形成的“打工潮”的惯性力量,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从90年代末期直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外来工被抛出正规的就业市场,游离于正式就业之外。据测算,广州市实际登记在册的外来劳动力约占在穗外来劳动力的一半左右,散工等非正规就业形式已成为一条重要的就业途径。
散工的出现,从主观上来说,往往是由于许多外来工认为自身的文化素质低,在城市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他们对劳务市场和职业中介机构不信任,为了谋生,只好采取有活就干的方式,做起了散工。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一部分外来工也认为散工揽活自由,较少管制,而且常常拿到的是现钱,心里感到踏实,所以虽然不如正规就业那样稳定和有保障,他们也愿意为之。
当然,散工的产生和存在,更直接的因素也是出于他们自身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散工具有“经济人”理性特征,他们许多人明明知道来到大城市谋生的艰辛与痛苦,但为了挣钱养家,受经济利益驱使,也只好不情愿而为之。在調查中,许多散工都说:“在家里比在城里舒服,但为了挣钱,小孩要读书,没办法只好出来打工”。挣钱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首要目的。有学者认为,“民工潮”不完全是农民自由意志的体现,而是农业严重凋落、无法生存的被迫选择,出外打工其实是惟一出路。
同时,“民工潮”是城市拉力与农村推力的双重结果。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整个农村发生了巨大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并产生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推动了农村劳动人口的向外发展,农村改革使人口流动得以可能;另一方面,城市改革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特别是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城市发展比农村有了更多的机会,一些职业的空缺,如建筑、搬运、环卫、保姆等,留给了进城农民。在这种推力与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外来工成为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一股不可或缺的部分。
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造成了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散工就成为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非常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失业下岗人员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因此,他们的失业不是因为暂时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而是许多人将永远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于是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做些制度性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求。
如此看来,在我国散工群体中,农民工成为外来散工的主体;城市下岗人员是散工群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近年来一部分大中专毕业生因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也在做一些临时性的、短暂性的工作,因而也会加入到散工队伍中来。应该说,散工已成为我国众多失业人口、流动人口的巨大生存空间,他们是城市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辅助部分。
三、散工生存状况的实证分析
为深入调查和掌握散工的生存状况和群体特征,笔者所在课题组立足于当前中国大陆经济最具活力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广州、杭州、厦门等城市的散工为研究对象,着重于散工的群体身份、谋生手段、经济收入、生活起居、关系网络、城市体验、社会适应,以及他们的社会支持、救助保障等内容。运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社会学的调查问卷等研究手段,深入散工生活和工作的场所,与他们谈心、交朋友。调查从珠江三角洲扩大至长江三角洲和闽南经济区,共发放问卷2110份,回收有效卷1967份,回收率为93.2%,其中广州市902份,厦门市755份,杭州市310份;访谈个案近500例,其中广州市300例,厦门和杭州各有70多例。以下从五个方面分析。
(一)人口学特征

城市人口学特征 广州 厦门 杭州身份构成7 4 6 9 8 . 8 % 3 0 . 0 3 % 0 0 2 2 0 7 1 . 0 % 3 6 1 1 . 6 % 3 8 1 2 . 3 % 6 7 8 7 5 . 2 % 2 7 3 . 0 % 3 7 4 . 1 % 1 6 0 1 7 . 7 % 6 0 . 0 9 % 1 6 5 . 1%性别 男女4 9 4 6 5 . 4 % 2 6 1 3 4 . 6 % 1 8 0 5 8 . 1 % % 1 3 0 4 1 . 9%农民下岗工人毕业学生做生意其他年龄2 0岁以下2 0 —3 0 岁3 0 —4 0 岁4 0 -5 0 岁5 0岁以上6 7 7 . 4 % 3 1 2 3 4 . 6 % 3 5 0 3 8 . 8 % 1 3 5 1 5 . 0 % 3 8 4 . 2 % 6 4 2 7 1 . 2 % 2 6 0 2 8 . 8 % 1 8 2 . 4 % 5 2 5 6 9 . 5 % 1 6 0 2 1 . 2 % 4 2 5 . 6 % 1 0 1 . 3 % 2 6 8 . 5 % 7 8 2 5 . 2 % 1 1 8 3 8 . 1 % 5 8 1 8 . 7 % 3 0 9 . 5 % 2 5 5 2 8 . 3 % 1 8 9 2 0 . 9 % 9 0 1 0 . 0 % 4 6 5 . 1 % 6 4 7 . 1%湖南四川广西江西安徽河南贵州本省其他2 3 3 . 0 % 1 1 6 1 5 . 4 % 4籍贯2 5 8 2 8 . 6 % 1 4 1 1 8 . 7 % 4 9 6 . 5 % 1 4 1 . 9 % 3 6 4 . 8 % 3 0 0 3 9 . 7 % 7 6 1 0 . 0 % 1 . 3 % 8 2 . 6 % 2 0 . 6 % 4 0 1 2 . 9 % 6 9 2 2 . 0 % 5 4 1 7 . 4 % 4 1 . 3 % 6 8 2 1 . 9 % 8 0 2 5 . 8 %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外来散工研究》课题组在广州、厦门、杭州三地的调查问卷材料综合而成。
综合三个城市的问卷结果,表明东南沿海城市散工主体来源是农民。值得注意的是,下岗工人以及毕业的大中专学生,也加入到散工队伍中,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生力量。散工以男性居多,约占65.5%,女性为34.5%。这是由于传统观念、家庭分工模式和生理等多重原因造成的。散工多来自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限制了女性外出务工。此外,散工一般从事的是脏活、累活、重活,女性的体力难以承担。散工中的少数民族很少,职业分布也没有呈现集中趋势。散工的年龄特征呈一种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即集中在20-29岁、30-39岁与40-49岁三个年龄段。这种年龄分布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年龄分布、社会特征、散工的工作特点密切相关。散工的籍贯分布呈现出较明显的“空间亲缘性”,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落差和路途远近是散工选择务工地的重要因素。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散工居多,但也有部分散工面临婚姻方面的困难和选择,尤其是未婚女性散工将婚姻视为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而在等待和观望。在文化程度方面,散工以初中文化程度居多,其次是小学,还有相当一部分根本没有上过学,但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也占有相当比例。散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有代际上升趋势,但就整体而言,散工文化程度仍偏低。
(二)工作和收入
散工寻找工作的途径主要是等雇主和通过老乡、亲戚或者朋友介绍,另有不少自称是“自己闯来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先期打工者的影响和带动。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当今大陆最主要的外出务工途经。散工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从事脏、苦、累的工作,普遍存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他们通常早出晚归,每天工作时间多在10个小时以上。即便如此,散工在就业上还有着很强的偶发性,工作不稳定,开工率低,常常是今天有事做,明天就可能失业。所以很多散工都是有活就干,利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揽活、来生存。
散工揽活的手段多样,灵活方便。第一,写个牌子或纸片摆在路边。很多搬运工都是三五成群地蹬着三轮车在街头路边等生意,雇主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跟他们谈价钱,或者按照牌子或纸片上留下的电话与散工联系即可。这种揽活方式随意性较大,宣传范围也十分有限。第二,贴广告。批量地印刷小广告贴在路边、围墙或电线杆上,写明服务的内容和电话联系方式。第三,在职业介绍所等待雇主,向雇主进行自我推销。保姆采取这种方式揽活的比较多。电话、手机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是散工们必不可少的谋生工具,调查中大多数散工都购置了手机,不少散工还有专门的电话本,上面记载着一些雇主、同行、亲戚、老乡的联系电话等信息。
调查表明,散工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以杭州市散工为例,每天工作在8小时以内的只占21.3%,在8-12小时之间的有45.5%,另有25.5%的散工每天要劳动12-15个小时,更有约7.7%的散工的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可见散工们由于一切都靠自己,只要有活干,有钱挣,就会不知疲倦地工作,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散工们长时间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打发闲暇时光的娱乐方式,正如一个被访者所说的:“反正闲着也难过,不如多干一下,多多少少还能挣点钱”。
散工的工钱多数是按照月、天、小时或者是件数来获取。工钱的价格多由雇主决定,通常很低廉,但散工常常为揽活而不得不委曲求全,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还有小部分是通过自己和雇主协商或者是中间人以及其他方式来确定。在受调查的广州市散工中,年收入在3000-5000元的约占总数的31.9%;年收入在5000-8000元占28.8%;年收入在8000-10000元的占11.9%;而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仅占9.1%。这与在工厂、公司的外来工相比,散工虽然也被克扣工钱,但是其比例要小得多。约有60%的广州市散工认为没有被拖欠过工资,只有3.7%的认为经常拿不到自己应有的劳动报酬。
(三)生活起居
散工的生活非常简单和朴素。由于收入微薄,散工们的日常开支十分节约。对于房租费、水电费、伙食费、生活用品费等必要的开支,他们省了又省。调查显示,超过半数以上的东南沿海城市散工(家庭)每月开支在500元以内。其中广州市散工每月开销在100元以内的有97人,占10.9%;每月开销在200-300元的散工(家庭)最为多见。为进一步了解散工的日常开支,我们专门对女性散工购买美容护肤品、衣服的消费及美容美发的频率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有58.5%的散工几乎没有买过美容护肤品,41.5%的散工的年服装消费不足50元,低于200元的共占66.2%,而从来没有或很少做过美容美发的占87.7%。
为了节省开支,散工在日常生活起居中想尽办法省吃俭用。在居住地点上,他们多居住在比较偏僻或者租金比较便宜的地方。“城中村”是散工们的主要栖息地,还有少数人寄住在亲友家甚至过着流动寄住的生活。在租居模式上,多以家庭、亲戚、老乡合租而成的联合家庭形式为主,或合租一套或共居一室,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活成本。这既是散工们无奈的客观选择,也是他们自觉的生存策略。散工们从农村来到城市,不仅是地域空间的跨越,也是文化上的跨越、心理上的跨越。当这种跨越出现衔接断层时,他们很自然地会运用乡土社会的经验来修补自己的地位缺失,这就是“家”及网络关系的照搬及推广至城市社区生活中,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在城市边缘地带聚居。
行业和居住方式的多样性也导致了散工们饮食方式的多样性。调查发现,散工们解决吃饭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自己做,有的和别人合伙做;有的在外面随便吃快餐(如搬运工),有的在雇主家和雇主一起吃(如保姆),还有的是在工地上吃(如建筑工)。散工在饮食问题上,既节俭又重视。节俭是为了省钱,寄回家中补贴家用;重视是因为散工从事的多是重体力活,身体的健康和强壮尤为重要,因此不仅要吃饱而且还要适当地补充营养,城里人不喜欢吃、价格相对便宜的肥猪肉便成了散工们改善伙食的佳肴。散工饮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一日二餐或一天多餐。一日二餐是指散工们一天只吃午餐和晚餐两顿,因为散工们多数较晚起床,于是通常不吃早餐或者在上午10点、11点早餐和午餐一起吃。一天多餐是指散工由于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他们或在工作过程中吃点东西以补充体力,或者晚上9点、10点回到家后吃些“夜宵”。
散工的省吃俭用还可以从他们生病的处理方式中得到反映。据统计,在杭州,有48.7%的散工在患病之后会“自己买药吃”而不去看医生。更有11.3%的人嫌药贵,连药都舍不得买,不采取任何措施,“自己熬过去”。而在广州,这类人的比例则更高,为12.6%。另有一些人会求助于打工者中懂得医药知识的老乡,如果遇到大病,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可想的时候,他们才会到诊所或正规医院就医,并有不少人会选择回家治疗。
散工的平时生活十分单调,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或是百无聊赖地等待工作之后,睡觉就成了他们最主要的休息方式。在杭州和广州,分别有43.2% 和39%的散工认为闲暇生活“单调”或者“很单调”。他们闲暇生活的方式也十分有限,主要是看电视、聊天、看报纸、逛街等。男女散工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有着性别取向、兴趣爱好、条件限制、家务分工等方面的原因。
(四)社会关系
从调查问卷数据来看,散工们的社交网络尚带有十分浓厚的乡土性,具体表现为与他们关系密切、来往最频繁的仍是具有血缘或地缘关系的“家人”、“亲戚”、“老乡”。许多人都是与通过传统关系网络提供的信息而一同出来务工的。来到沿海城市务工后,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人基本还是上述“自己人”。持这种意见的散工在广州、杭州和厦门分别占调查总数的95.6%、94.95%、85.1%。这种情况不但反映出散工的求职对亲友的依赖,也反映出流动劳动力是怎样自我组织和自我服务的。按照社会学家帕金的“社会屏蔽理论”,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社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10]。此外,社会的屏蔽会带来负面影响,造成“社会隔离”,导致社会资本的效用的局限性,如穷人的周围邻居和其他社会网络成员也多是穷人,不利于获得更多更好的信息和资源,形成恶性循环的“社会隔离”。
不过,由业缘而发展成的“朋友”已在散工们的日常社会互动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男女两性在社交网络方面也存有些微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男性通过业缘纽带发展的朋友关系要多于女性,显示出更为外向的社交心态。本来,朋友常常是指在工作、学习中结交而成的较为现代的关系,但因为普通劳动力无论是工作学习圈,还是业余交流圈多限于亲戚、老乡,所以朋友往往产生于亲戚老乡之中,朋友关系往往与亲戚老乡关系重叠。因此可以说,虽然在散工的生活当中,“朋友”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些朋友仍局限在与他们有着相似境遇的散工群体之中,散工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是以传统的血缘、地缘纽带为主。
散工与外界的交往对象主要是所在城市的市民。他们相互之间的接触主要是工作上的相互来往,以及在所生活社区与房东、邻居间的有限的交往。尽管接触有限,散工们对于本地人的评价并不是人们一般猜想的糟糕。在问及“与本地人关系”的问题时,广州市有62.2%的散工回答是“一般”;回答“很好”或者“较好”的散工占9.7%和19.2%;认为自己与本地人的关系“较差”或者“很差”的散工仅占6.3%和2.1%。而在杭州,散工们对于杭州人的总体评价也是比较正面的,认为“一般”的有25.8%,认为“比较融洽”的占30.3%,另有12.9%的评价为“非常融洽”。
在组织行为上,散工群体兼具内聚式和开放式特点,可以说是“形散而神不散”。他们一般都以地缘和血缘关系结成了松散的非正式团体,“抱团”现象显著。他们往往聚居在一起,从事相同或相关的工作,彼此之间相互照应,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也能共同遵守默认的准则开展良性互动。因此,同行之间的散工有着较融洽的关系,恶性竞争、相互拆台的现象很少发生。此外,由于一些散工往往约定俗成地划分了各自的生意范围,各自为政,因而也有不少散工与同行之间很少交往。
(五)社会保障和救助
中国的非正规劳动市场具有“容易进入,就业形式多样,就业与保障体系没有制度性联系”[11]的特点,作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主体的散工,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失业是散工最为担忧的问题,正是由于工作的零散性质,散工往往难有工作稳定的保障,短期失业也就难以避免。由于散工工作性质的零散及工资保障的缺乏,有49.0%的散工说曾遇到过身无分文的境况,这时就只有求助于身边的老乡或亲友,甚至需要家里提供接济。散工与雇主的关系很松散,没有很严格的契约、合同关系,往往活一干完,雇佣关系便结束。在广州调查中,有778人说他们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占全部调查人数的87.7%,只有其余的109人是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仅占12.3%。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散工们的医疗和健康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特别是一些危险性较大的职业,如建筑工,他们的工伤出现率比较高,但得到赔偿的概率却很低。当问到人身安全问题时,许多散工都显得很无奈,认为出了事也只好自认倒霉。
在统计分析时,我们还对不同性别进行了分类计算,以反映性别群体间的差异。统计结果表明,男性散工最苦恼的五大事项依次为 “挣钱太少”(58%)、“怕生病”(21.6%)、“竞争太激烈,工作压力太大”(19.3%)、“子女上学问题”(12.5%)及“生活条件差”(12.5%)。女性散工则分别为“挣钱太少”(54%)、“子女上学问题”(17.7%)、“怕生病”(16.1%)、“生活条件差”(14.5%)及“本地人对外来工的歧视”(11.3%)。广州散工最担心的问题分别为“没有工作”(39.8%)、“子女上学”(24.4%)、“身材不好”(21.3%)、“人身安全”(10.2%)和“遭到歧视”(4.3%)。男女散工在先后排序及内容上有着一定的差异,但仍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
在遇到这些困难时,散工们又会向谁求助呢?数据显示,散工们对于政府救助的信任度较低,因为在散工眼中,国家和政府似乎是很抽象的概念。在杭州有1/4的被访者表示“不能指望”、“不敢奢望”政府为他们提供帮助。广州散工则仅有4.8%的散工愿意找政府劳动部门求助,小部分散工干脆选择“不需要帮助”。广州、杭州和厦门三地的散工基本上都主张“自己解决”或“找亲戚、老乡和朋友帮忙”。对于希望政府提供的帮助事项,三个城市的散工的选择也相同,分别为“平等的工作机会”、“住房、医疗、保险”、“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解决子女上学问题”、“平等的户口政策”。
四、散工的群体性特征
综合上述分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散工具有如下群体性特征:
第一,散工在经济上是贫困的,无论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工作酬劳,都处于整个城市的底层。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用微薄的收入来支持更为贫困的农村老家,很多人即使在城市辛苦打工一辈子也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个人或家庭贫困的命运,在散工群体中,贫困是大面积存在的普遍现象。
第二,散工在身份地位上是边缘的。一方面,因为外出务工,散工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既定的农民角色,不再承担以往从事农业生产的责任和义务,生活方式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另一方面,他们身在城市而又不是拥有合法居留权的城市居民,这使得他们既在精神上得不到认同又在物质上不能分享现代文明的成果,生存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而且散工身份地位的边缘性还使他们丧失了一些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使他们本来就已经相当微弱的社会影响力更加被弱化。
第三,散工的择业和日常行为上具有“自由”性。散工的这种“自由”包含多层含义:一是职业的不固定性。很多散工表示,他们从事过不同职业,甚至什么活都干过,只要能找到一份赖以维生的工作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频繁的流动既使他们显得“自由”,也给他们增添了许多烦恼,其中最令他们头疼的莫过于暂住证的问题;二是生活上的选择弹性。很多散工都提到他们干活比较随意,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工作还是休息都由自己决定,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表示不愿去工厂,受不了约束,还不如做散工自由;三是他们在获取劳动报酬上的“自由”。很多人之所以愿意从事散工,很看重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完成一件活后,能够马上拿到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用他们的行业话语来说,就是“结现”。当然,散工的这种“自由”是相对的,他们的“自由”,准确地说是他们不愿安于现状却又不得不安于现状的形象诠释。
第四,散工的社会关系具有同质性和内敛性。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与老乡的紧密关系上,即工作上与老乡分工协作、共同进退;生活上同吃同住,分享家庭式的关怀温暖,地缘上的亲近在远离家乡的异地凸显出来。此外,共同的语言、相近的生活习惯等,把来自同一地区的人们紧紧吸附在一起,其社会关系具有很强的内敛性。由于他们的社会关系基本上是以血缘地缘为主,他们即使生活在异地他乡,也会自然地“复制”原有的生活形态;与此同时,他们所在的当地社会对他们某些方面、某些程度的歧视,反过来又会强化散工群体的内敛性。有学者认为,“城市边缘群体,在社会学研究中特指在城市化过程中,进城后的农民未能完成城市化,未被城市文化所接纳,只得处在城市文化的边缘。他们身在城市。但自身的文化特征却表现为较强的乡村文化色彩。”[4]从这个角度来说,散工社会关系上的同质性和内敛性可以说是乡村文化、乡土性的直接反映和表现,散工有可能成为城市传统文化的最后捍卫者。
第五,散工群体具有一定的潜在危险性。虽然调查资料表明,大多数散工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靠正当的劳动赚钱谋生,但也不排除社会学者黄平所说的由于市场没有提供机会给穷人,穷人最容易进入的就是走私、贩毒、包括贩人[12]的情况。如若处理不当,散工很可能成为社会流民,给社会带来不小的威胁。因此,若要圆满解决城市外来散工问题,消除散工群体潜在的危险性,关键还在于政府有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综上所述,散工是被排斥在城市主流文化之外、位于城市最底层的外来工群体,是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都市中的边缘群体和弱性族群。
五、几点思考与结论
1.有关散工在城市的生活现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学者们集中探讨的热点问题。散工由于自身所处的边缘位置和有限的社会资源,决定了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挣扎。他们身上处处显示出“贫困文化”的种种特征,散工研究具备了与底层社会理论对话的基础。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对于底层贫困问题主要有三种看法,即:贫困文化论、社会排斥论和相对剥夺论。前一种理论从底层社会个人角度解释底层贫困问题,认为底层民众自身应为他们的贫困承担主要责任;后两种看法则从社会结构角度出发,看待底层贫困问题,认为底层贫困由整个社会结构造成。这些观点都为散工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理论视角。然而散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贫困文化”,并不是全然源于自身的懒惰,或者说自甘堕落而致,也并非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所认为的是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人群所拥有的一套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整合体系,而更在于由于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习惯性的力量,直接剥夺了他们的发展机会,限制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不是散工选择了贫困,而是贫困选择了散工,他们无法选择。这样要摆脱贫困就需要有更多的外力的“牵引”,并激发穷人们“内力”使之迸发。两股力一同发力,才能解决贫困。因此,散工虽然说是“贫困文化”的表征者,但更是社会结构的产物。所以,解决散工和散工问题,不能仅仅从散工本身入手,而应着眼于更大层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及制度规范。
2.散工作为外来移民,适应问题也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一问题既与社会学的传统与现代的讨论相关,也与城市化和族群关系理论相连。多年来的散工研究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说明,由于城乡劳动力二元分割和社会习惯性的力量,散工在居住空间、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当地社区隔绝,形成典型的“二元社区”。尽管外来散工从他们的自身结构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群体,但他们成为被分割、孤立的一元,处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边缘,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发展机会,限制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3.散工的社会关系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和内敛性,国内外学术界在对外来移民社区的研究中都发现了散工群体有着明显的社会认同边界。这是因为散工处于体制之外,不能享受国家提供的服务和社会保障,只能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所形成的网络获得在城市边缘的立足之地,这些网络就是散工们的“社会资本”。散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可纳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讨论,散工看似“自由”,脱离了国家体制的直接控制,但实际上,国家权力对散工的影响和渗透无所不在,只是国家权力的操作方式变为间接性的。散工也成为“有实无名 ”的社会群体,“社会性”在散工群体中被凸显,非正式关系在散工群体中居于主导地位。散工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加深了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野。
4.散工既指称一个特定的社会人群,也表示一个特别的就业类型。这种社会从业者或就业类型在世界各地以及历史上都有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存在,并非为现今中国大陆所专有,只是称呼不同或没有专称而已。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经济改革的深入,城乡移民的日益增加,城镇职工职业流动的日趋频繁,散工作为一种灵活的就业形式,越来越成为吸纳流动劳动力、下岗人员、新就业人员的一个巨大空间。鉴于中国大陆的散工人数众多,影响范围广泛,身份特征模糊而复杂,衍生的问题突出,使得将其作为一个特别的社会群体进行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5.依照新的社会分层理论方法,我们可以认为散工正是我国大陆一个形成中的阶层,或者可以归属为某一亚阶层。它已具有自己比较独特的特点和形成中的边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城市非正规就业形式的拓展,散工的人数在日益增加,并开始具有了日益鲜明的群体特征。例如,散工中的主体部分就已开始形成了与农业农民、产业农民工、农民个体工商户等有别的身份认同。
6.对散工现象进行深入的解读,我们必须由具体而微的分析层次上升到一个更具宏大视野的高度。简而言之,我们应当将散工群体置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城乡二元化、都市二元化以及世界体系的脉络中来理解。城乡二元化形成了移民的推力和拉力,都市二元化则造成了城市就业机会与劳动力市场的割裂和阶层差异,世界体系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架构则是散工群体日益壮大的全球背景。
7.深入调查和研究城市散工群体,将促成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机构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对外来散工给予更大的关注和支持,尽快地改变散工的边缘地位和贫困状况。建议有关部门积极引导灵活就业人员树立积极的生活观、就业观以及人生观,帮助外来散工融入城市社会,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和改善城市管理部门各种不利于“外来散工”生存和适应的政策、法规及习惯做法,改变社会特别是城市政府机构人员和城市居民对散工的刻板态度和不良印象,倡导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和经济援助。一言以蔽之,散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产物,积极妥善地解决散工问题,是我国实现社会平稳转型、达成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一环。
[1]周大鸣.珠江三角洲外来流动人口研究 [J].社会学研究,1992,(5).
[2]周大鸣.广州“外来散工”的调查与分析[J].社会学研究,1994,(4).
[3]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
[4]甘满堂.城市外来农民工街头非正规就业现象浅析[J].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8).
[5]黄洪,李剑明.香港“边缘劳工”质性研究:困局、排斥与出路[M].香港:香港乐施会出版,2001.2.
[6]Harvey,Bruce S.&Rudolph L.Kagerer.Marginal Workers and their Decisions to Work or to Quit[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1976.Vol.35,Iss.2;pp. 136.
[7]Gaston,Noel&David Timcke,Do casual workers find permanentfull-timeemployment?Evidencefromthe Australian youth survey[J].Economic Record,1999.Vol.75, Iss.231,pp.333-347.
[8]周大鸣,周建新.2002年广东省外来工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A].广东社会与文化发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蓝皮书系列)[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9]程瑜,周建新.珠江三角洲外来散工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
[10]Frank.Parkin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A Bourgeois Critiqu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53-58.
[11]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12]黄平.中国大陆农民工研究座谈会纪要[DB/OL].http:// 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2447. 2000-12-23.
【责任编辑:林莎】
The Reality of Casual Workers in the Coastal Cities in Southeast China and its Theoretical Analysis
ZHOU Jian-xin
(Institute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at 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518060)
Casual workers mainly refer to the“freelancing”people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The phenomenon of casual work started during“the migrant worker rush”in mid-1980s.With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employment,casual workers have been growing in number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group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emography characteristics,job,income,daily life,social relationships,social security and assistance of the casual worker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southeast China,the most vibrant economic region in China,we find the casual workers there are economically poor,marginalized in status,“free”in job choice and daily behavior,homogenous and introverted in social relationship,and potentially dangerous.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casual workers,we should start with the issues such as social structure,adaptation issue,and informal relationship.
migrant workers;casual workers;poverty culture
C 912.4
A
1000-260X(2016)02-0035-08
2015-12-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客家文化研究”(12&ZD132)
周建新,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移民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和文化产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