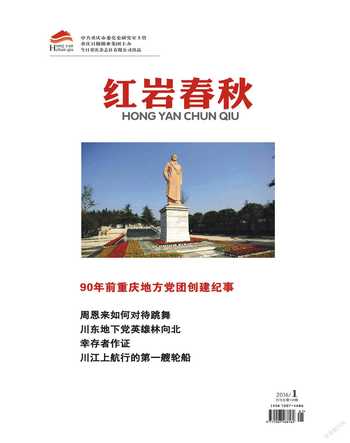歌乐山保育院生活散记
何延贵
编者按:他们的童年时代,正值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中华民族陷入深重危机之时。成千上万的幼小生命,因失去或远离亲人过着流浪生活,处境堪忧。为抢救战区难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及各地建立的保育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在重庆歌乐山建成的保育总会四川分会第一保育院(简称“川一院”,又称“歌乐山保育院”)就是其中一所,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历时最久的保育院。今天,那些在保育院度过了难忘童年的孩子们,已是耄耋之年,但万千思绪不断。为纪念那段岁月,本刊开辟栏目,特选编一系列回忆文章,由亲历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记录成长的时光。
我的童年是在战时儿童保育院度过的。当时日军强占了我中原腹地,到处抢掠、烧杀,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的家也陷入绝境。1938年秋,我刚满8岁,就和小叔、小姑以及两个姐姐离开了河南信阳吴家店的老家,一起被收容进汉口保育院。
我们在武汉只待了几天,便被编为第26批入川难童队,随后乘船沿长江西上,经宜昌、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辗转到达重庆。不久,被分配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四川分会第一儿童保育院(简称川一院)。因院设址在重庆歌乐山,人们通常叫它歌乐山保育院。
美好的环境
保育院位于歌乐山下的高店子古镇旁,那是一座偌大的院落,四周由竹篱围着。一进大门,迎面是一座简易的大礼堂。大院内,右边是错落有序的8排长长的平房,每排平房各有10多个小房间,两头是老师的宿舍,中间住着学生。每个房间有4架双层木床,能睡8人。大院左边也有几排平房,分别是教室、图书馆、医务室、厨房、大饭厅,以及老师们的办公室。不远处,有大片的田园,种植着小麦、玉米、高粱和蔬菜,还有几间饲养房,喂养了猪、羊、鸡、鸭等。
就这样,我们这些从全国各战区收容来的500多名难童,学习、劳动、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并茁壮成长。保育院的同学,除极少数在幼儿班的孩子外,其余都是按正规的小学编班,设1-6年级,每年都有毕业生走出保育院的大门。
当时歌乐山保育院在四川的二三十个保育院中,算条件比较好的。有人说是“示范保育院”,有人说是“贵族保育院”,是当时中外各界人士参观访问最多的保育院。
1940年春,恰逢儿童节前夕,那天阳光明媚,全院师生被紧急集合在操场上,同学们低声议论着今天会有什么重要人物要来。不一会儿,只见刘尊一院长引着3位仪态不凡的夫人走进来,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欢迎大会开始了,刘院长介绍说:“孩子们,今天孙夫人(宋庆龄),蒋夫人(宋美龄)和孔夫人(宋霭龄)来看望大家,和小朋友们共度儿童佳节。”我们掌声不断,兴奋不已。宋美龄以保育会理事长的身份代表两位姊妹表示,愿同学们过一个愉快的节日,要好好学习。宋庆龄是总会顾问,她以极其关切的口吻问候,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奋发向上,立志成才。大家都非常激动,饱含热泪地聆听着。尤其是国母宋庆龄,她那亲切动人的音容笑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1942年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院参观访问。那时美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之一,是中国的友邦,保育院的经费和物资大部分是由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华侨和一些慈善团体募捐的。因此美国要人来访,一定要好好地接待。院内上上下下着实忙乎了一阵子,打扫卫生,美化环境,整理内务,张灯结彩。我们当然也得打扮一番。由保育总会拨来一批“罗斯福布”(即斜纹卡叽布),为每人做了一套结实耐穿、做工讲究的童子军装。这套童子军装后来成为我们保育生的一个标记。
躲日机的轰炸
当年,日本飞机经常对大后方进行空袭,大肆狂轰滥炸。我们三天两头跑警报,生活总不得安宁。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初秋的傍晚,天空黑沉沉的,空气异常闷热,像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突然间,我们听到日机的轰鸣声,有同学大喊:“敌机来了!”我们不知所措,狂奔乱窜,谁也不知该躲到哪里去。慌乱中,我朝着院外的田野跑去,抬眼一看,黑压压的日机达三四十架之多,已经低空飞临到头顶,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眼睁睁地望着日机真的好害怕,我下意识地趴在地上,一点儿也不敢动,心里呯呯乱跳。日机呼啸穿空而过,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算是又过了一道鬼门关。
我们大多是在白天跑警报,每当空袭警报一拉响,同学们便三五成群冲向歌乐山的崇山峻岭,有的躲在树丛,有的藏在山崖夹缝中。那时汉奸活动十分猖獗,日机一到,地面上红色、白色的信号弹就“嗖嗖”地窜上天空,给敌人通报轰炸目标。我们年纪虽小,但对卖国贼的卑鄙行径恨之入骨。
有一天,天空无云,烈日炎炎,我和几位同学在跑警报途中,看见几架日机忽东忽西,掠空而过。远远地,我们发现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躲在一棵树旁,正扯出一面大白旗,不停地向日机摇晃。我们火了,大喊:“抓汉奸!抓汉奸!”那个家伙听到喊叫声,一溜烟地逃跑了。我们四处搜寻,始终没能发现其踪影。让这个坏蛋逃之夭夭,大家气得直跺脚,也难解心头之恨。
童声合唱团的弦律
童年是一首首歌,歌声绵绵不绝耳。从我进入汉口保育院,到被送往大后方,不论是走在大街上,坐在轮船上,或逢各种集会,总是能听到激昂的歌声,如《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黄河颂》等。歌乐山保育院建成不久,就组建了七八十人的合唱团。那时,我和大姐何延珍、二姐何延珉同住保育院,都被吸收进了合唱团,这事还被老师夸奖过。
每周课余时间,合唱团都要进行两三次排练活动,并经常在院内外的各种集会、联欢会和晚会上进行演出。一次,我们到附近的一所荣军医院为伤病员进行慰问演出。在露天广场上,面对和我们同样流落在外、受苦受难的伤兵大哥哥们,我们满含热泪、充满激情地唱着《慰问伤兵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等歌曲。唱着唱着,台下不时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声,我们越发唱得慷慨激昂。我们的歌唱不仅博得了阵阵掌声,更激发了听众对日寇的仇恨和抗日救亡的决心。
在歌乐山保育院,高年级的班级每月都要竞相出刊、出壁报,登载国内外大事,交流同学们的学习心得。我们的级任老师特别注意发挥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注重儿童动手能力的培养,采取了轮流编排出报的办法。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在一个深秋的晚上,级任女老师周泯,一位灵气秀丽的大姐姐,专门把我叫到她的宿舍里,鼓励我把这期壁报办出去。老师的信任使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微弱的桐油灯光下,我匆匆地编排、抄写。老师在一旁耐心地指点,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做标题,怎样剪裁,如何突出中心,怎样安排版面。时间长了,周老师还以茶水、点心款待我,我也更有兴致了,一直忙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壁报如期张贴出去,看到自己的学习收获和劳动成果,真是快乐极了。
歌乐山保育院里有各类教学设备,在当时算是比较齐全的。院里有图书馆,房间很大,收藏了不少儿童读物,供师生借阅。还有阅览室,摆着各种报刊、杂志。在课外的时间里,我总爱去翻阅,由此得到启迪,既增长见识,又增添了生活乐趣。
师生情谊深
重庆一带,雾气大,夏天时间长,气候又潮湿,到了5、6月以后愈加闷热。我们这些下江人(重庆人称呼来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由于水土不服、清洁卫生又不好,入院不久,几乎人人都感染上了疥疮。这种皮肤病的传染十分迅速,全身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红疙瘩,痛痒起来十分难受。
全院的老师和医护人员全力以赴,想尽一切办法进行防治,帮助挑破水泡,挤出脓水,点上药水和贴上药膏。平日,大家勤洗勤晒衣被,喷洒药水,忙个不停。如此反复,经过两三年时间,全院才算控制住病情。我也被这种讨厌的疥疮折磨得够呛,多亏老师们的爱心和细心,终于给治好了。
在歌乐山保育院生活的日日夜夜,老师们照料我们的起居饮食,教导和陪伴我们成长。与我们同甘共苦的老师们,只有不多的几位中年男先生,更多的是20岁左右的女先生。她们就像大姐姐一样,思想进步,朝气蓬勃,并且多是从当时的抗日战地服务团转来的,其中不少人还是共产党员。正如《保育院院歌》歌词中写道:她们同我们一样,“离开了爸爸,离开了妈妈,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老家”,但她们把全部的爱心给予了我们,默默地耕耘在伟大的儿童保育事业上。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老院长曹孟君,她为儿童保育事业呕心沥血,竭尽一切地做了那么多好事、实事,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美好,让我一辈子难以忘怀。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