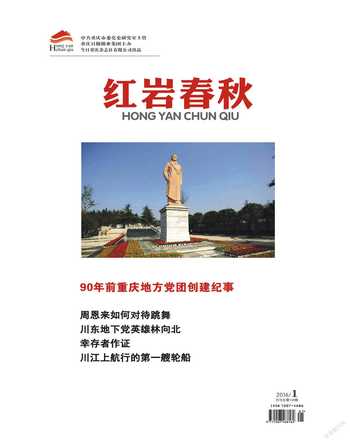90年前重庆地方党团创建纪事
简奕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中国近代社会矛盾及人民革命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是四川地区社会矛盾和人民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实现了党对全川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也掀开了重庆历史崭新的一页。为纪念中共重庆地委成立90周年,本刊特推出系列特稿,以缅怀革命先辈、感悟创业艰辛。
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僻处西南的重庆,开始有了一些共产党员的分散活动。但是,重庆的建党活动,却是从团组织的创建开始的。在党组织建立以前,团组织长时间代党工作,发挥党的作用。其间,重庆团组织开展国共合作,领导重庆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并在大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开始了在重庆的普遍建党,最终迎来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创建。
在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
历来被世人称作“天府之国”的四川,僻处内陆,交通闭塞,长期处于封闭型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和割据型的封建军阀统治之下,在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的发展都较沿海缓慢。因此,无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展,乃至建党建团,四川都相对落后。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爱国运动中,四川人民不居人后。有关五四运动的详细报道在5月16日传到四川后,学生们立即奋起响应,以成渝两地为中心,在全川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后的短短两三年中,四川人民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包括四川自治运动、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重庆裁兵运动等一系列以反对军阀专制,争取民主政治为主要形式的斗争中,展开了以拯救中华为目的的伟大探索。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在重庆蓬勃发展,社会上的文化思潮空前活跃。1924年出版的《重庆商务日报十周年纪念刊》这样描述道:“当此人心激昂,举国骚动的时候,四川的新闻界,以及一般舆论,也就非常感动鼓午起来,如服了兴奋剂一般,一变以前沉默态度,而为一种热烈奋发的样子;与各省取一致,以学生为后盾、攻击政府之外交政治,反对日本之侵略行为;提倡文化,鼓吹自治,高唱民权。……四川当时新出的日报、月刊、季刊、杂志、不定期刊……等出版物,也就风起云涌的出现了。”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广泛传播,为建团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主要有3种途径:
一是当时川内川外的各种新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0年以前,四川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了解,主要还是通过《新青年》一类的进步刊物来获得。1920年以后,各种宣传新文化、介绍新思想的刊物在四川纷纷创办,外地的各种新文化刊物也通过各种途径相继涌入四川,“四川人人羡慕新思想,容纳新思想,要算二十二行省中第一。就以各种出版物说,如《新青年》《新潮》《新中国》《每周评论》,四川一省的总数都占外省的第一位”。新文化刊物在四川的大量涌现和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都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寻找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是先进分子出川带回革命真理。那时的四川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寻求真理的愿望非常迫切,不少人选择外出探索: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四川青年就有两三千人;1919年初至1920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热潮中,我国共有1579名爱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四川有名在册的有472人,居全国之冠。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回川的同时,也带回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留在外地的也通过信函往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王右木是四川举起共产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他留学日本时曾广泛接触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回国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开始转向社会主义。1920年暑假,王右木到上海考察,会见了陈独秀等人,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发起到成立及上海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1921年春,王右木在四川首建马克思读书会。他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为阵地,创办《人声》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团结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从俄国归来的王维舟也在家乡宣汉县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创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吴玉章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期间,在校内培养革命力量,组织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在他周围团结了从日本归国的杨闇公等一批革命青年。
三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物纷纷来川活动。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恽代英、邓中夏、黄日葵、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的活动家、宣传理论家先后来四川活动,促进了共产主义的传播,为四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种子。1921年夏,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中夏、黄日葵应邀来重庆参加“暑期讲演会”进行讲学,在重庆青年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讲学会结束后,邓中夏留在重庆,领导了四川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反对封建教育的“择师运动”,到10月,才返回北京;1921年10月恽代英应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之聘,从武汉到四川泸县川南师范任教,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川南师范学生于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萧楚女来到四川,先后在重庆、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并担任《新蜀报》主笔,经常撰写引导青年革命的文章,积极从事青年运动。
通过种种渠道,马克思主义在四川广泛传播开来。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分子在探索中确定了自己的方向,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自觉地运用初步掌握的革命理论开展各项活动,积极投入和领导工人运动和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建立了重庆及四川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的创建
先建立共产党组织,再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团的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地方组织的普遍规律。但重庆的情况却较为特殊,是党员先建立团的地方组织,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团组织“以团代党”,发挥领导作用,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党的地方组织。
1922年4月,共产党员唐伯焜受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托,回到重庆,在重庆联中任教员并负责主持和联络筹建地方青年团组织。他与此前回渝的共产党员周钦岳一起,联络各界进步青年如董宝琪、李光斗、李守白等10余人。10月9日夜,唐伯焜、周钦岳、董宝琪、李光斗、李守白等人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重庆地方团成立时,共有团员10人,书记周钦岳。但是,当时在重庆地方团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唐伯焜。
会后,重庆地方团立即向团中央报告成立情况,并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予以正式承认,建议团中央与地方之间应该密切联系,注意加强各地方团之间的团结;同时,还决定立即着手组织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重庆支部等组织,以便更好地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和更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其在重庆地区的影响。当月30日,团中央承认了重庆地方团的成立,此后,又陆续承认了成都和泸县地方团的成立。
重庆团组织是四川地区最早成立的为团中央所承认的正式团组织。重庆地方团成立后,重庆其他地区也陆续开始了建团活动。1924年6月,在成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邹进贤回到綦江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团员,于1925年1月建立了綦江第一个青年团支部;1924年9月,童庸生发展鞠雪芹等人入团,建立了涪陵团支部,隶属重庆地方团。1925年1月,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也随之更名。2月,重庆地方团派南川籍团员张嘉铭回县开展团务,吸收汪石冥、张庚白、谈如渊为团员,并组建由张庚白任书记的共青团南川支部。到1925年春季,重庆地方团除了在市区的川东师范学校、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巴县师范学校、巴县中学、《新蜀报》等设有支部外,还先后在江北县(今重庆市渝北区)、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永兴场等地建立起了团的支部组织。
随着重庆地方团和各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相继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庆地区已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萧楚女整团
尽管如此,重庆地方团自身仍然存在着严重缺陷,缺乏大规模开展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和实际运动经验;加之重庆地处西陲,不在革命发展的中心区域,同时又远离党、团中央,联络不便,不能获得经常性的指导,使得重庆地方团的活动范围较窄,大都限于组织学习和纪念宣传等,不仅群众性和战斗性不强,且还没有脱离“研究小团体”的状况,大大制约了地方团作用的发挥。
1924年成都“五一”大会以后,一向标榜“超新”的军阀杨森逐渐暴露出反革命面目,大肆排挤知名革命者,廖划平、杨闇公等被迫先后离开成都前往重庆。这时,四川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王右木也牺牲在为革命奔波的旅途中,成都党、团组织骤然失去了优秀的领导人,作为全省革命中心的地位日渐丧失。客观形势的骤变,历史性地把重庆团地委推向了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地位。
但此时重庆团组织的状况显然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最严重的问题来自于组织内部。尚处于初创阶段的重庆团地委不仅组织较为涣散,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团员人数较少,总共才40余人,工作局面难以打开。特别是重庆团地委的主要筹建人唐伯焜组织能力较弱,且常不参加会议和活动。1924年初,团中央批准重庆团地委改选,新当选委员长(书记)的何星辅是个“江湖中人”,而任秘书的范英士竟没有入过团、入过党,甚至不知自己已“当选”,由此可见其草率;且当时重庆的团组织也大都是“学生团”,成员常因寒暑假回家或升学就业退团、脱团而去,整个团的组织活动实际陷于半停顿状态。更突出的问题还在于团地委内部不团结、内耗大,先有王右木与童庸生闹矛盾,以致分道扬镳;之后,童庸生到重庆参加重庆地方团,双方又将矛盾延续到工作中,进而影响到成渝两地团的团结,使全川团组织力量受到削弱。
恰逢此时,四川地区出现了一件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吕潘缔约”事件,后经团中央查实,“缔约”属于潘学海个人行为,与当地团组织无关。“吕”是吕超,国民党在四川的重要人物,一直跟随孙中山,时任熊克武“讨贼军”的第一路司令;“潘”是潘学海,曾是重庆地方团的团员,后来在南川县(今重庆市南川区)工作。两人在叙府(今四川宜宾)缔约,其主要内容是潘学海会同成都、重庆、泸州3处地方团向吕超请求每月接济100元,补助每个工作人员每月5元。这显然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等于把四川的主要地方团组织变为了国民党的附庸,完全违背了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事件发生后,了解情况的萧楚女及时向团中央进行了反映。1924年9月1日,团中央作出严厉处分,决定解散成都、重庆、泸县的地方团组织,委派萧楚女作为驻川特派员,授予他“调阅文件、教育同志、整顿组织之全权”。10月,萧楚女受团中央委派来渝,指导重庆团地委进行初步改组,撤换了唐伯焜,改由罗世文任秘书、杨砺坚任组织、何薪斧负责农工。
在萧楚女对重庆团地委组织整顿过程中,最大障碍来自于原主要核心成员唐伯焜、杨砺坚等人的抵制。唐伯焜是重庆团组织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但他把团内任职看成是“必我终身任事之势”,对外来的萧楚女采取了不少排斥甚至攻击的做法。童庸生等骨干也在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和主观性,特别对萧楚女此前应聘为军阀杨森秘书和出任《新蜀报》主笔之事提出责难。尽管这种指责毫无道理,但由于唐伯焜等人的煽动,不仅加深了童庸生对萧楚女的误解,甚至使杨闇公亦对萧楚女表示不满,认为萧楚女是在搞“权利事业”“排除异己”“意图破坏本团”。这使得本来就充满危机的重庆团地委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为尽快扭转局面,萧楚女忍辱负重,敢担责任。经过观察与调查,他了解到,团中央决定解散重庆地方团的根据主要是“与国民党缔约问题”,而事实上这一问题完全是潘学海的个人行为,与重庆团组织毫无关系,重庆团组织多数骨干成员是值得信任的。于是,萧楚女决定相机化解他们对自己的误会。
1924年11月19日,日本帝国主义在重庆肆意制造了“德阳丸案”(1924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德阳丸”号载运成色低劣的银毫抵达重庆,用武力抗拒海关检查,并打伤前去查验的人员,还将其中4人抛入江中——作者注),由此激起重庆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为发挥重庆团地委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萧楚女迅速率领重庆地方团投入运动,因势利导地领导民众开展反日斗争。在这场反帝斗争中,原本对萧楚女怀有成见的杨闇公等人,因革命信仰及反帝反封建立场一致而站到一起,他们捐弃陈见,并肩战斗,共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通过这场反帝运动,重庆地方团摆脱了“研究小团体”的羁绊,从此成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同时,也使重庆地方团与萧楚女加深了彼此了解,逐步统一了认识。
1925年1月,重庆团地委进一步改选,由经验更加丰富和老成的杨闇公任组织部主任代行书记职务;童庸生先是代理组织干事,后代理宣传干事;罗世文改为负责学生部工作。“一月改选”是重庆整团结束的标志,从此,重庆团组织迈入了一个新的广阔天地。
领导和推动四川大革命运动
在萧楚女整团之际,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洪流正涌入巴蜀大地。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给新改组的重庆团地委提出新的课题,即如何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正在开展的大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使更多的人在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动员更广大的民众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萧楚女和重庆团地委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一是加强宣传活动。重庆团地委发动全体团员深入城乡各地开展宣传演讲活动。根据团地委的要求,团员们每周都要外出演讲,每个团员均须分头轮番出去演讲,以周末、节假日和集会游行为最多。1925年2月,重庆团地委组织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会员们,利用旧历新年期间做了3次形势演讲,还利用国民会议促成会名义欢送出席全国国促会代表,集合14000余人举行游行。除此之外,团地委组织力量到城乡各地张贴反帝反军阀标语,组织规模空前的50余支演讲队,进行6天5夜的演讲,以及组织4万多群众参加街头游行。在重庆团地委的组织下,党、团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以及团地委创办的机关刊物《爝光》周刊也在重庆地区的传播逐渐扩大,对革命理论的宣传得到扩展。
二是加强组织活动。当时,萧楚女在加强对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思想宣传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在工人中开展革命理论的宣传。他除了以《新蜀报》为主要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工人当中,运用生动比喻和具体事例等工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杨闇公也经常出席一些学会和演讲会,向工人讲解剩余价值及唯物史观等问题,对提高工人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贯彻团中央关于加强工人运动的指示,重庆团地委于1925年2月设立了农工教育训练委员会,并增设了团的工人支部。同时,重庆团地委还通过吸收工人参加团的外围组织和免费入夜校学习等方式,在广大工人中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工人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三是加强建党工作。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对类似重庆这样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地区提出了明确要求:“为着扩大党的数量,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为此,团的三大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也作出相应规定:在“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根据党、团中央的两个决议案,重庆团地委承担起一项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任务,即代党发展党员,筹备建立党的组织。1925年3月,重庆团地委着手从团员中发展党员,杨闇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四是领导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1924年11月19日,骇人听闻的“德阳丸案”发生后,引起重庆各界群众极大愤慨,军阀政府反而向日本道歉,并不准将此事登报,不准群众团体、学校师生介入,妄图掩盖证据。惨案发生后,萧楚女立即在《新蜀报》上以“匪石”和“寸铁”为笔名连日发表长篇专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同时,重庆团地委在萧楚女、罗世文、杨闇公等人的带领下,迅速领导民众开展反帝斗争。11月27日,重庆团地委组织了46个群众团体在巴县图书馆召开大会,成立了“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在萧楚女等人的支持下,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提出“不经过各级官厅,由人民直接进行国民外交”,并鼓动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分头邀请各校师生一致力争。12月8日,“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发表第二次宣言,提出“德阳丸案”中的犯罪日人应即按照中日领事裁判条约,由两国官宪会同审判治罪;“德阳丸案”中的犯罪华人,应即要求日领事依法引渡,交中国官厅办理;受伤落水之海关查验人员,应由日清公司给予相当之损害赔偿;取消德阳丸船主在长江一带航业界之服务资格;日本领事向中国国家道歉;日本领事保证该国商船以后不得再有此等贩币殴人之行为等6项强硬主张,要求当局接受,并表示“不达目的,决不休止”。13日,重庆各界群众7000多人,高举“外抗侵略,内肃官方”的旗帜,在打枪坝举行群众大会。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捣毁了省长公署。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迫使地方军阀政府不得不撤换了重庆海关监督,日本也被迫调回了驻重庆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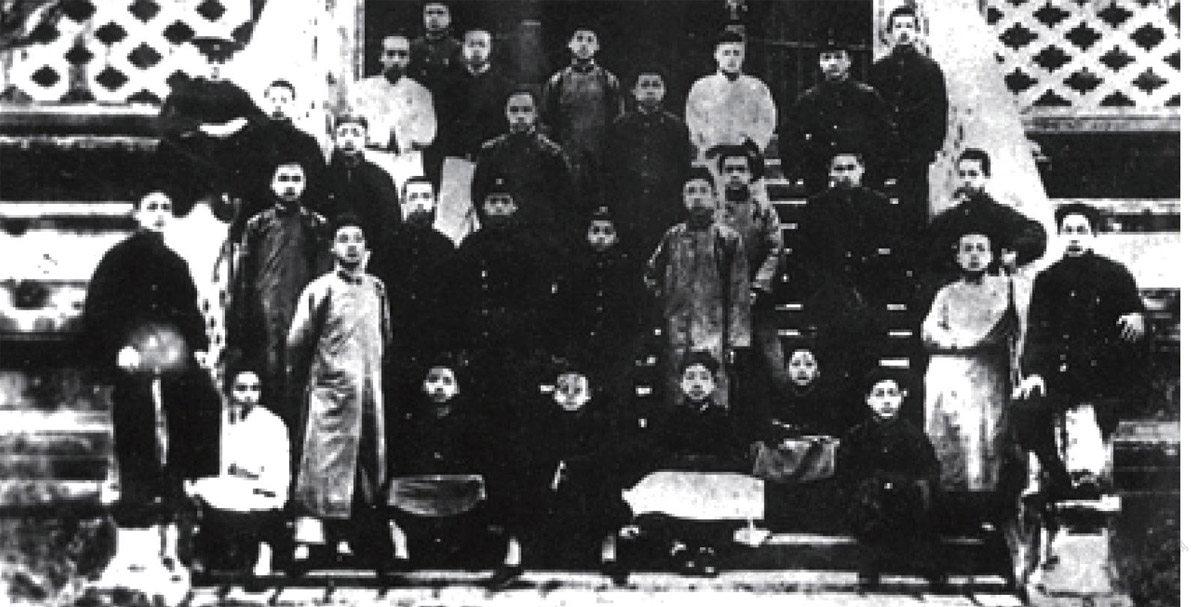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号召劳动群众组织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推动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以期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重庆团地委积极响应号召。1925年1月16日,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杨闇公当选为总务部副主任,直接领导运动的开展。2月27日,重庆团地委又组织1万多群众欢送重庆赴京出席国促会会议的代表,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广大市民的斗争热情。
通过一系列的斗争,重庆团地委在重庆地区的影响和声望日趋高涨,成为了这一时期领导四川地区革命的核心力量。重庆团地委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做的大量开创性工作和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重庆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