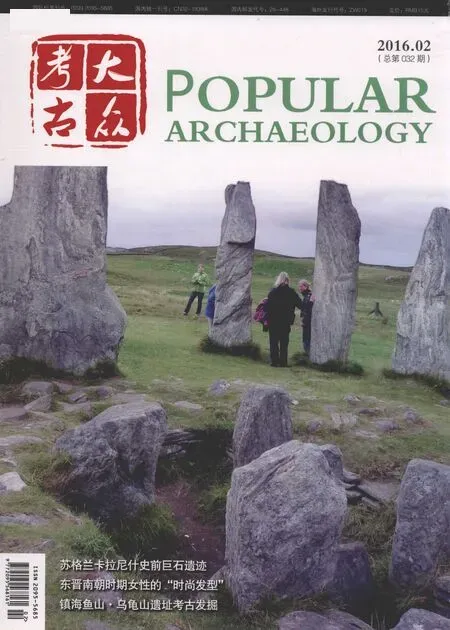陕西榆林石峁遗址的发现历程
文 图/魏唯一
陕西榆林石峁遗址的发现历程
文 图/魏唯一

石峁遗址皇城台远眺
相较于近年来石峁遗址考古的“石破天惊”,其实石峁文物的流散已逾百年,散见于世界各地的公私收藏,其价值与蕴意或明或暗,但皆难以真实揭示。这一“姗姗来迟”的“石破天惊”,在古董商与鉴赏家眼中悄然无痕。草灰蛇线,有迹可循,经过考古学家的“循循切近”,石峁城址最终得以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图景之中。
石峁是陕北榆林市高家堡镇的一个村庄,位于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坐落在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的交汇处,其地表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石峁村风俗不奇、景致寻常,就连地表延绵的“石墙”也为世代村民见怪不怪,只是“田间”、“墙头”偶见的精美玉器,附丽着奇异传说,在村民间口耳相传、津津乐道。
地不爱宝,石峁隐遁
晚清至民国年间,在石峁村一带出土玉器的消息不胫而走,为古董商贩竭力收罗、待价而沽,并以“榆林府古玉”的名义辗转流散,少量为金石学家著录,更多的玉器则为国内外公私机构收藏。例如20世纪20年代,时任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代表的美籍德国人萨尔蒙尼(A.Salmony),在北京购得榆林府农民出售的牙璋等玉器40多件。1949年后,不法文物商贩仍旧接踵而至,暗自盗掘,一批又一批的石峁文物流落民间。在百年流散历程中,石峁玉器背后隐藏的“石峁秘密”随着时间转逝,几经易手而日益模糊,绝大多数玉器早已失去自己的真实“身份”。
依据最近的调查统计,榆林地区民间收藏石峁玉器约2000余件,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广东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及台湾震旦文物研究会等均于不同时期获藏石峁流散玉器。由于历史原因,海外亦有多家博物馆和个人藏有石峁玉器,包括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日本白鹤美术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人类学博物馆及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等。大批文物流落民间乃至流失海外,足可想见许多有价值的考古信息已经永远消逝,每每说起此事,石峁考古队员们难免痛心疾首。

石峁遗址位置

石峁母亲河——秃尾河

萨尔蒙尼

石峁文化研究会藏品
伏脉千里,寻访石峁
20世纪70年代年,陕西省文管会戴应新先生根据神木县高家堡公社提供的线索,对石峁村进行了初步考古调查,征集到一批极具特色的陶器及上百件精美玉器。戴应新先生先后发表《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調查》、《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等文章公布了此次调查资料,并认为石峁是一座内涵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从此石峁遗址正式进入考古界的视野。
80年代初,西安半坡博物馆对石峁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试掘,发现了房址、石棺葬和瓮棺葬等遗迹,且出土了一系列有确切层位关系的遗物。据巩启明先生回忆,那个年代陕北生活异常艰苦,经常食不果腹,由于条件所限未能有机会做进一步大面积调查、发掘。借助这批考古资料,陕西考古界主张石峁遗存是陕西龙山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
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智荣先生继续对石峁遗址进行踏查,征集到石器、陶器和玉器标本40余件。在此之后,陕西历史博物馆、省文管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管办、神木县文化馆及高家堡文化站等多家单位多次对遗址进行过复查。
2009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罗宏才教授对石峁遗址开展考察,并公布了一批特征明确、造型独特的石雕与石人像,数量达20多件。

石峁遗址调查

石峁石砌城垣分布
科学考古,石城现世
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三方联合组成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2011年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考古队将传统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相结合,采取区域系统调查、遥感影像分析、全覆盖式钻探和重点发掘等方法,最终确认石峁遗址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史前石构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组成。“皇城台”为石峁遗址的中心区域,面积20余万平方米;依据山势围绕皇城台的一重石墙为“内城”,面积约为210万平方米;内城东南再扩筑半圈弧形石墙为“外城”,面积约为190万平方米。此外,在石峁遗址周围还发现了类似“祭坛”的石砌建筑遗迹。
为解决石峁城址年代问题及进一步了解聚落布局和功能区划,2012年5~11月,石峁考古队对外城北部的一座城门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因其位置在城址中部偏东,故称“东门遗址”。
外城东门遗址建筑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由“外瓮城”、南北两座石包夯土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马面及角台等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曲尺形门道连接,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东门城址位于最高点,位置险要,地势开阔,鸟瞰整个石峁城址。这一发现将整个东北亚地区土石结构城防设施的出现时间提前了数千年,并表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前夜,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伴随着频繁的战争。
惊喜还在继续,在城门早期地面之下发现7处头骨坑,埋葬的头骨每坑大致为24颗,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靓副教授鉴定,死者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种种迹象清晰表明,城址营建过程中存在奠基活动或祭祀仪式。此外,在倒塌的护墙里发现有精美玉器,显示了古人尚玉辟邪的观念。《竹书纪年》有云:“夏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晏子春秋》也有记载:“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璇室、玉门”。石峁遗址城门墙体中的葬玉现象,或许与文献中记载的“玉门”、“瑶台”相关。形制完备、结构清晰的墙垣是石峁先民防守外敌的军事屏障,那么玉器、奠基头骨坑的发现则暗示石峁统治者的精神期许。


玉钺

东门遗址墙体中出土玉器

结构清晰的外城东门
紧接着考古队员又在内瓮城的一段墙体下发现了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墙体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和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颜色鲜艳,图案精美,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见方。日本学者饭岛武次认为中国唐代才出现的压印起稿技法,被这一发现足足提前了两千多年,系古代美术考古及艺术史的重大发现。
石峁城址的发现犹如石破惊天,随即得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2013年1月石峁遗址考古发现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4月石峁遗址考古发现获得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在上海举办的世界考古论坛上荣膺“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人头祭祀坑

揭取壁画

后阳湾F2出土鳄鱼骨板

韩家圪旦遗址航拍
循循切近,文明重光
2012~2014年,石峁考古队对石峁城址内的居住区和贵族墓葬区ü ü后阳湾、呼家洼、韩家圪旦地点进行了发掘。在后阳湾遗址居住区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骨骼等遗物,可辨器形者包括鬲、斝、豆、盉、三足瓮等龙山晚期代表性器物。在众多动物骨骼中,还惊喜地发现了鳄鱼骨板,为陕晋中北部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首次发现。在此之前,陶寺遗址M3015以及清凉寺遗址M54、M82、M146均出土鳄鱼骨板,上述墓葬都是高等级墓葬。鳄鱼骨板应与鼍骨相关,是身份等级的象征,特别是陶寺遗址M3015一度被认为是“王墓”。因此,后阳湾遗址出土的鳄鱼骨板反映了石峁聚落的等级制度,为探索高等级墓葬与房址提供了线索。
在发掘韩家圪旦遗址的过程中,考古队员逐渐认识到石峁城址在埋葬制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婴幼儿使用瓮棺葬,葬具系日常使用陶具;青少年使用石棺葬,葬具系打制石块拼接而成;成年人使用竖穴土坑葬,并有木质葬具;高等级贵族墓葬中随葬有玉器、青铜器,乃至存在着殉人。

图① 贵族墓葬M1(殉人) 图② 石棺葬 图③ 瓮棺葬图④ 清理竖穴土坑葬
2015年,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步入转型期,进入樊庄子遗址发掘和城址内部功能区划的重点复查阶段。塞上六月风飞沙,时常刮得人睁不开眼,一天工作下来,嘴巴、眼睛、耳朵及鞋里全都是沙子,大家虽然面带倦色,但是心中满怀探索的激情与乐趣。
7月的陕北,烈日炎炎,酷暑难耐,80后执行领队邵晶和4位90后研究生组成的调查小队,开始对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ü ü“皇城台”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皇城台八阶护墙上的菱形眼纹装饰图案,共两组三只,砂岩质地,制作规整,全部嵌入石墙。其中较大的一组宽约30厘米,高约18厘米,东西间距28厘米。较小的一组位于其上方约60厘米处,宽33厘米,高约15厘米,因墙体塌陷,另一只被破坏。两组石眼均是在修筑皇城台北墙时嵌入而成,虽历经千年风雨,在巍峨坚固的石墙上,“菱形眼”依旧炯炯有神。此次调查确认了皇城台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ü ü宫殿区,由宫殿基址、墩台建筑和大型房屋等构成,雄伟壮观。“皇城台”的建造过程中除了追求防卫功能,也显示出威仪万丈、震慑众生的气魄。

调查皇城台

皇城台菱形眼纹

石雕人面像

石峁外城构造图及石雕人面像出土位置
在调查皇城台区域的同时,考古队员又在外城东门遗址南侧五号和六号马面间的坍塌石堆中,发现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石雕人面像,石料大致呈长方体,略有残损,周身打磨痕迹明显,人面轮廓为竖向椭圆形,内刻眼、鼻、嘴,古拙中透露出生趣。
8月10日是难忘的一天,考古队员在对东门遗址北墩台外侧护墙进行考察时,意外发现了一件玉钺,平置于错缝砌筑的石墙缝隙之间,上下间涂以草拌泥保护。这件玉钺仿佛见证了世人探访石峁的漫长历程,等待合适的日子“面世”,与考古队员分享石峁的故事。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又是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村民忙着细数田里的收成,石峁遗址今年的野外工作也将结束。从2011年的区域系统调查到2012、2013年对外城东门及内城居住区的规模性发掘,再到2014年对韩家圪旦贵族墓葬群的揭露与认识,及至今年的调查与发掘,使我们再次确认了石峁城址是一座龙山时代中晚期的高等级中心聚落。队长邵晶常常说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还年轻,要做的还很多。”我时常在想,我和石峁也许是一场华丽的邂逅,我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而她会一直矗立在塞外之巅。A

东门遗址石缝中出土玉钺

执行领队邵晶在刮面

金秋的收获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执行领队邵晶先生帮助,谨致谢忱!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硕士研究生)
——石峁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