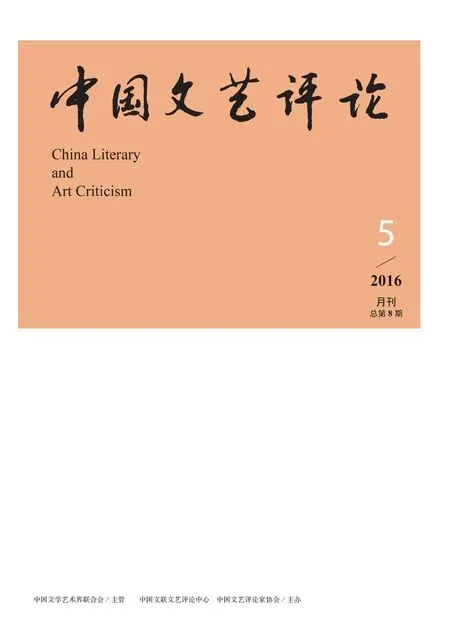长征题材美术创作的观念与手法
郑工
长征题材美术创作的观念与手法
郑工
2009年完成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和财政部三家单位组织实施,以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乃至改革开放以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内容[1]该选题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拟定,并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复同意后,正式公布实施。2005年工程启动,2009年组织验收,共有104件作品。参见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办公室编《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从《虎门销烟》《圆明园劫难》直至香港、澳门回归等,其中也包括了红军长征的题材,如《遵义之春》(中国画,吴山明等作)、《长征》(油画,王希奇作)、《红军长征的将领们》(雕塑,王洪亮作)、《彝族结盟》(雕塑,曾成钢作)等。2009年前后,国内各级部门还组织了不少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也推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作品,特别是各省区组织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将这一主题性美术创作推向深入。红色区域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活跃。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在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创作观念,与建国前十七年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艺术表现方式上又有怎样的特征?两对关键词指的是“角度与片段”及“细节与气氛”。
角度与片段
对于历史题材,很多人认为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当中,尊重客观事实,还原历史。所以,作者接到创作任务后都会“进入”史料、反复阅读、认真领会、了解史实。接着,他还得寻找自认为适当的方式,尽量去除主观成见。这里,就出现了创作者的视角问题。比如同一题材的美术创作,亲历者和后来者的视角很不同,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其视角也不相同。那么,哪个视角更为贴近历史的真实?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是强调亲历者的经验,眼见为实;其二是强调历史的客观性,避免主体意识过多的干预和偏见。而且历史学者大多认为,亲历者的经验可以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是历史研究的珍贵素材,而后者是历史的陈述。
1951年,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1]李伯钊(1911-1985),四川重庆人。1925年到上海,1926年冬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闽赣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10月,李伯钊在江西瑞金随部队开始长征,任中央工作团团员,曾“三过草地”。1951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大型歌剧《长征》,其剧作者为李伯钊,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之后,李伯钊又将其改编为话剧,八易其稿,于1982年完成并上演,名为《北上》。,这属于亲历者的作品。与音乐、戏剧界不同的是,有关长征题材的美术创作几乎都是后来者的作品,没有亲历者参与创作。 2013年由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书系《延安文艺档案·延安美术》,共9册,包括延安美术家、美术组织及美术作品。[2]郑工主编《延安文艺档案☒延安美术》,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该项目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共9册,包括《延安美术家》(上、下)、《延安美术组织》《延安美术家》(上、下)、《延安美术作品—综合》(上、下)、《延安美术作品—木刻》(上、下)、《延安美术作品—漫画》(上、下)。在组织编撰的过程中,我发现延安的美术骨干大多是30年代上海新兴木刻运动的美术青年,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陆续来到延安;亲历长征到达延安的美术家非常少,如黄镇,留下了一本长征途中的速写[3]黄镇《长征速写》,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该书由上海风雨书屋初版于1938年,作者误署名为萧华,题《西行漫画》,收入红军长征路上的速写25幅,其中有红五军团团长董振堂的画像。1958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时,经萧华本人核实,作为佚名作者画册。黄镇(1909-1989)在长征时任红五军团文化娱乐科科长、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在长征途中画有速写约四五百幅。,后来他就不从事美术创作了。新中国成立后从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美术家,如从延安过来的胡一川、罗工柳等人,有亲身的经历,也有时代生活的经历。胡一川画《开镣》有生活体验,因为他蹲过国民党的监狱;罗工柳画《地道战》,他虽然未去华北平原,但他抗战时在太行山生活与工作,更何况画了《毛主席在延安作整风报告》,这也是亲身的经历。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征题材的美术创作上,就未见亲历者的作品。如李宗津的油画《强夺泸定桥》(1951年)(图1)、艾中信的油画《红军过雪山》(1957年)、罗工柳的油画《宁死不屈》(又名《前仆后继》,1959年)及另一幅油画《毛主席在井冈山》(1961年)等等都属于后来人的创作。这就构成我们讨论的一个焦点,即后来人的历史叙述与当代视角的关系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历史事件,那些事件又如何纳入美术家的视野?

图1 强夺泸定桥 李宗津 油画210×300厘米 1951年
建国以来有关重大历史题材或者跟长征有关的历史题材创作,可分为两大阶段,以1979年为界。上述作品皆属于1950年至1979年这一时期。罗工柳他们的创作又属于这一阶段的前期,此时中国画画家傅抱石还依据毛泽东长征的诗词进行诗意画创作,如《清平乐·六盘山》(1950年)、《强渡大渡河》(画面立意取自《七律·长征》诗句“大渡桥横铁索寒”,1951年)、《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1958年,图2)等。后期出现了沈尧伊、何孔德等人的作品,如何孔德的油画《古田会议》(1972年)和《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1975年)。1974年,中央军委还组织画家高虹、何孔德、彭彬等人重走长征路,画了一批写生作品,于1977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画册《长征路上写生》。沈尧伊也于1975年用三个月时间重走长征路,回来后创作了油画《遵义会议会址》《革命理想高于天》与《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阶段基本上沿用的是英雄史观指导下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注意典型化的处理方式。到了1979年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在21世纪,美术家们重新看待这段历史时的视角就不一样了,而且以前回避的一些问题和事件也浮出水面,被遮蔽的历史也重新得以关注。

图2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傅抱石 中国画139.5×81厘米 1958年
长征路上的湘江战役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题材。这一战役很惨烈,是一场历史的悲剧。五昼夜的激战过后,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从哪一个角度表现这一战役是对画家的一种考验。军旅画家张庆涛花了五年时间画了一幅《湘江之战·1934》,把它作为一个悲剧性的题材进行刻画,他认为,要画湘江,要画出中国革命壮烈宏大的悲剧性!悲剧性不一定是史诗,但所有的史诗一定具有悲剧性。从欢呼胜利到面对悲剧便是视角的转换。接着还有一些更具体的问题需要考虑:如何表现悲剧?如何表现历史的挫折?如何揭开历史的伤痛?实际上,这些思考都基于当下的政治现实以及当代人的理解与体会。毕竟,艺术创作需要想象,而想象的空间则是由个体建构的。
所以,紧接着的问题是“如何让历史进入当代”。比如,这些年不少地方都组织画家“重走长征路”,重返那些革命遗址与遗迹采风、写生并进行创作。美术家们表现什么?是如实地对待眼前的景物,再现遗址遗物,还是将画家当下的感受灌注到对象的形式或形象的表达上?同样都是遗址遗迹的写生,我们可以参照1974年何孔德等人长征路上的作品与2009年戴士和等人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支持下所开展的“伟人足迹写生”作品,两相比较,就必然推出两个概念,即“大视野”与“近距离”。何孔德他们是“大视野”,画面的空间阔大,有近景、中景和远景;而戴士和他们的画面往往是一景一物,或一些玉米,或一把椅子,一张毛泽东用过的桌子(图3),都是静物,这也是近观,细看视点很集中,迫在眼前。虽然都没有涉及到人物与事件的表现,却因为观看方式的改变,对象的呈现意义就不同了。前者偏向于客观性,后者偏向于主观性,而这主观性内容又通过客体的外在形式进行表达,连同形色的意义主体对物微妙的感受结合在一起,个体性问题比较突出。戴士和认为,这是现场感,让对象还原到素材的层面上,进而打开人的想象空间。这也可以看出两代人观看方式中的时代差异。

图3 毛泽东在瑞金用过的办公桌 戴士和 油画120×120厘米 2009年

图4 而今迈步从头越 沈尧伊 油画180×338厘米 1976年

图5 娄山关大捷(《转折》三联画之三)沈尧伊 油画 300×300厘米 2008年
同一作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题材进行再创作时,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呢?还是以沈尧伊为例。他在1975年至1976年创作的油画《而今迈步从头越》(图4),画面的主体是毛泽东,形象十分高大,并带领着一批中央红军翻越娄山关,画作采用了一种历史叙事和形象象征相结合的手法。但在2006年至2008年,他又创作了油画《娄山关大捷》(图5),画面完全两样,毛泽东的形象不再出现了,表现的是两军交战,且是伏击战。胜利者与战败者易于区分,但不突出个体,只是给予红军的群体概念,完全进入历史的叙事,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在历史事件当中以冲突与牺牲表达悲怆的集体英雄主义,为无名者树立墓碑。我们可以从画面的分析,激发人们思考新的问题,包括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主体的或远或近,其直接的作用是什么?是宏观叙事抑或微观叙事?历史想象的空间是否因为时间关系被一步步地放大?等等。
历史是被不断阐释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复现了历史,而在于你从哪一角度观看并述说历史。叙述者的主体意识控制着每一时期的历史复现,并决定历史复现的面目。或者说,历史的复现就是当代精神的某种折射,是当代创作某种范式的体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其范式特征是什么?即采取中心构图,强调戏剧性冲突,预设高潮,注意聚焦式的观看,体现古典的英雄史观。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术创作中的英雄史观已被消解,一种平行的视角不断出现,并影响着历史的叙事方式。譬如,强调“场面”与“阵势”、“细看”与“近观”,以线性的扩展方式构筑内在的叙事逻辑,注重推论及前后相续的关系,有着非中心化的倾向。
再看一个例子,全山石1961年创作的《英勇不屈》表现的是井冈山时期赤卫队的斗争,与他2009年与青年教师翁诞宪一起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相比较,二者虽然题材不同,但表现的都是英雄主义的悲壮主题。在形象塑造上,出现了主要英雄人物与群体形象的对比关系,也出现了象征性金字塔构图与叙事性平行构图的差异;局部的凝望转换为全景式的鸟瞰。观看方式的转变导致表现方式的变化,而表现方式的改变则意味着艺术观的变化。

图6 陈独秀与《新青年》 胡伟 中国画 246×617厘米 2009年
除了“观看”之外,还有“片段性”问题。美术创作的个体性很强,因为艺术的独创性要求,迫使艺术家要独具慧眼、别出心裁。这种个性的表达,不仅在于个人的风格与手法,更在于观看的角度,即从什么方向看,又以怎样的心境去看待?你想看到什么又看到了什么?这里,“悬念”出现了。“片段性”问题就在此观看的“悬念”中产生。任何一种历史的呈现都是片段性的,何况与视觉的观看密切相关的造型艺术,无论在空间维度或时间维度上,都不可能有太大的延展。所以,空间片段或时间片段的前后暗示历来备受关注。但在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作者往往沉浸在“事件”中,而不注意观看:“形象” 变得不重要了,“瞬间”的选择也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却是“事件”本身及个体的期待。那么,个体对“事件”的看法必然影响对片段的表达;或者说,作者所沉浸的“事件”肯定不再是一个具体发生的事,而是在期待状态下转换为连续性历史行为,其零散化的表达方式不可避免。
在片段性问题上,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继续提问。第一,单一人物形象本身只是这一事件的承载者,为什么多人物的组合能构成一段历史的陈述?胡伟在谈他创作中国画《陈独秀与〈新青年〉》(图6)的心得体会时说:“一个人只露出一个头,一个人只露出一只脚,或者一个人的眼镜镜片在闪光……”。[1]胡伟:《把历史带到今天——〈陈独秀与《新青年》〉创作谈》,《美术》2009年第2期。他就是用这种片段的拼接组合方式,构成一种新的历史叙述。第二,寓言或象征性的形象处理往往是片段式的,如何在事件的陈述中扩展人们的阅读空间?同一画面空间的分化与隔离,最终会落在事件的时间维度上。可见,“位置”并不是单纯的空间问题,它会在人物之间寻求事件的关联,构筑时间的历史流程。第三,人物作为事件的主体依然存在,但其主体性在事件的陈述中已被质疑或已然消解。画家并不追溯事件的起因,而注重表现事件的过程,关注事件中的主角及各个人物的表情。表情成了事件中人物叙述的着眼点,也构成阅读中的片段性因素。事件的意义就在这种阅读中产生,而事件主体、创作主体及阅读主体的关系也被重设了。第四,叙事与象征在整体事件的陈述中如何妥善地处置。避免单一性的陈述,注意形象内涵的深刻性,构图中的排列问题在此时可以凸显出来。
细节和气氛
在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细节确实变得越来越重要。张绍城说他在描绘《淞沪会战——十九路军》一画(图7)时,曾经思考他“笔下上海的街道究竟要损毁到什么程度”。[2]杨斌、徐沛君:《图鉴历史 再谱华章——部分参加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美术家谈创作》,《美术观察》2009年第10期。而且他一直在寻找叙述材料,如南方特有的斗笠(十九路军的主体是广东人),画了一只、两只、三只,直至第七只。他通过细节的表达,使每一只斗笠都不一样。他又画了南方人特别喜欢的水烟筒、上海街头常见的黄包车、战斗中倒下的战士、街道上垒起的沙袋、成堆散落的弹壳……如此种种,在黎明前寂静的上海街道、黑暗中通过各种物件的质感所表现出来的各个细节,都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在画幅三分之二处构成一条缓缓移动的中心阅读地带。作者没有放弃任何一处细节的叙说,但也在控制着一种一张一弛的叙述节奏,在看似一般化的处理方式中,令作品深入人心,触及一种人人都可感悟到的情感。

图7 淞沪会战——十九路军 张绍城 油画205×380厘米 2009年

图8 湘江之战·1934 张庆涛 油画 218×469厘米 2009年
如果回到长征的题材,我们还可以比较张庆涛的《湘江之战·1934》与沈尧伊的《湘江之战》(《转折》三联画之一)。它们为同样的题材,也同样地关注细节。张庆涛的《湘江之战》(图8)细节在哪?就在一群走在前方的战士:他们的脸部表情和身体动作,褴褛的服装,被硝烟熏染的皮肤,或背负伤员艰难前行,或抬着担架运送伤员。细节的真实表达具有一种现场感,让人如临其境,但它的力量并不仅限于此。作者没有通过这些细节的描绘去强化“伤残”与“败走”,而是在战士沉重的脚步中看到他们在困境中崛起的坚强意志,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一束奇异的光打在队伍后排的中间部位,照亮了毛泽东,而画幅左边昂首嘶叫的战马,以及画幅右边双手叉腰站立的周恩来,平衡了整个画面。画家正是通过细节叙述这一历史事件。如果没有细节从何谈论叙述的生动性?有意思的是,这支队伍的主体是那些冲锋陷阵的战士,毛泽东、周恩来的位置并不那么凸显,但并没有因为这些位置的调整而改变他们作为引导者和精神领袖的形象。因为只有他们两位是实写,有名可查;其他都是无名的战士,可为虚写。这种虚实关系没有因为细节的问题而受到影响。这幅画作,张庆涛从2005年画到2009年。沈尧伊的《湘江之战》(图9)也创作于2006年至2008年。两幅画的创作时间很接近,但构思的距离却很远。沈尧伊画面的主体是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在湘江上空盘旋轰炸,强行过江突围的红军队伍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那是一支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队伍,没有火炮,也看不到什么英雄壮举。也许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但过江的队伍如同一股潜流横穿湘江,江面上因飞机的投弹激起的水柱冲天而起,水雾弥漫,硝烟四起,动感很强。一般情况下,静止瞬间有利于细节的刻画,细节又与图像呈现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但如何描绘运动的瞬间呢?细节的陈述如何穿插,情节展开的合理性何在?沈尧伊的画回答了这些问题。细节在图像的呈现中最有利于披露“事实”,或者说,最有利于让读者相信这就是“事实”本身。

图9 湘江之战(《转折》三联画之一) 沈尧伊 油画300×300厘米 2008年
我们总以为“事实”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在历史画的创作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就在事实,而且往往是在“艺术”的名义之下。比如,我们通常将对细节的过度重视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态度,将其视为非艺术的。尽管在“事实”面前,有时“艺术”会显得十分矫情。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并不平衡,因为等同是没有意义的。在人们的理解中,艺术的真实性应大于历史的真实,反之也没有意义。艺术的矫情在于再现事实的时候,用“应该如此”取代了“原本如此”,用普遍性替换了特殊性,用“美的”掩饰了“真的”,用“号召”取代了“记忆”。我们通过艺术难道仅仅想了解历史的事实?抑或是了解历史的事实必须通过艺术?不,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在事实的基础上给予人们以精神的力量,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艺术创作本身也是一次历史的写作,对作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尊重“事实”,从而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然而艺术的品质往往在于细节:不仅在于对象物的细节,还在于艺术形式自身的一种细节。比如,中国画善于用线条表达,在绘画的语言表达上可以称之为单线陈述,因为那些线条在勾画过程中能将各种心理因素融合进去,并形成一个新的叙述。这里的细节就开始摆脱图像的限制,向单纯的形式问题回归。如2009年王有政、杨光利创作的《纺线线——延安大生产运动》(图10),画面完全用白描的线条构成,不加一点渲染,也不上色,各种人物动态表情都融汇到线的陈述中。细节很丰富,线条的质量也很高。作者通过线的交错穿插、长短疏密,将人们的视线引入画面,令观者既阅读了形象,又依据线的运动及表情了解了整个事件。不经意间,“情节”退却了,留下的是线的陈述——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线条表达。如此一来,对“事实”的考证也就流落在个别的材料上,如衣饰、发型、纺车及其他一些道具。图像的客观呈现或线的形式陈述都离不开细节,但细节的独立意义何在却不是每个人都认真思考的。在形式叙事中,细节的客观性被主体指定,而这种形式的指定性使形式本身陷入细节的相关讨论,并为一种情绪所笼罩。譬如线的“平铺直叙”方式,既有形式本身的意味,又带入相关的情绪,而情绪随着细节的展开,表现出特殊效果,不夸张不生硬也不做作,虽然这样不容易出现激动人心的场面。如韩书力的《高原祥云——解放西藏》一画,虽有晕染上色,但画面构成的基础还是线条,其平易朴实的语言状态更亲近历史本身,一方面去除意识形态的遮蔽性,另一方面为艺术家自我的“表达”寻找新的空间,在形式语言层面而非观念层面上体现其创作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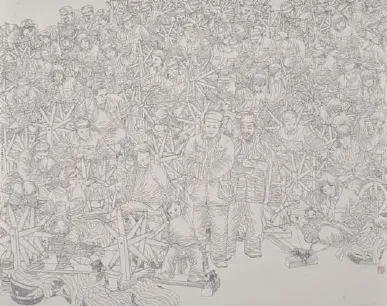
图10 纺线线——延安大生产运动 王有政、杨光利 中国画260×330厘米 2009年

图11 残日·1937年12月·南京 许江、孙景刚、崔小冬、邬大勇 油画360×900厘米 2009年
细节之外还有一个“气氛”问题。在战争题材的创作中气氛如何重要,与细节之间的关系如何调整?对此每人的理解并不相同。创作《血战台儿庄》(2009年)的徐青峰认为,“画战争题材和其他的创作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的细节显得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气氛’的把握,整张画的气氛是否能感染观众,是重中之重”。“在大场面的真实战争场景中,个人只是其中一个点,大片的是青灰色的硝烟——这是我了解到战争的真实。如果把其中的一幕搬上画面,会像一张灰色调的风景画。”[1]《就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作品——〈血战台儿庄〉,作者徐青峰答记者问》,《潍坊日报》2009年9月20日第4版。回到场面的问题上,我们可以联想到一片战火纷飞、
腥风血雨,渲染气氛有助于整体性的观看,但绘画依然还需要细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充实画面、丰富内容,让事件中的各种“事实”得以呈现。如许江等人集体创作的《残日·1937年12月·南京》(2009年,图11)就注意到大场面的氛围与多层叙事的关系。画面的整体是一个大坑,硝烟蔽日,被捕的中国民众以及士兵都被赶到坑内,周围站着入侵的日本兵,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就在此进行。氛围的营造有助于历史叙事的整体语境,而一个个细节的展开,如人物的动作、表情以及道具,都会构成叙事的具体要件。无论是那些已经死去的或正在面对死亡的人,都体现了一种民族大义。没有细节的呈现,何以体现画家对这一事件的认识。
当然,也有一些画家将细节的问题转化为肌理性的语言,以此融入到画面的气氛当中。比如,战争过后留下的一片废墟,其自身就存有一种悲剧性的力量,被摧毁的东西留给人们一片遐想。不少历史画作者追求的是再现历史的真实,而有些历史画家却在历史的遗址面前以自我感受去追踪历史。历史的痕迹,或者说,物的痕迹与画的痕迹相互迭换,如蒙太奇般的切入或跳开,在人的视觉印象中不断错置,形象不断地抽离,形式上出现了虚化和雾化的现象。如陈树东、李翔的《百万雄师过大江》(2009年),画面完全依靠气氛,一种用油色肌理营造出的特殊氛围,表现1949年解放军横渡长江时的壮观场面。千帆竞发,船上的士兵只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谈不上什么形象的塑造,画面上是满目帆影以及被炮火激起的水柱。作品中的绘画性被强调了,个人手法突出了,“事实”陷入到肌理性的细节中,所陈述的“事件”也被弱化了。章晓明、周小松创作的《抗美援朝·激战》(2009年)也是如此,表现了一次攻占高地的战斗。激战过后,阵地上布满尸体,层层堆压,胜利的旗帜在硝烟中飘扬。作为历史事件的那场战斗显得不重要了,我们不需了解那是上甘岭战役抑或其他,我们看到的是战争严酷的事实,想到的是战争与人的生命之关系。当然,事件本身的弱化并不意味着历史陈述的退却,而只是其陈述的内容变化了。
当历史事实成为造型艺术的材料时,个人的艺术创作手法,是不是分别往两个方向发展。在个别问题上寻找个别的解答方案,或以代言的方式让事实出走,从而流放他乡。前者的主观意识更为强烈,形式更为多样,不拘一格;而后者貌似客观,也不过是将主体意识隐藏在事物的表象背后,让客体出场,手法多写实,倾向于叙事性或象征性的表达。
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玉雯)
- 中国文艺评论的其它文章
- 文学的魅力是什么
——专访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