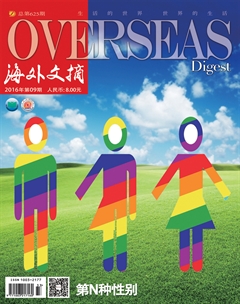我们时代的自恋流行病
托比亚斯·贝克尔++刘黎
自恋狂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骂语,自恋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精神障碍。同时,自恋也是人类过上快乐、充实生活,取得成就的必要前提,是出现伟人伟业的推进剂。
前国际足联主席约瑟夫·布拉特几周前介绍自己的传记时,这样谈及他辞职时的心情:“我承受着痛苦,耶稣也承受着痛苦。但现在我又恢复正常了。”
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大毒枭、墨西哥人乔奎恩·古兹曼在最后一次越狱时,有了两个疯狂的想法:第一个是找人拍摄一部讲述他英雄事迹的电影,并亲自挑选制片人和演员;第二个是接受演员肖恩·潘为《滚石》杂志进行的长达7小时的采访。这次会面被警方获悉后,他又坐进了监狱。
职业自行车手兰斯·阿姆斯特朗曾被问到,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什么,他的回答并不是“我服用了兴奋剂”,而是“我重回了竞技场”。2005年他第七次赢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卫冕次数史无前例,接着却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认为自己是个无辜的英雄。2009年他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就算我不服用兴奋剂也能轻松甩在后面的人赢得比赛”。阿姆斯特朗复出后被揭露是个兴奋剂违规者,他的7次冠军头衔均被剥夺。
瑞士主持人、媒体企业家和曾经的德国SAT1电视台商业经理罗杰·沙温斯基在他的新书中讲述了这3个小故事。书名叫《我是最大的——为何自恋者会失败》。书中主要讲述因自负而陷入灾难的男人们的故事,比如德国足球界的杰出代表弗朗茨·贝肯鲍尔,为德国成功取得了2006年世界杯的主办权,现在却涉嫌行贿;托马斯·米德尔霍夫,贝塔斯曼教育集团和卡尔施泰特万乐百货邮购集团前董事会主席,由于背信弃义和逃税锒铛入狱;让德意志银行走向深渊的自大狂约瑟夫·阿克曼,他让访客在他的办公室外等待数小时,只为展示自己的权威。沙温斯基写道,在我们的社会中,自恋的种子四处蔓延。
不管是男女老幼,沉溺于自己世界的自我中心者、自怜自艾的自封“首领”都不胜枚举。他们出现在电视、网络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真人秀和选角秀中,在闪光灯下。在社交网络中,图片分享网站Instagram的用户每天分享8000万张图片,其中无数张都关乎数字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自我。
整形外科的候诊室在2015年迎来了比前一年多出约10%的顾客量,目前有约六分之一的德国人选择在健身房中塑造形体。为完成自己的新畅销书《新领域》,作家伊尔迪科·冯·库尔提为自己的脸注射了玻尿酸和肉毒杆菌,洗了肠子,参加了咀嚼训练,甚至还去了修道院,并表示有人希望她在那里留下来。可以说,她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专门打整自己。《新领域》是一本以无所不在的自我吹嘘为主题的“照镜子式”文学作品,是一份来自自恋社会的自恋报告。
还有其他来自“我!我!我!”现代世界例子吗?比如 C罗。这位足球明星是个狂妄的天才。他这样回应来自对手粉丝的嘲笑:“我有钱,又帅,球也踢得倍儿棒。没有其他理由。”又比如饶舌歌手坎耶·维斯特。他为自己的一张专辑取名为《耶稣》,他的新专辑名为《巴勃罗的生活》,在美国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上,他感觉自己待遇极差,于是私下说过这样的话:“他们都疯了吗?伙计,我比斯坦利·库布里克(美国电影导演)、巴勃罗·毕加索(西班牙画家)、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哥伦比亚大毒枭)的影响力都要大50%,不管是生是死,都不例外,而且接下来1000年都不会改变。”
还有唐纳德·特朗普。他的办公室位于纽约闪闪发光的特朗普塔中,里面摆放了一面大镜子。如果有人问他欣赏谁,钦佩谁,他的回答是:“我欣赏镜子中的自己。”美国《名利场》杂志曾评价他为“短手指的粗俗家伙”。他的回答是:“我的手指很长,很美,我身体的其他很多部位也一样。”
和作家沙温斯基的预期不同,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坎耶和C罗都还没有失败。但是他们都是自恋者。特朗普打破了所有预言,成为了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他的很多政治对手认为他不仅自恋,而且病得不轻。
傲慢、虚荣、自私,或好自我表现,自恋、利己,容易陷入病态,喜欢贬低批评者的人,简单地说,一个非常不讨人喜欢的人,如今被认为是自恋者。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学诊断如同自恋这样深深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今,除了“你个纳粹分子”之外,很难想到还有比“你个自恋狂”更大的侮辱——或者其实也有,比如“你有自恋型人格障碍”。
这是一个既看不见同情,也不崇尚团结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们可能知道自己的病态。有的人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祸根,有的则将之归咎为该死的因特网。只有一点是明确的:一个由自恋者组成的社会注定走向毁灭。
爱上自己倒影的美少年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提出“自恋传染病”“自我的一代”“自我膨胀”等表述,并表示,“如同中世纪的瘟疫一样”,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流传很难得到控制。瑞士精神病科医生格哈德·达曼认为自恋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精神障碍”。
但是,自恋究竟是什么?这个概念源自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耳喀索斯。他是水泽神女利里俄珀被河神刻菲索斯强奸后生下的孩子。全希腊的男男女女都热情追求美貌的那耳喀索斯,但是他拒绝了所有人。没过多久,他的高傲就和他的美貌一样广为人知。有一次,他在池塘中看到了水中的自己,马上就爱上了自己的倒影。他日日夜夜在岸边徘徊,越来越绝望,因为这美丽的倒影无法回应他的爱。当他试图亲吻它时,他掉进了水中,淹死了。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那耳喀索斯的形象还是正面的:古罗马人戴着刻有他形象的首饰,以表达他们对爱的需求。这一点随着基督教的诞生发生了改变,基督教宣扬博爱,因此用质疑的目光审视那耳喀索斯的自我之爱。直到19世纪末,自恋这个词才流行起来,最初用来指一种一般认为肮脏不堪的性爱好——自慰。
几年之后,精神分析法创立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才真正让这个概念变得有名。他区分了原生自恋和次生自恋。原生自恋是指每个婴儿完全关注于自己的正常健康的精神状态,而次生自恋是指人们为安抚自己缺失的自我价值感,而回到幼儿时期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状态的一种精神障碍。
1979年,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克里斯多夫·拉什在自己的辉煌著作《自恋时代》中严厉批判了自恋现象。他的很多想法,例如对当时而言全新的通过瑜伽和纯天然食物实现自我的观点,或是对变老和死亡带来的恐惧的思考,直到今天读来都还有借鉴意义。我们在约40年后的今天谈论自恋时,这本书仍是个典范。
两种自恋者
如果在《明镜周刊》档案中查找曾被记者视为自恋者的著名人物,可以发现一张长长的清单。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意大利前总理)当然常常被提及,此外还有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前希腊财长)、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前德国财长)、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前德国国防部长)、金·卡戴珊(美国名媛)、乌利·赫内斯(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前监事会主席)、若泽·穆里尼奥(葡萄牙籍足球教练)、阿尔扬·罗本(荷兰足球运动员)、帕丽斯·希尔顿(美国社交名媛,演员,希尔顿酒店继承人之一)、肖恩·潘(美国演员)、爱德华·斯诺登(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朱利安·阿桑奇(泄密网站“维基解密”董事与发言人)、尼古拉斯·伯格鲁恩(慈善家)、安德斯·布雷维克(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行凶者),像这样的还有很多很多。
但是您注意到什么了吗?
他们几乎全是男人——除了金·卡戴珊和帕丽斯·希尔顿这样的声名狼藉的名媛。奥地利精神科医生、畅销书《自恋陷阱》的作者莱因哈特·哈勒宣称,在这本书出版后,他收到了约5000封信和邮件,其中70%都是女人写的,她们相信:“您描写的正是我的伴侣!”只有5%的男人写道:“我的伴侣就是这样。”其他25%是认为自己的大部分男性领导是自恋者的男女雇员。如果是在弗洛伊德时代,人们会说:“这女的究竟想干嘛?”但是现在,人们说的是:“这男的疯了!”
“男人确实更容易有自恋行为,”哈勒说,“他们更可能处于掌握权力的位置,因此也更容易实现这一点。”此外,男性的自恋行为更让人讨厌,因为他们往往更富攻击性。约70%的男人都有自恋型人格障碍,这是自恋的最极端病态形式。
但哈勒的同事达曼表示,关于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是围绕“男性的自恋”展开的,因此有方法论上的问题。它源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拉什发表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学著作,提出了“自恋人格特征清单”,这是社会心理学家们迄今仍在使用的确定一个人是否有自恋倾向的一份问卷。美国精神病科协会的分类系统DSM被认为是明确区分健康和患病的精神病科圣经。当自恋型人格障碍第一次出现在该系统中时,自恋这个主题算是在研究机构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自那时起,处于研究中心的就常常是出现在男人身上的外向、坚定、自大的自恋。只要他们是极度自恋者,他们就是傲慢、自负、有野心、独断、阴险的。可以说,他们就是以往我们所说的大男子主义者,凭自己的意志、喜好行事,毫无同情心、团队合作精神等如今大受欢迎的品质的家庭和企业大家长。他们的自恋主义散发着睾酮的味道。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内向、敏感、脆弱的自恋,它更常出现在女人身上。这种自恋至今很少得到研究。精神分析师巴尔贝尔·瓦尔德茨基以此为主题写了《女性的自恋:对获得肯定的渴望》一书。“男性很容易自吹自擂。”瓦尔德茨基说。相反,自恋的女人却常常羞怯内向,很容易感到伤心,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吃了亏。她们用美丽和纤瘦来平衡自卑心理,因此容易患上饮食障碍。
对于自恋出现的原因,有两种理论:童年时获得的肯定太少或太多。自恋者童年时需要努力在父母、周围人和自己面前扮演一个完美的形象,以争取爱和肯定。这和古希腊那耳喀索斯的传说不谋而合。那耳喀索斯是强奸后出生的孩子,因此很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缺失父爱,母亲也会以矛盾的目光看待他。第二种理论出现得更晚:自恋者得到了太多肯定,被围绕着他团团转的直升机父母所溺爱。心理治疗师瓦尔德茨基说,被宠坏的孩子也是孤独的,他无法真正了解自己是谁,认为世界需要他这个超级英雄。
不久前,德国《时代周报》为特朗普的卷宗加上了“美国最大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标题,并讲述特朗普的父亲弗雷德有多严厉。在儿子唐纳德又一次翘课之后,弗雷德把他送进了一所军事学校。在那里,小唐纳德必须站得笔直,接受咆哮的退伍军人的惩罚。那所学校的校训是:获胜不是最重要的,它是唯一重要的。
心理学家认为,有些职业的人尤其容易患上自恋型人格障碍,例如顶级银行家、顶级运动员和杰出政治家。在选举日当晚,政治家们出现在电视里,对哪怕最差劲的选举结果做出解释。他们不能失败。此外还有所谓的拿破仑情结,即小矮子可能拥有的过剩虚荣心:列宁身高165厘米,施罗德174厘米,普京170厘米,萨科齐165厘米,贝卢斯科尼164厘米,梅德韦杰夫163厘米。
在书中,沙温斯基提到了气象专家约尔格·卡其尔曼,他曾邀请后者录广播节目。沙温斯基说,卡其尔曼非常有魅力,也很健谈、幽默,是个“外向的阳光男孩”,很受大家喜欢。但是他还有另外一面:一旦没有达成自己的愿望,他就马上开始吵吵嚷嚷,变得粗鲁而伤人。沙温斯基认为卡其尔曼就是个自恋者。在终于洗清了困扰自己多时的强奸嫌疑之后,卡其尔曼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用高明漂亮的污蔑中伤去平衡公众影响,正是这种自大的态度阻碍了他的重新发迹。在卡其尔曼的世界里,只有一个标准:不能无条件支持我的人,就是我的死敌。
极端自恋者热衷于嘲笑他人,却从不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嘲讽。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是个自恋者,他派人建了一座有1000多个房间、一个清真寺和一个核掩蔽所的宫殿,而且控告了一个德国讽刺作家,而不是对他开的玩笑一笑置之。上文提到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也是如此。沙温斯基在书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2015年5月,7名国际足联官员在苏黎世贵族酒店巴尔拉克酒店被捕。沙温斯基邀请当时的国际足联新闻发言人瓦尔特·德·格雷戈里奥来上他的脱口秀节目。在节目的最后,沙温斯基请他讲个他心中的全苏黎世最好的笑话。格雷戈里奥只犹豫了一小会儿就开了口:国际足联主席、他的秘书长和新闻发言人坐在车里,谁开车?停顿了一会儿后,他揭晓了谜底:警察。观众笑了,而布拉特炒掉了格雷戈里奥。
网络:和世界等大的展览厅
我们的社会似乎一致将自恋视为一种缺陷,甚至一种精神障碍。当然,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已经受够了某些利己主义的领导者之苦,可能还会受特朗普或普京这样的潜在精神病患者折磨。但是,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马丁·路德不也是一个自恋者吗?亚伯拉罕·林肯?穆罕默德·阿里?列奥纳多·达·芬奇?大卫·鲍威?如果没有这些自恋者,人类能有今天的面貌吗?自恋不也如同恐惧一样是一种推进剂,能够创造伟人伟业吗?

2014年奥斯卡颁奖礼上的好莱坞明星
而且,网络真的是将数字化一代变成自私自利怪物的机器吗?美国作家约纳坦·弗朗茨恩在宣传自己批判因特网的小说《无罪》时曾说:“网络是促成自恋者形成的最大工具。”但是如果网络只是帮助达成完全可以理解的日常需求——例如曝光度和共鸣——的工具呢?
长期以来,自恋行为都是富人和权威的特权,只有他们可以在公共场合大声责骂别人,夸耀自己,赢得听众。可能正因如此,几百年来,除了自恋艺术家的自画像外,主要是统治者的肖像占据肖像画艺术史。如今,借助手机摄像头,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能为后世留下自己的形象,而且可以将这些照片挂在和世界等大的展览厅——网络中。在脸书、Instagram、Pinterest上,自恋者向世界呼喊:“看这里!我在这里!这就是我!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怎么看我?回答我!”
“谁是百万富翁?”等猜谜节目,“德国寻找超级明星”和“全德超模大赛”等选秀节目,“单身汉”和“超级减肥王”等真人秀节目,“烹饪大王”等美食选秀节目的出现,和“自拍”现象的盛行“相得益彰”。没过多久,出现在电视上的人,就比坐在电视前的观众更多了。“透过摄像头,在演播室的聚光灯下,在观众的关注中,曾经的无名小卒通过展示自我,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心理学家马丁·阿尔特迈尔在他的《寻找共鸣》一书中这样写道。阿尔特迈尔引用了城市规划师格奥尔格·弗兰克1998年在其所著《关注经济学》一书中阐述过的一些著名立论:“他人的关注是所有毒品中最难抗拒的,它让所有其他诱惑都黯然失色。因此,声望比权力更重要,财富在声名面前不值一提。”
但法兰克福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马丁·多恩斯在他的新书中写道:人确实变得更加自恋了,但是他们对此有充足的理由。
“身份认同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心理问题。”多恩斯的同事阿尔特迈尔写道,“这个时代的人们寻求社会反响,展示自己生活的每一点细节,以了解自己是谁,能做到什么,对别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在媒体中展示自我成为一种生存的证明。”可以说,数字现代化时代的身份认同箴言是:我被看到,故我在。
阿尔特迈尔的观点也解释了,为何这么多人毫不关心自己的信息安全。“在寻求他人关注的过程中,人们更倾向于在全世界的网络中留下痕迹,而不是避免痕迹的出现。因此比起害怕被社会监视,他们更害怕被他人忽略。”这种态度令信息安全保护者绝望。
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植根于“婴儿只关注自我”这一设想。现代研究已经推翻了这一点。“婴儿就已经开始寻找母亲的目光,想从她脸上的表情得知自己是谁了。”阿尔特迈尔写道,“他对她微笑时,就能从她的面部反应中了解自己。”成人在社交网络上的行为也相似。自恋心理鼓励他们展示自己,并获得一种身份认同。“自信需要证明,身份认同并不会在静默中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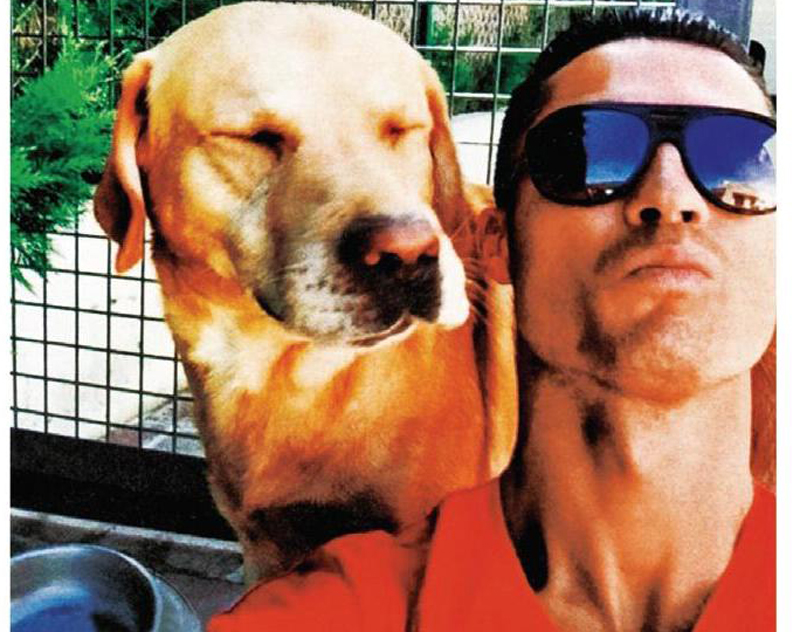
足球运动员C罗
很多关于疯狂自拍的文章都引用了俄亥俄州立大学一项研究的结论:频繁上传自拍照的男性网民尤其容易成为自恋者。容易忽略的是:他们的自恋实际上还处于正常阶段,绝非病态。科学家和记者骂金·卡戴珊和社交网络上的其他自我展示者,也是因为,公开展示自己的思想曾是他们的特权。阿尔特迈尔称之为“自恋式嫉妒”,它正是出现在那些担心在数字现代化时代失去自己在媒体世界中的特权地位,因此反对年轻人的冲击,以捍卫自己固有舞台的学者们身上。他们骂自恋者,正因为他们自己就病态自恋。
自恋带来的优势
如同“我如何看待自己”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的那样,自恋行为广为流行: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比平均水平更聪明,更有吸引力。在很多情况下,这当然都是幻觉,就是从纯数学的角度也可想而知。但是对自己的过高评价能带来巨大优势。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经济学家周意(音译)发现,自恋的艺术家能赢得更高的奖项,开办更多的展览。有自信的人,别人也会认为他更有才。其他研究也表明,波斯尼亚战争的幸存者中,在测试中表现得自视稍高的人,比起那些按实际情况看待自己的人,精神状态要更好。世贸中心恐怖袭击中的幸存者也不例外。大卫·赫尔施莱费尔、安吉·洛夫等经济学家发现,技术公司中的自恋董事愿意为革新投入更多资金,并借助这些革新获得更大的成功。那么,所有人都会受益于个人的自恋行为吗?有时候,自恋也会为集体带来好处吗?可以肯定的是,认为自己很特别的人,往往也能取得特别的成绩。
哈佛医学院讲师、心理学家克莱格·马尔金以这种现象为主题写了一本书,并在书中消除了很多偏见。“自恋不总是负面的,”他写道,“准确来说,为过上快乐、充实的生活,有些自恋行为是好的,甚至是必要的。”认为自己高于常人的人更有领导能力,也更有热情、创造力,因此对别人更有吸引力,他更爱和他人交往,更快乐,往往也更健康,爱情关系也更好。“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写道。相反,那些认为自己是普通人的人,也就是说能够正确看待自我形象的人,更容易患有抑郁症和恐惧障碍。

5月的欧冠决赛上,皇家马德里获胜后自拍的足球运动员托尼·克罗斯
马尔金谈起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的母亲就是我所认识的最了不起,同时也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人。”他写道。她是一个高大的金发女人,富有幽默感,亲切,热心交际。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马尔金越来越意识到她的自我中心主义:她吹嘘自己早年做芭蕾舞者的成就,在交谈中透露某个名人是自己的熟人,为每一道皱纹不安,穿着10厘米的名牌高跟鞋。
马尔金认为,她年轻时,其他人的喜爱和赞赏让她相信自己是特别的。这使她拥有了自信、乐天的性格,充满勇气、活力和热情。所有这些都是他钦佩她的地方。但是当她失去了自己的美貌,丈夫去世,她必须从大房子搬进小公寓的时候,她必须找到其他途径来感觉到自己的特别之处。马尔金这样对自己和我们解释,在这种情况下,那不遭人喜欢的自恋性格,其实只是人类鼓励自己振作起来的一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