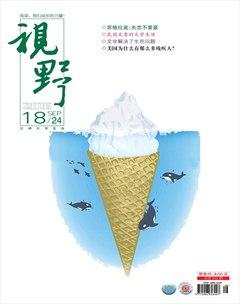山村
大江健三郎
山谷底端的临时火葬场,是一个仅开垦了灌木和草丛、掘起浅层土的简易火葬场。在那里,我和弟弟正用木片翻弄着散发出油脂和灰烬臭味的柔软表土。山谷已被日暮的雾气完全覆盖,那雾气清凉得仿若林中涌出的地下水一般。我们居住的小村庄,坐落在斜向山谷的山腰上。村落四周包围了一圈石头铺设的道路,葡萄色的光芒正倾泻其间。我伸了伸一直弯着的腰,无力的哈欠令口腔最大限度地膨胀开来。弟弟也站起身,在打了一个小哈欠后,冲我微笑。
我们放弃“采集”,将木片扔到繁茂的夏草深处,勾肩搭背地踏上村里的羊肠小道。我们来火葬场搜寻死人的残骨,是为了找到形状合适的骨头,制成佩于胸前的徽章。然而,村里的孩子们业已将这里搜寻殆尽,我们一无所获。或许我有必要把某个小学伙伴狠揍一顿,抢走他的骨头。我回忆起两天前,自己从黑压压并排站立着的大人们腰间,偷看村中的女性死者在这明亮的火焰中被焚烧的场景:她横躺着,挺起肿得像小丘似的赤裸腹部,露出满怀哀伤的表情。我害怕了,牢牢地抓住弟弟纤细的手臂,加快了步伐。如同某种甲虫被我们发硬的手指肚捏住后漏出的黏性分泌液一般,死者的臭气似乎又折返到了鼻孔里。

火葬不得不在我们村露天举行,是因为那段在夏季来临前的漫长梅雨季,由于长时间执拗地持续降雨,洪水便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山崩压毁了我们村通往町(町是日本地方行政区划之一,以人口规模来说,比村大,比市小。另外还指位于市或区以下的小区划)上近道的吊桥,我们小学的分校被封锁起来,连邮件都滞留了。村里的大人们在迫不得已时,才会顺着山脊走上那条泥土松散的狭窄小路,摸索到町里去。因此,向町上的火葬场搬运死者,也便难以想象了。
不过,对于我们村,对于我们这个古老且未经发展的开拓村而言,与町完全隔绝并不会引发切实的烦恼。因为在町上,我们这些村里人如同肮脏的野兽一般被人们所厌恶,对我们而言,所有的日常生活都紧实有致地塞在——这个聚集在一个俯视山谷的斜面上的——小小村落里。况且对孩子们而言,分校能在夏季伊始关闭,也挺不错的。
兔唇站在村口石板路的起点处,怀里抱着一条狗。我一边推着弟弟的肩,一边奔跑在老杏树投下的浓郁树荫之中,同时还窥视了一眼兔唇臂弯中的狗。
“喂,”兔唇晃动的手臂令狗叫了一声,“你看看啊!”
伸到我面前的兔唇的胳膊上,满是咬伤,伤口周围还沾着鲜血和狗毛。咬伤像冒出的嫩芽似的,分布在兔唇的胸口和肥短的脖子上。
“瞧瞧!”兔唇严肃地说。
“你没遵守同咱一起去逮山狗的约定啊。”惊讶和懊恼填满了我的胸膛,“一个人去的吧?”
“我去喊你了呀!”兔唇急忙说,“可是你不在。”
“被咬了啊。”我用手指轻触着狗说道。那条狗鼻翼翕动,露出狼一般的眼神。“爬到窝里去了吗?”
“怕被咬到喉咙,缠上皮带就进去了。”兔唇充满自豪地说。
我清楚地在日暮的紫色山腰和石板路上,看到了喉咙上缠着皮带、全副武装的兔唇,周身在遭受山狗撕咬的同时,从用枯草和灌木搭的狗窝中抱出狗崽的姿态。
“只要喉咙不被咬就成,”兔唇用自信强烈的声音说,“还要等到只剩小狗的时候。”
“我见过它们从山谷里跑来。”弟弟热心地说道,“整整有五条大狗。”
“是啊,”兔唇说,“什么时候?”
“刚过晌午的时候。”
“后来咱就出门了。”
“它白白的,真不错啊。”我抑制住羡慕的尾音说。
“它妈与狼交配过”——兔唇用下流却又现实感满溢的方言表达出这样的意思。
“好厉害啊。”弟弟如梦呓般说道。
“它已经完全和我混熟啦。”兔唇夸夸其谈地说,“不会回到山狗群里了。”
我与弟弟一言不发。
“喂,瞧着!”兔唇说罢,就将狗放到石板地上撒开手给我们看,“瞧瞧!”
可是,我们并没有低头看狗,反而抬头望向那片覆盖住狭长山谷的天空。一架巨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飞机,正以惊人的速度从那里飞过。急剧的声响充斥在波动空气的回音中,短时间内将我们湮没。我们如同被油粘住的飞虫,身体在这声响中一动都不能动。
(由天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饲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