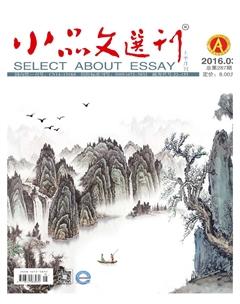世上本无苏州河
安静
悉达多曾经在一条河流之前,听着河水的起伏奔腾之声,望着河水涨落流转,顿悟出世事虚妄与人生虚无,在那昼夜流走不息的河水岸边,悉达多学会了耐心、等待、倾听之术,这些都促使他成为明心见性的般若圣徒,那河水度着他,朝着涅槃之境前行。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最后一天的上海,空气清透明净,雾散,天晴,清寒。我从苏州河上游的古北路桥出发,一路朝东,往着苏州河的终点———外白渡桥,徒步前进。沿着苏州河南岸开始行走,河水沿岸被人为截成多段,某一段河水的边沿被圈入某公园之中,晨练的老人们在寒风中来回行走,为求肉体康健。另一段河水,则成为某高层小区的一部分,被冠以河流景观的商业价值。为了前行,我必须得从南岸和北岸之间转换路径,经过一座座路桥,一点点接近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接地带。
行走过程中,想起一个诗人写过的“我将沿河失落自己”,这如同一个深入骨殖的咒语,在一遍一遍的回荡反复之中,带着自己一瞬间返回少年时,一瞬间又脱离出肉身,从高处俯视我可能会经过的一生,或者成涓涓细流最终干涸,或者化成水汽,消散不见。少年时,一心想来上海求学,未果。多年后,行走在苏州河的沿岸,这才想到时光已经过去十多年。赫尔曼黑塞所描述的悉达多,正是在河水的岸上,想到少年悉达多、中年悉达多和已然白发苍苍的老年悉达多,顿悟这人生从来无有固定的界限,欢乐与痛苦同在,生命与死亡同在,时光的翩跹与流逝,不过只是自己的幻觉。
我不禁想到,如若真如此虚幻,那仅有的真实槃是什么?难道只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佛法涅寂静的道义?抑或是一场人生的苦修,让人放下心中执着,放下贪嗔痴,让这人生在自以为充实的虚幻之中虚幻地度过?再或者,通过人生修炼,能找到凡俗生活中心中的平静安宁,因为这些会让人心中宁静,安然,充满欣喜,接近般若。
在苏州河两岸不停行走,两岸如一帧帧慢速流动的图像,有时候穿过一座桥,一片生鲜活泼的生活画面就带着世俗的喧闹之声,铺头盖脸地涌过来,熙熙攘攘的人群围绕着各种食物,剥离出人存在的最真实的内核———不过是以动物的本能而存在着,吃喝拉撒油盐酱醋;也徒遇一座被隐入干枯树洞中的佛像,人们在佛像面前摆上香火,撒上硬币,这又将生活从最基本的物质本能层面,一下子提升到了精神范畴,但这种精神层面的祷告,不过是对物质生活的另一种方式的求索,依然会落到柴米油盐的层面。而那高于物质凌驾于本能之上的信仰,或许只能从苏州河上那粼粼水光之中寻得些许。
苏州河上有许多材质的桥梁,桥梁将人从此岸度到彼岸,在很多程度上它们跟“路”有着同样的概念,几乎所有往来于桥梁上的人,都会忽视桥下那缓缓流动的苏州河。而平静如镜的河水,正投影着这个城市的面貌,鳞次栉比的高楼,面临拆迁的废弃的民居,被时代摒弃的大烟囱,诸多蓝顶的旧厂房……它是个无比忠诚的镜面,以宁静的神色,照着这个城市的面容。忽而快速驶过一艘监察轮船,让一整条河水,剧烈地摇晃起来,城市所有的投影,都摇摇晃晃地波浪状变形,那变形撕扯的画面,像极了水泥城市的真实面貌。与此同时,被摇晃激荡而起的河水,剧烈地拍打着河岸上的堤坝,响起低沉的浪声,也是在那水声里,弥漫起河流的水腥气,扑进胸腹,河水以凶猛的方式,告知观者,它的诸行无常。
在苏州河的某一段上,它流经光复西路,在此看到一片与城市风景全然不同的破败异常的居民区,从狭窄的弄堂里走进去,弄堂两边的矮房子陈旧不堪,无数条密集的电线与绳索穿插在弄堂的高处,湿淋淋的衣服滴着水,正是十点左右,起床的人在各自的房里清洗,整个灰暗色调的弄堂里,睡眼惺忪的女人拎着痰盂走在清晨的阳光里,某个小角落里,端着一盘花生米搓着花生米外皮的男人,对着盘子吹了一口气,外皮飞起,他就消失在行走的我的眼界之中。弄堂里各种气味陈杂,有爆香的食物气味,淡淡的尿骚味,香烟的味道,一些香火气息,诸多味道柔和成复杂的气息,为这个破败的旧居民区打上独特的标签,当是时,一群信鸽响着哨子从小区上空飞过。在此,生活的活色生香的面容,压过了它的潦倒沉沦的一面,在这里,生活最真实的一面,都在冬日阳光里自在存在。
行走到后来,误入河边一片被遗弃的荒园,园中有第二面粉厂的破旧房子,一片随风摇晃的白色芦苇在水岸上呈现枯态,其中一片荒地里,长着两米多高的荒草的一片土地上,白艳艳的冬日太阳照耀出整个荒园中的阴冷气息,几条眼神不善的野狗在园中奔跑起来,这些都让人感到荒凉,也在心中突然散发出极大的惶恐之感,曾经听闻一个前辈讲,他的挚友曾经在黑夜中的黄河之上渡船游荡,天黑时分,他心中产生出灭亡一切的孤独感,那种孤独让人心中产生极大的恐慌,那个飘零多年的粗狂汉子,在漂流的黄河之上,禁不住自己地大声哭泣。我在荒园中,快速奔跑起来,那种恐慌越来越重,后来我终于知道,那种恐慌是对于未知的危险和潜在的死亡的恐惧,虽然那都是我臆想而来,然而,总归让我这经常独行的人,心中有了保护自己的欲望,这或许是好的。
苏州河蜿蜒曲折,两岸的道路自然也时断时续,在两岸来回,不断向前行走,破败的旧房屋与摩天大楼同时存在,旧时光老调子与时尚气息互相交融,老年人步履蹒跚弓腰前行,年轻人脸上带着恣意的狂放气息,这些都令赫尔曼黑塞所写的语句鲜活起来———“世界在每一个瞬间都是完美的,所有的罪孽都领受神恩,所有孩童都是潜在的老人,所有婴儿都打上死亡印记,而所有的垂死者都必获得永恒的生命……佛存在于劫匪赌徒身上,而劫匪亦存在于婆罗门之上,在极深的禅定中,人可以触摸时间并同时经历过去、现在和将来,于是一切皆善,一切完美,一切即梵。”苏州河穿过的城市中,生活的人类,就在所有的两极之间这般辩证而客观地存在着。
在断断续续的两岸,我走了一些错路,也走了一些绕得很远的路,而代价就是我会让自己走得更加疲倦,这也让我想到人生,按照生活常理,人应该走正确的轻松的路,然而有时候,因为没有导航者,没有指引着,独自行走的人,必然会走在一条自己的路上,错路绕路都会增加人的疲劳感,消耗时间,让接近终点的过程更加漫长,而事实上,在这些绕路上,却会有另外的风景。当一个人在生命里踽踽独行,打着自己的火把,没有人指引,或许,只要不断坚固自己的坐标,一直前行,那个终点总会到来,只是会让人多行走许多路,许多年,甚至一生。然而,终究会因为是自己行走,会让心中有所慰藉。
行至下午,我已经满身疲倦,双腿机械地前行,放弃与坚持在心中争执,最终选择带着一些偏执的坚持,双脚疼痛,我一瘸一拐地独行着,后来看到东方明珠在绕过一个弯道的时候突然闪现出来,心中已然充满欣喜。到达外白渡桥的时候三点二十分,从早晨八点半出发,经过二十来座桥梁,走了不知道多少里路,将近八个小时,我终于抵达。彼时,太阳已然带着夕阳的面容,投射在周围古老的建筑上,让那一天的时光忽然柔软之极。
只是令我惊异的是,曾经苏州河终结之处,河水融入黄浦江,江水会从北至南地流淌下去。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苏州河的尽头,被砌了一道高高的堤坝,将苏州河与黄浦江阻挡开来。这让我想到杜拉斯曾经写过的《阻挡太平洋的堤坝》,她的贫穷坚韧的母亲,曾经用堤坝阻挡太平洋,妄图阻止咸涩的海水淹没良田,最终堤坝依旧被毁,西贡的海岸边,只留下混凝土打造的巨大石块,证明着她的母亲的反抗与失败。只是不同的是,苏州河上竖立起的堤坝,我相信坚不可摧,它会竖立多年,除非再一次被人工摧毁。它让这条河流,从某种意义上被阉割被阻挡,成为一条无法入海的死河流。我站在那堤壩前,往来时的苏州河望过去,上海大楼被太阳染上金褐色光芒,它成为河水的背景,沿着我的视线,河水亮起一道波光点点的亮光,让这条河水,顿时闪烁出帝国斜阳的忧伤,而这,成了它在我眼中最后的镜像。
人类害怕遗忘与被遗忘,给时间编了号,为空间命了名。只是,这世间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而这世间,或许也本无苏州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