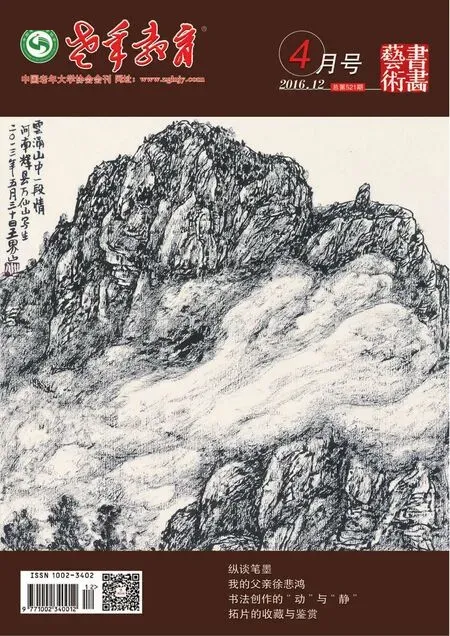我的父亲徐悲鸿
□徐静斐
我的父亲徐悲鸿
□徐静斐

《双骏图》 徐悲鸿
1929年11月20日,南京正值初冬。这天,母亲蒋碧薇陪我外祖母戴清波、舅舅蒋丹麟去明故宫游览,由于乘坐马车来回颠簸,回家吃晚饭时,她便感到肚子痛(此时,母亲怀孕已7个月)。当夜爸爸便将妈妈送进鼓楼医院,整整一天,孩子生不下来。一位德国医生检查,说因胎儿受震动已脱离胎盘,且胎盘在前,胎儿在后,必须动手术。爸爸听了医生的话,急得脸色都变了,忙问医生:“有没有危险?”医生说,动手术可保全大人,小孩靠不住,如不动手术,大人、小孩都有危险。爸爸听后,只好在动手术的医疗单上签了字,不安地在手术室外等待着。晚上9时半,医生终于从母亲的肚子里把我取了出来,当时我的体重只有4磅,而且一声也不会哭。为了抢救我这个早产儿,我被4个热水袋团团围住,奶从滴管里一滴一滴地滴进我那不会吃奶的小嘴里。我便这样奇迹般地活了下来。3天后,我会吃奶了,而且吃得很多,吃了就睡。后来爸爸开心地对我说,你生出来时,还没有家里养的猫大。爸爸为我取了个美丽的名字lily(丽丽),在外文是百合花的意思,他希望他的女儿能像百合花那样洁白无瑕。
1932年,由几个朋友资助,为我家在傅厚岗6号盖了一幢楼房。于是当年年底,我们便搬进新居。楼下左边是一间阳光充足的大画室,右边是一间饭厅,一间客厅;楼上两间卧室,爸爸妈妈住一间,我和哥哥住一间;三层小阁楼上则住着我的大表姐程静子女士;楼后的一排木平房,是男女佣人刘妈、坤生和同弟住。
搬入傅厚岗后,爸爸在家时间较过去多了,只要不去“中大”上课,便在画室作画,一画就是几个小时,画的国画将整个画室地面都铺满了。我们经常等他吃饭,菜饭热好又凉,凉了又热,他都不出来吃。他的脾气是作画到入神时,谁也不能惊动他,一定要把那幅画画完才罢休。有一次,我等爸爸吃饭等急了,便从关着门的钥匙小孔里偷偷看爸爸是否画完了,只见爸爸微笑着,一面在聚精会神地作画,一面用他自己的诗调,低吟着杜甫的《秋兴》。好不容易爸爸一张画画完了,坤生立即开门说:“先生,吃饭吧。”爸爸点头,放下笔,走出画室。几只淘气的猫乘机而入,把爸爸摊在地上的画踩了许多梅花形脚印。爸爸见此,顾不得吃饭,又跑进画室,把几只猫轻轻抱起,摸摸它们的头,打开窗子,把猫放出屋外,这才关上门,到饭厅吃饭。大人坐在桌上吃,我和哥哥照例坐在小凳上,每人一份菜,放在方凳上吃。爸爸没有忘记在饭前叫我把贴在墙上的法文字母念一遍,然后再吃饭。吃饭时,爸爸不许我们把饭粒撒在桌上,如掉下一粒,他立即叫我们拾起来吃掉,并且常说:“你们天天吃着雪白大米,却不知稼穑之艰难……”
家里的习惯既中又西,我们既过旧历年又过圣诞节。但过圣诞节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比过旧历年更深,这是因为哥哥的生日是12月26日,正好是圣诞节后的一天,所以每年哥哥的生日都和圣诞节一起过。到了那天,妈妈在家中的圣诞树上,挂满了五彩缤纷的小灯和闪闪的彩带,爸爸的学生扮成圣诞老人,给我们带来节日礼物,晚上又吃生日蛋糕。到我入睡前,同弟亲切地坐在我的床前:“妹妹,快快睡,闭上小眼睛,圣诞老人的礼物专门送给睡着的乖孩子。”于是我赶快把眼睛闭起来。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我高兴地看见一个新的洋娃娃放在我的枕头边。
爸爸在“中大”艺术系当教授,每月薪金300元,母亲在家料理家务,招待客人,生活优裕而安定。
在我的记忆中,童年时代南京的一段生活是很幸福的。美中不足的是,爸爸妈妈常常争吵,起因是爸爸喜爱收藏古董、古字画及金石图章,一见到好画、好古董,便爱之如命,不惜重金加以收买;而母亲喜欢过舒适的生活,又好请客。双方都要花钱,尽管父亲收入很高,仍不免因矛盾而发生争吵。

《猫》 徐悲鸿

《雄狮》 徐悲鸿
一天,门口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一部黑色小汽车在我家门口停下。张道藩走出车门,按了一下门铃,坤生去开门。
“是张次长来了。”坤生说。
妈妈换了一件紫红色旗袍,缓缓下楼。
张道藩眉开眼笑地对我妈妈说着好听的话,模样显得很殷勤。
张道藩为了打击爸爸在政治上的进步和达到占有妈妈的目的,不断采取一些隐蔽的手法,挑拨爸爸和妈妈之间的关系。谣言接二连三地传到妈妈的耳朵里,妈妈的性格变得愈来愈烦躁,脾气也越来越坏。
1935年初,田汉被捕的消息传来,爸爸整天焦急不安。为营救田汉,爸爸四处奔走,一直无效果,而田汉在狱中病得很重。最后,爸爸不得不去求张道藩。后来我才知道,张道藩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对爸爸说:“悲鸿兄,我早就让碧薇嫂转告你,不要管田汉的事,这样下去,对你的前途非常不利,可你不听,这样吧,看在老朋友的分上,我去说说情,试试看。”几天后,张道藩又来到我家,对爸爸说:“经过我说情,他们要两个有名望的人作保,才能让他出来治病。”“这个我能够!”爸爸如释重负地说。
经过几天的努力,由宗白华教授和爸爸在保证书上签了字,终于使田汉伯伯保释出狱。出狱后,田汉伯伯全家几口人都暂住我家(包括田汉伯伯的母亲、妻子),这样又引起了一场风波。
“你保田汉已经冒了很大风险了,现在你又把这帮穷朋友养在家里,管吃管穿,你能管得起吗?我真不懂,这样做到底对我们全家有什么好处?这个家就这样被你毁掉了,你还拒绝给蒋介石画像……”妈妈又吵起来。
由于爸爸拒绝给蒋介石画像,又由于爸爸把田汉伯伯全家留在我处,加之田汉伯伯出狱后不久,继续进行抗日的进步戏剧活动,张道藩便进一步策划对父亲的陷害。学校出现了反对父亲的标语,造谣中伤的流言蜚语接踵而来。爸爸也无法再在南京呆下去了,只好于1936年6月去了广西桂林。爸爸在《广西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无礼、无义、无廉、无耻。
妈妈由于受到张道藩的影响,政治观点愈来愈向右转。但她仍然关心着父亲的安危,希望爸爸能放弃反对蒋介石的观点,仍旧回到南京过舒适的生活。于是,妈妈在1936年8月14日赶到广西,想说服爸爸回南京,向国民党反动派让步。爸爸虽然想回家,但不愿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因而拒绝回南京,妈妈只好一人返回。返宁前自然免不了又是几场激烈的争吵,政治上的分歧和感情的破裂都日益表面化了。
就在妈妈回南京的第二天,张道藩又来到我家。他进了大门,走过花园,进了楼房的大门。
妈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终于落入了张道藩的圈套……由于先后6次要求与母亲和好均遭拒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爸爸于1944年2月9日,在贵阳登报与母亲脱离同居关系。2月12日,正式与廖静文女士订婚。母亲大为恼火,在一个星期日,我从学校回家,见吕斯百与妈妈坐在客厅里说话,妈妈命令我立即给父亲写信。我问:“写什么?”妈妈愤愤地说:“我念一句,你写一句。”我顺从地拿了笔纸,记下了母亲口述的内容:“爸爸,你为什么追求一个女人就要和妈妈脱离一次同居关系,假如今后你要追求十个女人,不是要和妈妈脱离十次同居关系吗……”我记好后,拿给妈妈看,她看了很得意。由于家庭没有温暖,我的思想非常消沉。我当时才15岁,不太领会妈妈的这些刻薄话通过我去骂爸爸,会给爸爸的精神带来多大刺激,也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使我和爸爸的关系产生隔阂。

《田横五百士》 徐悲鸿
妈妈当时就把信交给了吕斯百叔叔:“你看看悲鸿有什么反应?”隔不几天,吕斯百来向妈妈汇报了:“徐老师没有说什么,只叫我好好安慰安慰丽丽。”妈妈见骂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便想在离婚费上捞一大笔钱。她把我和哥哥的教养费要得很多,要100幅画,100万元。当时父亲的身体已渐渐衰弱,但为了还清妈妈提出的那笔数目很大的子女教养费,不得不日夜作画,一站十几个小时。爸爸的身体便这样累垮了。1944年夏,爸爸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病危住院。可爸爸没有钱治病,他在中央大学领不到工资,工资都被吕斯百送给我母亲了,卖画的钱又被母亲拿去一部分,剩下二十多万元,几乎全被偷盗父亲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的大流氓,冒名“刘将军”的骗子骗走了。
当我从卢开祥那里得知爸爸病重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就在那个星期六下午,我和同班的女同学小陈一道,经小龙坎到高滩岩中央医院去探望父亲,小陈的家便住在高滩岩医院附近。我们走了十多里路,小陈指着一片房子说:“那里就是中央医院。”我按她指的方向找到中央医院。当我走进病房时,只见爸爸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好久未刮了,脸既黄又肿,半闭着眼睛。继母廖静文女士一个人守在他的身边。
“爸爸,我来看您了,您好点了吗?”爸爸睁开眼,见到我,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低声说:“你怎么不上课,老远跑到这里来?”“今天是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是你妈妈叫你来的吗?”“不是,是我自己来的,妈妈不知道我来。”爸爸见我这么说,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眉头又皱起来:“你应该告诉你妈一声,不然她会因为你没有回家着急的。”“我……”爸爸忽然感到这样来要求我太过分了,他把头转向廖静文:“静,你看看盒子里有什么好吃的。”廖静文走到桌子边,将一个盒子拿过来,里面只剩下一块半像炒米糖一样的点心。继母叫我吃,我迟疑了一下,就拿了那半块点心,慢慢地吃着。等我吃完了,爸爸对我说:“路太远,你赶快回去吧!以后不要来看我,要好好用功读书……”我点点头,望着满脸病容的父亲,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一面用手擦着眼泪,一面离开了爸爸的病房。
我默默地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想。来时因为和小陈一路有伴,不知不觉就到了,现在一个人走回去,路竟是那样长,走了很久很久还没到小龙坎。好不容易远远看到一片灯火,小龙坎快到了,可还有几里路。我就这样走呀,走呀……由于天气炎热和饥饿,加上营养不良的贫血,使我感到头昏。我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也记不清是怎样进了校门,怎样到了那间阴湿的宿舍,便一头倒在床上和衣而睡。

《飞扬跋扈为谁雄》 徐悲鸿
1945年12月31日,父母的离婚协议书在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宿舍张圣奘先生家签订。参加的有律师沈钧儒先生,证人马寿征、吕斯百。我也跟着妈妈去了。
爸爸来得很早,他面色苍白,一脸病容,提着一个粗布口袋,装着满满一口袋钱,这是母亲提出非要不可的100万元离婚费,还带了100幅画,这都是父亲带病赶画出来的。父母在离婚协议书上正式签字,28年的夫妻关系从此彻底断绝。
母亲拿到了画和钱,十分高兴地去中国文艺社打了一夜的麻将。
不久,父亲和继母廖静文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正式结婚,由郭沫若先生和沈钧儒先生证婚。1946年秋,我被母亲带回南京,继续在“中大”附中读书,从此和爸爸分开两地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