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 决定作文的精彩程度
文/龚 峰
责任编辑:吴新宇
细节 决定作文的精彩程度
文/龚 峰

我在长期的作文教学实践中,发现很多学生的习作有粗糙、粗略的毛病,该详写的地方非常简单,文中找不到细节描写。比如写人物,其举止行为仅三言两语,很不到位,以致外在形象模糊,没有个性特点;心理描写流于浅表,没有深处的内在波动。再比如写景状物,也不是基于独到细微的观察,描写模式化、机械化。很多学生作文,通篇就是几条筋,内容空洞,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要想文章精彩传神,取决于细节。作者所状摹的物事纤毫毕现、栩栩如生,就会给读者以如临其境的“现场感”;刻画的人物形象鲜活、血肉丰满、个性彰显,就会让人如见其人,如历其事。如果再有不俗的文采,就会让人拍案叫绝,叹赏作者的“神来之笔”。
古人在论述文章的详略得当时,有两个精准形象的比喻:“密不透风,疏可跑马。”所谓“密不透风”,就是在写与主题密切相关的节点时不惜笔墨,“工笔描绘”(当然,该略写的地方千万不能繁琐,要一笔带过,惜墨如金)。我们可以从众多经典作品中得到借鉴与启示,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语言风格就是以极其张扬的细节著称,汹涌的联想让他的感觉达到了“爆炸”的程度。他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对一片高粱的描写动辄数百上千字,仿佛像素极高的摄像机,“摄”出的作品当然是精彩绝伦的。
初中语文教材中也有很多注重细节描写的“案例”,语文老师上课时都会就此详加分析。我在此再举几例,供大家回味感受。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现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文章细腻、温婉,一篇写父亲的《背影》角度特别,情感朴实、真挚,感动了几代人。其成功之处,我以为与精微描摹日常的、能够唤起共鸣的细节密不可分。他父亲已经年迈,体态臃肿,给儿子买橘子已勉为其难,“穿”“爬”“蹒跚”“探身”“攀”“缩”“微倾”“抱”“扑扑”,这一系列动作让父亲的慈爱展露无遗,让作者潸然泪下的同时也让读者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如若换一种粗枝大叶的潦草写法,“父亲去给我买来橘子”,感人之情从何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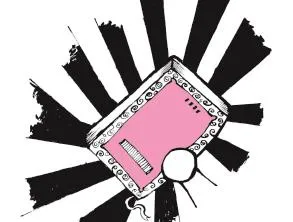
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
《水浒传》是一部写豪侠英雄的古典小说,里面的人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杀富济贫,快意恩仇。从故事铺排和人物性格的塑造看,古代章回小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人物和情节大同小异、不够细腻的问题,但施耐庵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整部《水浒传》中熠熠闪光的亮点确实不少。如情节的张弛、叙事节奏的缓急、语言的粗豪泼辣与情节的细微精彩等,《水浒传》都是我们学习写作取之不尽的宝库。
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我们印象最深、最解气过瘾的就是那“三拳”。“打”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为了惩治郑屠这个地痞无赖,愤怒的鲁达并未逞一时之勇,来到肉铺,劈头盖脸就揍他一顿,而是“三激”郑屠,对郑屠大加戏弄,可见其有胆识、有谋略。而伸张正义、惩治恶人的“三拳”,一拳一个落点,一拳一个比喻,一拳比一拳厉害,则不仅让人解恨,更在读者面前刻画出了一个英勇非凡、武艺高强的“梁山好汉”形象。至此,一位嫉恶如仇、扶危济困、重义轻财、粗中有细、勇而有谋的肝胆英雄,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
清代卓越的短篇小说家蒲松龄文笔相当洗练,是惜字如金的典范。当学生学习这篇《崂山道士》时,会为他神奇的想象大呼过瘾。道士投箸作法,在墙上贴一片纸,竟成了一轮皓月;再作法,竟能唤出月中嫦娥来为客人起舞助兴。嫦娥的秀美音容、婀娜舞姿栩栩如在目前。作家真是高超的魔术师,不管想象中的人物在远古还是在未来,和我们的距离有多少光年,都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就叫“神来之笔”。我们要用自己的文字再造美轮美奂的情景,必然得仰仗出神入化的细节。
我的短篇小说《元老》塑造了一个韦小宝式的不学无术、看风使舵的市井无赖形象,他叫袁四堂。里面有一段他在学校打铃的细节特写,适当地运用了夸张手法,读者感言“印象最深”,眼睛一闭,就似看见袁四堂在打铃:
铃就挂在学校中央的那棵百年老樟树下,是抗日战争时期鬼子留下的炸弹壳。大家看见,袁四堂有时拎着小闹钟,有时卷起袖子、手捏钢管在校园巡弋。他打铃的姿势很特别,得进行一个特写:起床铃,连敲足有三分钟,先是春雨润物,潜入幽夜,愈来愈急骤,铁骑突出刀枪鸣,银瓶乍破水浆迸。再又降低八度,轻抹慢捻,师生们被惊破的梦在杳渺低徊的声波中缓缓弥合,忽然,武松揪住了吊睛白额猛虎的顶花皮,铁钵大的拳头猛砸七七四十九拳,你不得不在雷霆檑木中惊坐而起。上课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以三下为一逗号,节奏鲜明,温和婉转。下课铃,镗……镗……镗!一记铜音画着无数同心圆荡漾开去,又一记铜音推波助澜。吃饭铃,连续七下,七剑下天山,七饭踢啊七饭踢,同学们敲着瓷碗,在袁四堂奏鸣的铃声里如大河之水夺闸而出。
责任编辑:吴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