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前,郝景芳只字不提《北京折叠》
高丹
四年前,写完《北京折叠》后,郝景芳“几乎没有一刻挂念它的死活”;四年后,《北京折叠》获得2016年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郝景芳说:“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
“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拿到了博士学位,2013年开始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2006年开始,写一些科幻小说,后来又写一些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然后最近新出的这本《生于一九八四》是一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我的简历大概就是这些。” 在《生于一九八四》的发布会上,郝景芳如此介绍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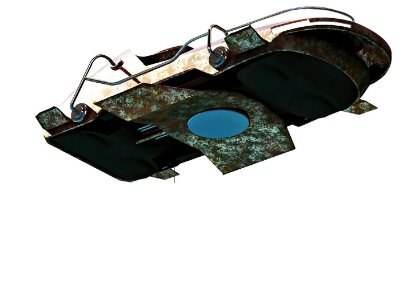
因为《北京折叠》,她开始被称为“科幻作家”,但她却尽可能地避免谈及《北京折叠》和雨果奖。
那些加持,我不能信
事实上,传说中的郝景芳远比她的自我介绍“神奇”得多。
在知乎上有一个声称是郝景芳的同学的回忆很有意思:“这姑娘是当年隔壁班的学神,新概念作文她拿的名次貌似是够北大中文系免考的,然后她竟然考了清华物理系,我当时还觉得这种学神是不是若干年后出现在科研大牛名单里,结果就看到她入围雨果奖提名,真是智商碾压无时无刻不在。”一个郝景芳的邻居也跟着吐槽说,从小就活在这个“别人家的孩子”的阴影里。
郝景芳说之前有个关于她的报道是“郝景芳超越《三体2》入围雨果奖”,还有一篇在社交网络中刷屏的帖子——《白天是清华金融女,晚上是宇宙学女神》,针对一些传闻,郝景芳笑着回应:“我在国务院很小的一个研究机构工作,给政府写一些报告。我没有见过习大大。有人传我给李克强总理写信,这个事情已经被越传越远。是不是我接下来身份地位就到了随便进出中南海?”
而她真实的成长经历,则伴随着延绵不断的焦虑。

刘慈欣一直不吝于表达他对郝景芳的欣赏,甚至曾把郝景芳的风格与科幻大师雷·布莱德伯利相比较。称“她把我们常见的科幻题材洒上了一层很诗意的阳光”
高中时,郝景芳就痴迷物理。海森堡、玻尔等人关于量子力学的普及版阐释,震撼了她的世界观;而薛定谔的《吠檀多哲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更让她叹为观止。“高三的时候我看科学和哲学,看爱因斯坦写的散文集,以及薛定谔写的宇宙真实性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关系的文章,我感觉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
她曾经坚定地想做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因此,她上了清华物理系,并读到了硕士研究 生。
在清华,她发现大牛太多了。曾经有一次,她鼓起勇气找班里的大牛请教一道怎么都解不出的题,大牛看了一眼,实事求是地说:“这道题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没做,你看看讲义吧。”
感到自己在天体物理学方面无法做出杰出成绩后,郝景芳改读宏观经济学的博士。这个改变,使她观察世界的角度更多元,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建构她的科幻世界,建立运行规则。
“外界冠以我的‘学霸女神这样的东西,我是不能信的,我一旦信了,就会被营造出来的盒子囚禁,然后我会更加在意别人的感受,也就因而更加触碰不到我的内心。”郝景芳承认,有人关注是好事,但善于焦虑的她也会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冷静,“这件事并不会令我的写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假象,对于我将来的写作生涯是不利的,一个人的写作必须是连续的。”
因此,她不太愿意别人一再提及她的《北京折叠》,更不愿意大家因此而界定她的写作。
“原来你最近过得还不错”
2002年,郝景芳荣获全国中学生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但是她并不像新概念的大部分作家那样关注青春与疼痛。

《星旅人》和《孤独深处》是郝景芳此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北京折叠》便收录在《孤独深处》中,而《生于一九八四》则是最新出版的现实类虚构作品
“那时候我自己关注更大一点的问题,我关注宇宙、量子力学、人的自我意识,关注人是什么,世界的真相假象;我也特别喜欢看哲学家们写的关于人、自我、人类意识等这一类的书。我的关注就导致我非常眼高手低,这中间巨大的差距是不可弥合的,我自己对校园爱情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就想写关于人和自我意识这样的书。”
过高的志向令她一开始根本没法落笔,“我最开始根本就没法儿写,其实爱因斯坦写文章的那种举重若轻是建立在大量的人生经验上,他对于某一个问题有着几十年的思考。而我过于强求,一上来就想写大命题,人不能假装自己懂而去谈论一些东西,所以我后来就从一些比较轻巧的、小的东西开始写,科幻里面假想一些东西,可能都不像文学,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探索,后来慢慢加上生活中的所思所感,这样就不是谈论一个终极命题,而是从生活中有小的困惑出发,这样才能找到一些我确实想写的。”
2011年,郝景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北京办公室实习,随IMF总裁拉加德穿梭于星级酒店、中南海、国家会议中心,研究宏大的社会性课题,见证着“制度的生产过程”;与此同时,她租住在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楼下一片棚户区,她混杂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中,主动与出租车司机、餐馆老板攀谈,了解看病、上学这样看似正常却是很多家庭巨大困扰的命题。
她看到了在一个个巨大的数字之下,是很多人为了生存而奋力地挣扎。重重叠叠却又天壤之别的片段和场景,在郝景芳的生活里静默地交汇再平行,看似人尽皆知,一旦细想,便掉入绝望的漩涡。
2012年,她花了三天时间完成了《北京折叠》。她想要表达她感受到的“不平等”。于是,在《北京折叠》中,她建立了一个制度,把“不平等”推向了一个极致。
《北京折叠》没有宏伟的科幻,唯一的科幻核心是:日渐拥挤的未来北京,昼夜之间空间翻折,因出身和阶级划分的三个空间的人们一起分摊每个四十八小时,轮流苏醒,交替生活。“第三空间”的人们日复一日在和平的绝望中度过近乎无意义的一生。主角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老刀,为了孩子学费去干类似走私的行当。虽没有生离死别,但小说的残酷之处在于,“第三空间”的底层民众甚至不具有被剥削的价值,他们存在的意义原本可被“第一空间”发达的机器人替代,只是“第一空间”的决策者们为了让他们“生存”下来,便将他们安置在流水线上扮演着“垃圾工”,无知无觉走过一生,而他们的一生被彻底挡在了“第一空间”的通胀之外。
郝景芳并没对这部作品报以获奖的期盼。在她看来,一部小说写完后,它就是脱离了作者的存在,“它的命运与我无关,几乎没有一刻挂念它的死活。”直到它获了奖,郝景芳的感觉是:像是得知了某个在远方的游子的近况——原来你最近过得还不错。
在得知入围雨果奖后,她也只是在微博简单回应:“能入选雨果奖很惊喜。当初小说只发在一个新创的电子杂志上,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再次感谢宇昆兄的翻译。小说的翻译与被接受程度紧密相关。不能和大刘的作品一同入选,心中的遗憾甚至大过了惊喜。宇昆兄在帮助华人作品推广方面居功至伟。”
郝景芳再一次强调,外在的评价并不是她内在发展的轨迹,“对于我而言,我自己写作方向道路,写作计划都没有发生变化,这可能就是个热潮,对我而言都一样,我仍旧是按照我喜欢的路子来写我喜欢的东西和我感兴趣的话题。”
不希望小说成真
获奖前一个月的那次采访,郝景芳会尽可能地将话题拉回新书《生于一九八四》。在这部作品之前,郝景芳已经出版了三部长篇科幻小说《流浪玛厄斯》《回到卡戎》和《流浪苍穹》,还有中短篇小说集《星旅人》《孤独深处》和《去远方》,其中,《北京折叠》便收录在《孤独深处》中。
不同于以往的科幻题材,《生于一九八四》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而1984年,正是郝景芳出生的年份。
这本书以1984年为限,记录了这之后的三十年过程中两代人的心路历程。书中的父亲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反思自己年轻时的所为,在内心负疚的驱使下前往世界各地,寻求精神出路。女儿自小按部就班上学读书,生活平稳,却在面临人生方向选择的时刻感觉迷茫,经历了精神崩溃的痛苦,最终获得领悟,找到内心的清明安宁和立志从事的事情。

作为《北京折叠》的英文译者,刘宇昆(左)也收获了一座雨果奖杯(《不存在日报》王编糖匪/摄)
郝景芳说《生于一九八四》缘起于她在清华读书时的焦虑:“一方面焦虑自己和其他人的比较,觉得自己很多地方不如别人,希望能够跳出这样的挫败感和这种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我想找到自己可以依靠的东西,但是我总觉得我的头脑其实可能空空如也,脑中的东西都是别人灌输给我的,这种感觉就让我更加难受。然后那段时间我还会陷入其他的困惑,于是我就是不断想要劝劝自己说,我这个人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我想写的是我自己的一些困惑、一些想法、一些焦虑的过程,实际上的缘起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然后我考虑每一个想法不能是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想,需要有一些人物和经历为载体,后来我脑子里就出现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形象,她每一步是有哪些困惑,她自己做了怎样的努力,怎样解决,又有了新的困惑,慢慢的这个女孩子的形象就会越来越清楚,然后我就把她写了下来。”郝景芳说。
在读《生于一九八四》时可以发现有一章是没有标点的,全都是呓语一样的碎碎念,她说:“这些其实就是我的一些胡思乱想的意识流,词语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会有一些场景,然后就把场景里面涉及到的语言、词汇写进去。我主要想的是主人公一定有大量的信息在头脑里碰撞。”
郝景芳称此书为“非自传的自传体”小说。她说:“如果说这个我和主人公有什么经历上的相似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在写一种焦虑的心情,所以它其实是相当于一个内在的自传。”
至于未来的写作方向,郝景芳还会延续自己的习惯——假想一个世界,然后去推理,她一定要把逻辑推通了,再往下写。“我自己比较热衷于写社会制度,我喜欢假想一个不存在的国家,类似于《镜花缘》的。我以后还会写别的制度,可能跟我们的现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映照和联系。”
在这次采访结束的一个月后,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击败斯蒂芬·金的《讣告》,获得了2016年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
发表获奖感言时,她说:“实际上,刚才我还在考虑自己去‘雨果奖落选者派对上的样子。获奖者派对,落选者派对,我都不知道自己更期待哪一个。科幻作家很喜欢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到,不管好坏,是幸运还是不幸。在《北京折叠》这部小说中,我提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面对着自动化、技术进步、失业、经济停滞等各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有一些黑暗,显然并非最好的结果,但也并非最坏的:人们没有活活饿死,年轻人没有被大批送上战场,就像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
这不禁令人想起《北京折叠》获得中国科幻坐标奖后,她写获奖感言时的情形,那时的她正在计算着明年财政收入预测,这是给全国人大的项目报告,忙得没有时间吃饭、喝水。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了下来,郝景芳突然有一种因为荒诞感而引起的伤感:“无论我怎么书写这个世界的荒诞,我还是在这个世界中貌似严肃地活着,并为此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