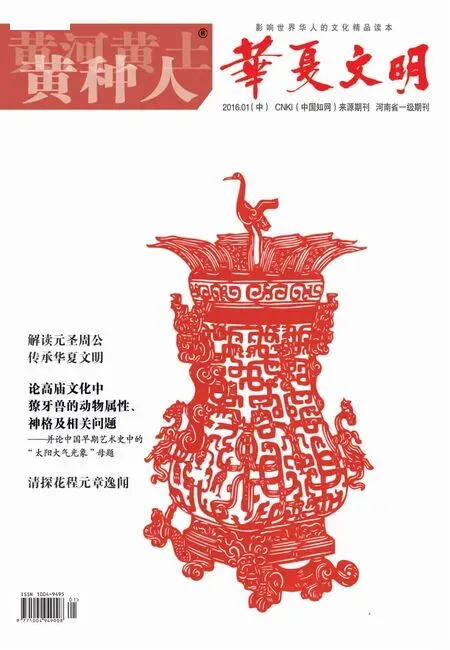陕西铜镜研究概述
□冯 霜
陕西铜镜研究概述
□冯 霜

1979年西安枣园出土的昭明镜

1952年西安市出土的尚方镜
陕西地区是我国古代几个主要王朝周、秦、汉、唐等的中央王权所在地,该地区出土的铜镜具有典型意义。但是,几十年来关于陕西地区出土铜镜的系统研究却显得不尽如人意。笔者在阅读了陕西地区铜镜研究的相关著作后,对近几十年来陕西地区铜镜研究的概况进行了简略的总结,以便为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应用的素材。
铜镜铸造业作为青铜铸造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手工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铜镜作为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其次,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古代铜镜,更多的是研究其历史文化价值。后者的研究对我国现代考古学、历史学、美学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对出土铜镜形制、纹饰、铭文、制造工艺的系统研究,可以对出土铜镜的遗迹单位乃至相关遗址的年代作以推断,从而可以建立相关的时间标尺,为时代并不十分明确的遗迹、遗址提供判断依据;从对铜镜纹饰、铭文的阐释,并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对铜镜制造工艺的科学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思想文化、精神世界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在进一步研究过程中,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铜镜形制、纹饰、铭文、铸造工艺的研究,可以为下一步研究当时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提供依据。
一、陕西铜镜研究的主要成果
陕西地区作为中国古代几个重要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出土的铜镜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在经济文化承载的内容上,相比其他地区而言更加精美、内涵丰富。
陕西铜镜研究的主要成果可以概括为专著类和研究性论文两大类。
1.专著类。关于陕西铜镜图录类的研究专著,第一本是在1959年由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陕西省出土铜镜》。该书是关于陕西地区铜镜专门研究的处女作。书中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之前,陕西省各地基建工程清理发掘中的铜镜作一简单初步的统计。该书中总共收录了陕西出土铜镜173面。主要收录的是汉唐铜镜。该书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来展现陕西地区出土铜镜的具体信息。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在陕西地区出土铜镜的基本信息,并且以这些基本信息为基点,尤其是以其中涉及纪年铭文的铜镜基本信息为基点,从而可以对这些出土铜镜的墓葬情况作以归纳总结,为解决相关的历史问题提供断代依据。
1984年,孔祥星、刘一曼主编的《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将我国古代铜镜作了系统的梳理,对此后学者学习、了解和研究铜镜具有典范意义。该书中涉及有陕西出土的铜镜34面,多为汉唐铜镜。
1992年,孔祥星、刘一曼主编的《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是关于铜镜类图录专著中较为规范的版本。该书收藏的铜镜主要是考古出土和文物征集品,以铜镜拓片为主,亦有部分照片及摹本。以历史演变为序,基本上按照铜镜流行的先后顺序排列。所收铜镜较多,其中不乏涉及陕西省出土的古代铜镜,对我们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地区乃至其他省市地区铜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2年,程林泉、韩国河主编的《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收录了336面铜镜,其中334面出自1100余座墓葬。该书除了一般性的介绍外,还用了大量篇幅对秦、汉铜镜的各种类型进行了分型、分式,不论是铜镜形制还是纹饰、铭文都做了总结概括,是目前对汉镜类型最为细化的研究,同时也是学术界第一次以地域划分为依据对铜镜进行研究,对我们更进一步分阶段、分区域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镜起了带头作用。
2008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主编的《西安市文物精华——铜镜》(世界图书出版社),所收录的铜镜均为西安市出土或征集的精品。其时代上起战国,下至明代,共170余面,可以说是西安铜镜的系统展示。尤其是书中对铜镜研究中的专业术语作了详细的阐述,对初次接触铜镜者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2012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主编的《千秋金鉴》(三秦出版社),主要是对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藏铜镜进行整理。收录的铜镜上起商周时期,下至明清时期,并在其中的仿古铜镜页作了详细描述,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藏铜镜的具体情况。使用了多国语言(中文、英文、日文)解说,更加便于外国学者们了解陕西省铜镜历史演变脉络。该书是博物馆收藏铜镜研究的一个展示,是继《陕西省出土铜镜》之后,又一部对陕西省出土铜镜以及在陕西省境内征集铜镜进行描述的力作。
2.研究性论文。陕西出土铜镜的研究性论文主要有三部分:
(1)综合性研究。如宋新潮先生的《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1],对春秋以前的铜镜进行了分类研究,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铜镜的来源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其中涉及陕西境内出土的铜镜共13面,主要是分布于扶风、凤翔等地区,年代主要为西周早、中期。

陕西出土的真子飞霜镜

陕西出土的仁寿四神纹镜

陕西出土的日光镜
马利清的 《出土秦镜与秦人毁镜习俗蠡测》[2]认为毁镜习俗与地域民族有关,在时间上也只限于秦文化崛起过程中,并对陕西咸阳地区出土秦代铜镜的相关状况作了简单概括和推断。陕西地区虽然属于秦王朝中央集权所在地,但是出土秦铜镜很少,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秦王朝存在时间很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秦人自身就有毁镜习俗。
(2)个别铜镜研究。如昭明的《陕西凤翔出土汉镜举要》[3],刘在时的《陕西黄龙发现四十四字铭文汉镜》[4],刘占成的《陕西蒲城县延兴村发现宋代铜镜》[5],朱捷元的《陕西永寿县孟村发现隋代铜镜》[6],徐信印、徐生力的《安康地区出土古代铜镜》[7]等文章,对陕西地区出土的铜镜都有所描述。
(3)博物馆馆藏铜镜研究。主要有高嵘的《唐代铜镜之美——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铜镜》[8],商县博物馆的《陕西商县博物馆收藏的铜镜》[9],杨倩的《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馆藏汉代铜镜鉴赏》[10],王桂枝的《宝鸡市博物馆收藏的铜镜》[11],卢建国、贾靖的《宝鸡市博物馆收藏部分古代铜镜》[12]等,这些文章主要是分时间段更新博物馆收藏信息,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馆藏铜镜,以及博物馆现状。
以上著作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陕西地区铜镜发展的基本状况,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材料。
二、陕西铜镜研究成果的分析
从1959年出版的陕西铜镜图录专著《陕西省出土铜镜》算起,对陕西地区铜镜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行,越来越多的铜镜不断面世,对于新出土铜镜的研究也从未间断过。
1.陕西铜镜研究成果分类。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铜镜研究的相关成果,可分为以下两类:
(1)铜镜图录类(其中包括馆藏铜镜和非馆藏铜镜大体形制的介绍)。研究著作中以图录类最多。如《陕西省出土铜镜》,该书对陕西地区出土铜镜的具体信息都做了标记,从而启示我们可以利用统计学的一些方法,比如对铜镜质地做检测之后,将其所测数据进行整理研究,从而利于我们科学地运用这些数据对铜镜作进一步的内涵揭示。又如《西安市文物精华——铜镜》一书,对西安地区出土或征集铜镜中的精美者进行了选择性整理,时间跨度较长,其中有许多珍贵的标本,并且很多铜镜都是首次面世。这些首次面世的铜镜又为我们日后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从而又敦促我们在下一步研究中要更加注意新材料、新发现在文中的应用。
另外,陕西地区铜镜研究中的馆藏铜镜整理类的大宗,目前要数陕西历史博物馆编撰的《千秋金鉴》。该书通过展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藏铜镜,为我们全面展示了陕西近年来铜镜出土的相关状况。还有一些论文,主要是介绍博物馆内的铜镜,如《陕西商县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馆藏汉代铜镜鉴赏》《宝鸡市博物馆收藏铜镜》《宝鸡市博物馆收藏部分古代铜镜》等。这些文章主要是对不同时间段内收录于博物馆的铜镜作以简单的信息更新。
(2)按照历史年代对铜镜铭文、纹饰进行整理,进而揭示铜镜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主要著作有程林泉、韩国河主编的《长安汉镜》[13]、马利清的《出土秦镜与秦人毁镜习俗蠡测》[14]。学位论文中,如郝少晶的《仙山并照——唐代山水纹类铜镜研究》[15]、李婷婷的《唐代狩猎纹铜镜研究》[16]、车正萍的《试论汉代铜镜的纹饰》[17]、陈章龙的《宋代铜镜分期初探》[18]、王颖的《唐代花鸟铜镜的考古学研究》[19]、李新成的《东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20]、田敏的《汉代铜镜铭文研究——以相思、吉语、规矩纹镜铭文为例》[21]等,这些著作通过划定区域和时间范围来对限定时间内的铜镜内容进行详细梳理,特别是对铜镜铭文的解读,可以联系历史事实,从而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经济文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2.陕西铜镜研究存在的问题。陕西地区出土铜镜众多,但是专著并不多,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大多数专著研究不够全面深入。很多著作只是选择出土或征集铜镜中品相上乘者进行研究,这点主要体现在对汉唐铜镜的研究方面,如在研究汉代铜镜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只是注意到博局镜,并对博局镜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容作以深刻研究,但是对于同时期其他铜镜重视度不高。再如唐镜研究中的海兽葡萄镜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很多学者由此只看到了唐代文化交流的印迹,而未注意到该时期铸造技术进步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虽然对该时期的特种工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同样对于该时期其他种类铜镜重视度不高。所以很多学者在收录材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因此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研究主要以图录类居多,对铜镜纹饰、铭文分型、分式的研究以及纹饰、铭文所能反映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只是简单涉及而深入研究甚少。
(2)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镜进行分段研究,对各历史时期涉及铜镜进行详细的分型、分式研究著作亦是十分缺乏。尤其是其中有的图录类书籍只是标出了铜镜的出土地点和尺寸,但是关于铜镜的其他方面包括所反映的思想文化等信息深入研究不够。
(3)馆藏文物的研究地区,主要集中于关中的西安、宝鸡地区,其他地区涉及较少。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博物馆中的精美者,对于那些品相较差的铜镜重视度不是很高,因此,在研究论述过程中不够全面翔实。
三、陕西铜镜再研究可行性分析及研究思路
由于陕西地区出土铜镜已经有相当大的数量,大多数铜镜档案信息也十分明确,因此,对进一步研究能够提供基础资料。另外,研究著录、论文已经有一定的数量,可以为下一步研究提供借鉴。由此,笔者对陕西铜镜进行再研究作以下思考:
1.梳理。可以对之前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梳理,从而建立陕西地区铜镜研究论著目录。即可以依据年代序列将之前的研究论著进行分类。
2.建档。对所有铜镜——无所谓品相好坏、做工差异——进行统计建档。其中对于出土信息明确者,按照历史编年的方法将各个历史时期铜镜作一简单梳理,统计其详细信息和数量,并对其发生、演变作一简单概括;对铜镜出土后由于人为原因信息不详者,将其与信息明确者进行对比,并对其进行归类,从而形成全面的铜镜图录。
3.分类。依据该图录进行下一步研究。(1)将所有铜镜按照形制的不同进行类型划分,将各个历史时期的类型作一统计;(2)对有铭文者进行统计,并针对其铭文内容进行详细分类、解释,由此便可以形成专门的陕西地区铜镜铭文专著;(3)对铜镜纹饰作统计,分析该纹饰的具体内涵;(4)利用科技手段,对铜镜进行成分分析,从而总结其演变规律。
4.分析。将各类铜镜的纹饰、铭文内容与各个历史时期具体的历史人物故事以及历史文献内容结合,全面地对铜镜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分析该铜镜所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内容以及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等内容,从而明确其产生的社会现实以及历史原因。
5.整合。通过综合各个历史时期铜镜形式、纹饰、铭文、成分的研究,建立起各个历史时期陕西地区铜镜的框架。整合各个时期铜镜特点和历史文献所反映的历史史实并做到:一方面建立起陕西地区铜镜具体材料的详细脉络,将无论是出土还是征集、无论是精美或是品相较差者都能全面地加以梳理总结;另一方面将历史文献与铜镜铭文中所反映的历史史实相结合,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社会现实,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铜镜更多的资料信息,也为历史学等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依据。
注释:
①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7年02期。
②(14) 马利清:《出土秦镜与秦人毁镜习俗蠡测》,《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06期。
③昭明:《陕西凤翔出土汉镜举要》,《文博》1995年03期.
④刘在时:《陕西黄龙发现四十四字铭文汉镜》,《文物》1984 年 07 期。
⑤刘占成:《陕西蒲城县延兴村发现宋代铜镜》,《考古》1985 年 03期。
⑥朱捷元:《陕西永寿县孟村发现隋代铜镜》,《文物》1982年03期。
⑦徐信印,徐生力:《安康地区出土古代铜镜》,《文物》1991年 05期。
⑧高嵘:《唐代铜镜之美——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铜镜》,《收藏家》2009年01期.
⑨商县博物馆:《陕西商县博物馆收藏的铜镜》,《文博》1988年 01 期。
⑩杨倩:《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馆藏汉代铜镜鉴赏》,《荣宝斋——物华天宝》2012年09期。
(11)王桂枝:《宝鸡市博物馆收藏的铜镜》,《文博》1995年05期。
(12)卢建国,贾靖:《宝鸡市博物馆收藏部分古代铜镜》,《文物》1991年 07 期。
(13) 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15)郝少晶:《仙山并照——唐代山水纹类铜镜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编论文集,2014。
(16) 李婷婷:《唐代狩猎纹铜镜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编论文集,2013。
(17) 车正萍:《试论汉代铜镜的纹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编论文集,2004。
(18) 陈章龙:《宋代铜镜分期初探》,长春:吉林大学编论文集,2007。
(19) 王颖:《唐代花鸟铜镜的考古学研究》,西北大学编论文集,2014。
(20)李新成:《东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编论文集,2006。
(21)田敏:《汉代铜镜铭文研究——以相思、吉语、规矩纹镜铭文为例》,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编论文集,2011。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秦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