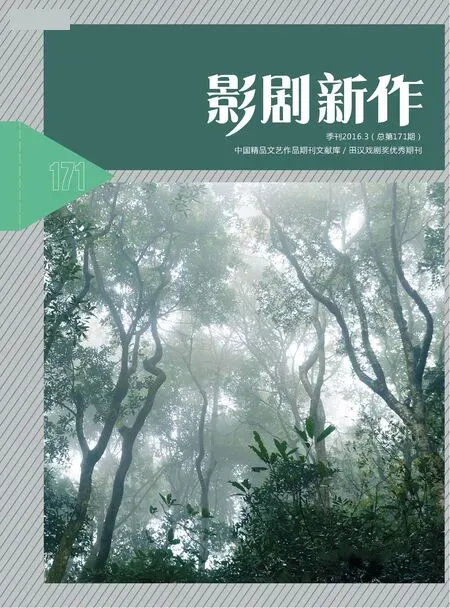故园旧梦
——重游岭南画派发源地可园有感
熊天涵
故园旧梦
——重游岭南画派发源地可园有感
熊天涵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岭南却秋意迟迟,夏日依然徘徊留恋着这片土地。这里的夏季总是特别长,秋天又短如白驹过隙,你尚未察觉,已是冬日凛冽。在四季并不分明的城市里,绿意从不缺席,而在老莞城的一隅,绿意更是特别眷顾一方小园。亭馆绿天深,楼起绿天外。绿意生长在可园随处的角落里,四时常在;落在画家无数的画卷上,永久封存。
乘着这满目的绿意,顶着依旧炎炎的烈日,我陪同友人再一次走进可园,走进这个在东莞的土地上已经静立了百余年的岭南私家园林,走进这闹市里的最后一片静土,最后一处洞天。
时值正午,可园游人零稀,一切似乎都是沉静的。穿过碧廊,纤竹微微摆动,枝叶在切切低喃,层叠的竹影投印在斑驳的花砖上,也将它们的私语说与这一朵朵盛开在脚下永不凋零的繁花。登上高阁远眺,亭台轩榭的檐角高扬,屋宇层层攀叠错落,可园之景尽收,便如主人一般居幽志广、览远怀畅。又走近碧池,垂柳轻抚着池水,天鹅在树下觅得一处阴凉,懒懒地弯着颈项,望着水中的自己。我们不禁放轻脚步,唯恐打扰那一砖一瓦、一花一树,唯恐有半点唐突打破了这个刚刚在心中织起的,关于可园的梦。
道光三十年(1850),张敬修开始修建可园,历时近14年,他才终于将心中的颐养之地筑造完成。张敬修为了可园倾注了太多心血,在宦海沉浮半生,即将卸甲归田的他只想为自己寻一方静谧的天地,远离戎马刀光,忘却世俗尘嚣。“未荒黄菊径,权作赤松乡”,他只愿以陶渊明、张良为志,晨起廊下漫步,看悉心培育的一株株芷兰猗猗葳蕤;午后楼中抚琴,听不舍释手的唐琴绿绮幽幽鸣响;夜晚亭中赏月,沐岭南海岸遥遥送来的习习凉风。曾经的战火硝烟在这日复一日的静好岁月里远去消逝,只余下这一颗悠游自在的心。
张敬修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不住地点头,心中已然为这心爱的园子想好了名号——“意园”。他邀请友人们前来,分享自己的喜悦,众人穿行在这玲珑雅致的小园里,也不住地点头:“可以、可以”。这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地称赞提点了张敬修,何不名为“可园”?可堪游赏!是啊,可以!当然可以!于是可园成为了莞邑乃至岭南文人荟萃的乐园,群贤毕至、鸿儒往来。他们初春踏青、夏日品荔、秋季赏菊、隆冬咏梅,在这一方小园里品味四季更迭轮回,感叹人生流年似水,寻找内心宁静安然。
这群贤里就有岭南画派的始宗居巢、居廉,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年。若是没有“二居”,可园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大约也只是一个有些历史的公园罢了。可居巢、居廉兄弟的到来,为这本就古雅的小园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使可园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抹去的一枚烙印,成为岭南绘画追随者的朝圣之地。
东莞作为岭南绘画的重地,在古代一直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明代莞人张穆亦是史上重要的绘画名家。张穆为东莞茶山人,性好养马,亦爱画马,他宗法宋元,最为心仪赵孟,常以线描勾勒,以淡墨皴染,用笔谨细敦厚,笔下骏马生动传神。时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名士大儒彭孙、屈大均将他比为唐代画马大家曹霸、李公麟。除去鞍马,张穆在鹰禽、人物、兰竹上也有极高成就,且诗书画印兼善,尤为全面,在明末清初画坛享有盛誉。
张敬修本人也善作画,他尤爱画兰,园中所植兰花已被他描摹千遍。他的侄子张嘉谟受其影响,也钟情于兰,留下了众多以兰为题的画作。张穆画马之余也爱画兰,现今可知他离世前的最后一件作品即为兰石,兰草生于奇石夹缝中,傲然挺立、顽强不屈。兰花自古为文人墨客所爱,它高洁出尘的品性正是文人所追求向往,咏兰绘兰的名篇佳作更是不胜枚举。张敬修绘事之余甚至亲自撰写了画兰专著《兰说》,记录他画兰的主张与心得,嗜兰之情可见一斑。居巢、居廉也有不少兰花作品遗世,他们居住在可园,常与张氏叔侄品评彼此所绘之兰,研讨画兰之法。
张敬修虽投笔从戎,征战沙场二十年,但他镌刻在骨子里的文人气质却从未被磨灭。他雅好金石书画,精通琴棋诗赋,广交文人墨客,时邀友人雅集。在广西历官时,张敬修结识了侨居桂林的番禺人居巢,爱惜其才,纳为幕僚,给予他慷慨资助,并让其侄张嘉谟拜入居巢门下,和居廉一起学习绘画。伯乐难寻,居巢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奉为知交,亦师亦友,自此相随,终于来到了滋养他绘画之地——可园。回看当时“二居”的作品,总可以从中找到可园的印记。居巢有一方印为“可以”,每有得意之作则落此印于画,也侧面印证了“可园”之名的由来。
岭南画派由“二居”始兴,他们善花鸟小品,上溯宋代院画、元代文人画,近追恽南田笔意,深入传统。同时又别具一格,独创撞水撞粉之法,专注物像质感的描绘,重视写生,形成恬淡明丽的绘画风格。“十万买邻多占水,一半起屋半栽花”,张敬修在可园里广植汀花逸草,豢养飞鸟渊鱼,为“二居”营造了一个欣然生动的花鸟世界。可园里随处都是他们作画的题材,擘红小榭里摘落枝头的丹荔、碧环曲廊旁随风摇曳的翠竹、问花小苑内悄点新蕊的蛱蝶、雏月池馆下倏然游走的锦鲤,甚至厨厅灶房里的新鲜果蔬,这些岭南风物都一一被“二居”永恒定格在画中。他们浸淫在此,与自然为伴,得生动之趣,获得源源不绝的素材与灵感,最终将这些尽数展于毫端。张敬修为“二居”提供了最大的空间与自由,使他们能够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可园幽静的环境,居此悠闲的心境,不仅可以舒散怀抱,亦得以从容艺文。
张敬修对居巢的绘画评价极高:“写生妙笔擅徐黄,更具梅花铁石肠。无数奇峰出怀袖,前身应是米元章。”居巢绘画,近半是赠与张氏叔侄以作答谢。居巢在可园居住时正值中年,是绘画风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可园幽雅精巧的特点与他的绘画相契谋和,在园中的写生也对他大有裨益。清末堪逢乱世,若没有张敬修的慷慨相待,为他们提供安逸的生活与良好的作画条件,“二居”绘画会形成怎样的面貌,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犹未可知。也正是在可园的日子里,他们不断摹古写生,开创了岭南绘画新的风格,为今后岭南画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张敬修的威望与雄厚的财力使得他身边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在可园里的集会热闹非凡。“二居”客其门下,往往被张敬修举荐给众人,因受泽被,名声鹊起。且他们在诗文上亦有极高造诣,与集上文人博古论今、讲艺问学、诗酒相和,受文人所青睐,结交愈广。“二居”在可园纳徒传业,将自身所学授予弟子,岭南绘画新风悄然而起。
“二居”与张氏叔侄的情谊笃厚,他们在可园里相伴十年,直到张敬修去世,二人才离开可园,回到广州旧居隔山乡,仿造可园修建十香园。而就在张敬修去世的第二年,居巢也在十香园中离开人世。居廉延续着堂兄之学,广收门徒,其弟子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被后人并称“二高一陈”,最终开创了岭南画派。
身居东莞,我已不记得来过多少次可园了,如今陪同友人再一次走进这里,骄阳似乎也被趟栊拦在了门外。踏上精巧的花砖,透过斑斓的彩窗,细数封尘的历史,极目望去,似乎每一个角落都有先人的身影,每一个画面都曾入了他们的绘卷。立于园中,我们隔着百年的岁月洪流,去触摸、去感知清末岭南文人的那份清雅闲适的意趣,那颗精巧出尘的玲珑心。
清末社会日渐商品化,画家也有着职业化的倾向。“二居”就是当时典型的职业画家,而张氏叔侄则是“二居”的赞助人,这也是商品社会下新型的人物关系。然而即便如此,他们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文人角色,他们的生活、言行、绘画仍然与文人趣味休戚相关。可园的幽雅就是清末文人旨趣在建筑上的呈现,“二居”绘画的恬淡风格也是出于文人喜好的自觉选择。于是,我们游赏可园,观看“二居”绘画,都似如沐清风,退去了凡俗嚣躁,内心平和悠远。
百年已过,可园附近已是高楼林立,高架就在咫尺之外,每日车辆川流不息,我们呼啸而去,来不及驻足望一望无声的小园。今人与古人所处环境、生活方式、见闻言思已是截然不同,我们永远也无法回到曾经的可园,还原那样的日子。可园被遗忘在喧哗的闹市里,古时文人的那份情怀也遗落其中,鲜有人再去拾起。而绘画也迷失在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失却宁静,背离传统。在传统日渐式微的今天,在评价标准被利益左右的时代,我们忘了初衷,忘了纯粹。
在可园流连,从骄阳当空到日暮西下,终于还是要离开。走出可园,尘嚣扑面而来,可生活总是要继续,我们还是得义无返顾地在浊世里漂浮。与可园的一顾,就像是走入了一场旧梦,梦里有幽远的琴声、有袅袅的云烟,有永不退色的苍翠、有四时竞艳的群芳,有身着长衫的人们畅怀高谈、有立于窗前的画家揽袖执笔。梦里一切都已久远,泛着淡淡的昏黄,似乎真切地存在着,又似乎缥缈地无踪可寻。斯人已去百年,空余可园静立,多么庆幸我们还有这处园林,还有那一幅幅画卷,可供我们缅怀、供我们追寻。世事纷乱,我们不时还是要来到可园,要展开尘封的画卷,寻觅那一片绿意,做一场久违的梦,找回那个安静的自己。
熊天涵 广州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 谢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