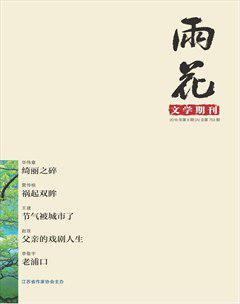三棵树
范燕慧
一
一千年,还是两千年?最早,说这棵银杏树是三国孙权的母亲栽下的,那时孙权18岁,骑白马,当阳羡长,统管一县。后来说时间不太对,栽树的人,不是孙母了。坚持的人说,不是孙母,又是谁,能让一棵树活两千年?
反正,岁月太深。就连村子里最年长的老人,似乎也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先有这棵参天银杏,还是先有这个小村落。仿佛开天辟地,它就在那里,枝繁叶茂,沉默不语。
太湖西岸。杏花烟雨,风过四季。这个名叫双桥的渎边小村,与周边的村庄并无二致。村里小河,清亮宁静;房舍错落,鸡犬相闻;石拱桥边,那棵面目苍老的银杏,就像熟悉不过的自家人,经年累月,任凭人们在她身边来来往往、出出进进,似乎并不在意是否得到过额外的关照和留意。然而,村庄却因此树而闻名,方圆百里的人们都知道,双桥有棵白果树;而说到白果树,定然知道就是指双桥。
白果树长在隔壁的河西队。其实早就没有生产队了,但人们还是习惯称队。那树,离我家仅有几步之遥。儿时的距离感,往往并不准确,过两顶桥才能到达的白果树,在我的记忆里,总是有点遥远的样子。记得少时,人们有事没事,都喜欢在白果树下集聚。摇着饭碗、端着茶缸;饭碗不是用来摇的,但端着饭碗唠嗑,于碗中稀薄的农人,是一种别致的逍遥。农闲的时候,干脆是从午后到黄昏,女人或做针线,男人闲聊或下棋。而小孩子们,更是把树下那一片场院,当作游戏的乐园。跳皮筋,踢石子,追追打打。而常做的一项游戏,就是几个小伙伴去合抱大树,四个或者五个,甚至更多,拉着手,仰着头,贴着树,相互看不见对方的脸,只听见彼此笑闹的声音。
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时光。如果不是后来的生活变故丛生,我和双桥的联系,或许会比现在更紧密一些。只可惜世事难料,变迁无定。十八岁那年,母亲病殁,家也随之没了。人如浮萍草芥,无奈随命运摆弄。我与双桥,就此逐渐断了形式上的联系与亲近。年少之时的孤苦离散,以及亲情的计较凉薄,在当时虽有年轻可以抵挡,却始终不敌记忆鲜明持久,几经岁月钝化,终于绵延成内心的隐痛,苦苦纠缠,挥之不去。因此,对于故土,以及那些我血缘意义上的亲人,我始终心有隔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奇怪的是,形式上的疏离,却并未影响精神上的长久维系与相依。浮生半世,兜兜转转。生命中于我而言所有重大的事件,断断续续,反反复复,都在梦里,在双桥重新演绎。譬如出嫁。多少年来,总是细节生动地一遍又一遍再现在梦境里。梦里也在疑问:为何不是别处?为何还在此地?
醒来也疑惑。搬家已然五六次,而梦里头念念不忘的家,怎么永远都在那棵白果树下?
找不到答案。但我愿意相信,桥边的银杏树,是知道缘故的。两千年,都够沧海桑田好几回了。看护一个村庄那么久,定然知晓祖辈血脉中最隐秘的关联,以及冥冥之中情感的超拔与微妙,至于尘世之中的那些人情厚薄、起伏跌宕、欢聚离散,在悠长得看不到尽头的时间河流中,以她两千年沧桑睿智的目光,恐怕连朵浪花也算不上。
是的。生命之中,总会有些东西让人无法言说和承受,无论先后,无论轻重,都逃不过时间的稀释和缘分的左右。法不孤起,必仗缘生。某些梳理和领悟,不是不做,不是不来,而是在静静等待,等待某个时机的到来。
丙申初五,午后,雾霭散尽,阳光正好。我迫不及待地去双桥,不仅仅为形式上的看望,更是为了去感受和呼吸白果树修炼千年的气场。
尘霜满面。第一眼就把我惊到。枯枝已然爆满新芽,齐刷刷直指蓝天碧空。苍老和遒劲,如同层次丰富充满张力的油画,逼近我的视线。
树下遇见乡亲,面熟却不相识。
“两千年了,这么长。”我感叹。
“是啊,有年代了呢。”见我徘徊树下,语气骄傲地主动应答。
“记得有个疤,怎么找不见?”
“诺,在那。截去的那个枝桠,比现在任何一个都大,做了三十多张泥凳呢。”
“哦,是紫砂一厂的师傅下乡教学徒的时候做的吗?”
“是啊,这批泥凳,质量好着呢,如今取都取不到了。那时候教的第一批学徒,现在都是大师级别了呢。咦,你怎么知道,你是双桥人吗,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没有告诉他,那一批泥凳,其实我家也分到了一张。母亲,也是那批学徒中的一员。
泥凳,并不是凳子,而是紫砂艺人用来制壶的工作台。为什么把台子说成凳子,村里没人说得清楚。或许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泥凳是一个艺人的气场,所有的敲敲打打、转转捏捏,都在泥凳上进行。老艺人的泥凳总是光亮的,沾满着岁月的旧气。最寒酸的艺人,也会讲究泥凳的料子,那不是脸面,是实力,是一种实打实的份量,碗里的粥可以薄些,泥凳的料子,无论如何,要厚些、再厚些。
那棵银杏树,成全了多少紫砂壶、又成全了多少紫砂艺人呢。拥有一张用银杏树料做成的泥凳,在双桥村,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资历。
快四十年了,树上被截去的那个枝桠,疤痕已被新长的枝桠所覆盖,不细看,已经难以发现。如若树也有知觉,那么当初的断肢卸甲,应该也是痛不欲生。三十多张泥凳,在贫穷年代里成全过的家庭,以及每一天在泥凳上诞生过的紫砂壶,是疗愈伤疤的良药吗?而母亲用过的那一张,是不是也躲在某个安静的地方,每天都在成全着鲜活的作品,成全着某个艺术生命呢?
如若渡尽劫波,可获意外重生。那么,当初的疼痛,可不可以是另外一种成全?此刻,我唏嘘在当下,树默然已千年。
无声告别。我拍下树的编号,这棵世界上最古老的孑遗植物,正以蓬勃的姿态,迎接她第二千零一个春天。马上,又是一年枝叶招展,硕果累累。
二
甲午年秋天。一个晴朗的早上。在柬埔寨王宫的花园里,我见到了佛教传说中久负盛名的无忧树。那一刻,四周喧闹而又宁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熙熙攘攘,怀揣着不同的目的和心情,在佛国明朗的阳光里缤纷而行。柬埔寨气候炎热,植被茂盛,空气洁净,每一次自由的呼吸,都会令眼鼻心肺舒畅无比。水,空气,食物,这些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基本要素,在这个目前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度,却都质地上乘,让人羡慕。可见世间事物,果然是各有利弊。置身于稠人广众的王宫圣地,不时有微风送来清凉的气息,内心的放松和畅快,就这样轻易被填满了。随行的朋友告诉我,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某个春天,确切地说,是四月,佛祖释迦牟尼,就降生在蓝毗尼花园的无忧树下。
蓝毗尼,在尼泊尔。《过去现在因果经》中,曾这样描述佛祖出生的情景:“夫人见彼园中有一大树,名曰无忧,华色香鲜,枝叶分布,极为茂盛,即举右手,欲牵摘之,菩萨渐渐从右肋出。”经书中所提及的夫人,即为摩耶,是佛祖的母亲。
有限的佛教知识告诉我,小乘佛教,是柬埔寨的国教。这样说来,世间稀有的无忧树,能在柬埔寨的王宫里生根开花,肯定是佛祖在冥冥之中作了某些安排。但凡奇花异树,一旦与宗教结缘,就必定吸引众生的目光,或被视作祥瑞,或教人无端敬畏。而一棵与佛祖有缘的树,一棵见之能忘忧的树,在人们的想象中,必定拥有巨大的能量与灵性,或能解除愁苦,或能施布福泽,这才引得众生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心生向往而顶礼膜拜。于是,来自大千世界的虔诚之心、向佛之心、好奇之心,乃至欲望之心,如百川归海,纷纷在此地汇集,在一棵名叫无忧的树下,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不约而同,来寻求某种解脱、安慰、满足和宁静。
佛法博大精深,我般凡夫俗子,自然难以参透,而对于未知的陌生,却从来都不缺乏探究的好奇。身边的人流,如恒河之水,川流不息;那一日,我于树下静默,满心期待会有神秘的力量悄然降临,来满足我未了的愿望,解除我今生的愁苦。于是,我额首,闭目,静心,敛神。不放过身心任何一丝幽微的变化和感受,企图在这神秘的无忧佛国,获得某种开示和领悟。伫立良久。然而,除了远处缥缈的佛音,以及自己悠长的呼吸,我所有的专注,仿佛都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是我宿慧不深,还是我不够虔诚?抑或是烦恼太多,欲望丛生,连佛缘深厚的无忧树,也不肯帮我?我睁开眼睛,不由得抬头仰视,只见大树上部枝繁叶茂,亭亭如盖;中部以下,却从树干直接长出黄蕊红花,花茎一米有余,仿佛有刺,曲折缠绕,说不出的庄严神秘。而此刻,头顶碧空如洗,眼前花叶分明。如若此树果然有灵性,那么如今我与无忧,近在咫尺,却如隔天地两重,没有丝毫的联接与呼应。一时间,不觉若有所失,心中怅然。
也罢。红尘烦恼,本是今生的修行。能与无忧树如此亲近,即便是作片刻的停留,也已然是缘分,更何况,得与不得之间,本就没有清晰的界限。而我也相信,佛祖慈悲,所有的安排,必然自有深意。
于是,释然,放下。
从柬埔寨回来,故园已是深秋。寻常的日子里俗事纷扰,高远莫测的无忧树,渐渐在我的记忆里模糊淡去,只剩下一帧帧安静的照片,存于我的手机相册里。
直到一年以后的某一天。是冬季,下着雨。中午时分,我像往常一样换上运动装备,撑着伞去单位一墙之隔的森林公园走路。回想这一年里,换岗位,添烦心;事务纷乱、抽丝剥茧,日子过得异常辛苦。午间走路,几乎成了我解压和锻炼并重的生活方式。我按照常走的路径,沿着小水库绕行。天气骤变,此时,已是冷雨交加,寒气逼人,天地之间,似只有我一个人在雨中独行。远远瞥见有一老汉,像是公园里干活刈草的杂工,穿着雨衣,挎着竹篮,迎面走来。大概见我空手,又着装休闲,仿佛叹气似的对我说:“这样的天气,还出来旅游啊。”
“老师傅,我不是旅游,只是走路散心。”
“哦。”老汉看了看天,又看了看我,说:“真是好福气,不过老天爷倒是公平,他会把每个人的力气都收走。”
一时间怔住。
“老师傅,此话怎讲?”
“像我们出力气的人,能歇会儿,就是福气。怎么会专门去走路呢。”
一拐弯,老汉不见了。
一阵寒风袭来,脑子里仿佛清静了许多。
原来,各人眼里的世界,居然是如此不同啊。劳心,劳力,皆是劳动;而力气多寡,是心生的。我所不欲不喜,或许正是他人所欲所喜;而我所喜所欲,或是他人不喜不欲。众生众心,佛祖定然看得分明。既有所求,就有喜乐哀苦,岂能无忧?既有所比,必有计较委屈,怎能无忧?既有所欲,定有爱恨执着,何来无忧?
我呆立雨中,望湖面碧水寒波,烟雨朦胧,然心中澄明,往日心头种种,如同尘头落地。佛祖有大智慧,他早就知道,忧虽不能无,然忧尤可忘。忘与不忘,全在自己,一念地狱,一念天堂。
一瞬间,我仿佛看见,远方的万里晴空下,无忧花嫣然浅笑,无忧树亭亭如华。
三
一直以来,我都深信,大凡汉语的词汇,皆为自带独特意象的精灵。比如“菩提”,总是带着平和玄妙的气场,稳稳地来到我的眼前。觉悟,智慧;温暖,慈悲。我见着它,思绪就会不由自主地超拔辽远,联想起天地万物,神灵神祗,水火金木;还有时间,生死,轮回,因果;以及统领万物众生而无处不在的“道”。
至于菩提树,只怪那首偈语,流传得太深太广。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让我一直误以为所谓的菩提树,只不过是一个传说,犹如神一般的存在。
而在佛教里,菩提树的确是神一般的存在。如果我们站在时间的制高点上,让目光穿越千年,也许可以看得见,某一日,乔达摩·悉达多从沙雾中走来,捧着钵,赤着脚,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太热了。太渴了。太累了。极目四顾,恰好发现河岸上有棵菩提树,于是,他踉跄着朝树下走去,走到叶子下面,闭目。盘腿。坐定。一阵荫凉袭来,思绪突然如电光石火,穿云破雾;眼耳鼻舌身意,顷刻间无比澄明。想通了。彻悟了。这一路走来,佛陀必定是穿越了无数的山川、河谷和森林,长途跋涉,忧思无果,偶然来到菩提树下,偏巧在那里悟得了正道。于是,菩提树,理所当然地成了众生膜拜的神圣之树。
如果不去印度,我想一睹菩提树真容的好奇心,也不会那么强烈。然而因工作关系,庚寅年初,我居然去了一趟印度。
时光深处的印度,就是古老传说中的西天。而老百姓的“上西天”,便是赴死。遥远和死,都系在一个名叫唐玄奘的僧人名下。他带着徒弟,远赴西天取经,一路山水迢递,凶险无比,最后九死一生,修成正果。但在吴承恩的描述里,那天竺之地,却尽是花草松篁,鸾凤鹤鹿,霞光瑞气之类灵光闪耀的字眼,可谓处处暗香浮动,犹如人间圣境。而“菩提”,正是那仙境中的主打植物。因此,以我对印度的有限了解,加上《西游记》给我的无限想象,心里早就认定了印度必定是处处祥云缭绕,异香扑鼻,幽深莫测;菩提树也定然遮天蔽日,灵鸟梵音,清越绵长,犹如深谷天籁。置身印度,如同身处仙界,理应从头至脚,神清气爽,恰如醍醐灌顶。然而,从海德拉巴,一路行至德里,所见所闻,却让我大跌眼镜。
如同冷不丁推开了一扇陈旧的垃圾箱的大门,一个无比肮脏杂乱的景象,铺天盖地,轰轰烈烈,无遮无拦地扑面而来。这巨大的落差,让我猝不及防,目瞪口呆。一个天大的嘲讽。千奇百怪的混乱,如同一头怪兽,张着滑稽的大嘴巴,得意地嘲笑我的孤陋寡闻和自以为是。
一个旧世界。拥挤。破烂。杂乱无章。污迹斑斑。各色各样的什物,就像刚刚从某辆看不见的大卡车上倾倒出来,散布各处。车辆,商铺,小吃摊;垃圾,帐篷,流浪汉;猫狗,菜场,废墟,乞丐……这里就是一个二手货的天堂。令人眼花缭乱的旧物,汗津津,油腻腻,灰扑扑,充斥在街道、巷子、建筑和空地里,横七竖八,东拉西扯,密密麻麻,前呼后拥,千姿百态……
无数只腾空而起的苍蝇,打消了我试图买些水果的念头;“one dollar,one dollar”,一群群争先恐后大小不一的流浪儿童,围追堵截式的乞讨,迫使我急切地想要逃离……遮天蔽日的菩提树呢?霞光瑞气的人间圣境呢?惊异无比。疑窦丛生。虽说佛教在印度盛行了几百年后,最后已不传于印度,但慈悲普渡的佛陀,如何眼见得道之处的众生这般受苦?
不过,凡夫俗子们或许有理由相信,这说不定正契合了佛陀的某种深意。因为几乎所有的印度人,仿佛都对眼前的脏乱熟视无睹,而且都在这无边的脏乱里生活得兴致勃勃,热气腾腾,风生水起。他们不修今生,但求来世,安心于种姓制度的森严等级里,以现世的造业,换得来世的福报。好吧。现世既为幻象,那么繁华抑或荒芜,有序还是混乱,贫穷或者富有,似乎也没什么区别吧。
此行出差印度的目的,是学习。因为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世界领先。作为全球从事BPO业务最多的国家,印度被当之无愧地称为“世界办公室”。而在海德拉巴,拜访过的萨蒂扬软件园,就是全球性信息技术咨询和服务的供应商,满足最严格的国际质量标准。管理严谨,装备豪华,技术先进,令人叹为观止。看着眼前满大街杂乱散漫肮脏到令人发指的生活现场,我已经搞不清楚,哪一个版本,更接近于真实的印度。也或者,印度本来就有两套系统,虽然冰火两重,却能互不干扰,安之若素?
在印度,除了从接待我们的萨蒂扬副总裁的表情里,感受到过些许傲慢的神情,对于眼前这个执着狂欢于生死轮回中的印度,这个还在为人口马上可以超越中国而欢欣鼓舞的印度,我看不出有丝毫的焦虑和野心。
困惑也好,失望也罢。谜一样的印度,令人神往的菩提树,都随着时间如灰尘般飘落在记忆的深处。直到四年之后。
甲午年夏天,我在台湾中台禅寺,太偶然地从导游口中得知,禅寺进门处那棵枝桠横斜的树,就是久负盛名的菩提树。
顿时,我仿佛有一种骤然惊醒的感觉。
无论形态还是枝叶,她都在释放着一种彻骨的普通。太普通了。菩提树,简直就是一个寻常陋巷中走出的布衣平民,没有亭亭而立,没有仙风道骨,没有玉树临风。通体的素朴、安然、静默,在寻常慵懒的阳光里,一副散淡、随遇而安的样子。
或许,是菩提树果真有灵性,它知道,绚烂终将归于平淡,时间唯一不能吞没的,不是杰出,不是不朽,而是普通。而唯有平常,方能持久?!
后来……
其实后来什么也没有。上苍并未格外恩赐我那么多的奇遇和点化。只是有一天,我在无意间又与“菩提”这个词汇相遇。突然间,感受到一种平和的温暖。细细品味,它并不来自天外,而是源于我的内心。我终于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许多能够永恒的东西,只是因为它们被赋予了意义。而菩提的意义,至少接通了慈悲、护生、真爱、包容。她外形的普通就像普天下的苍生。所以她被全世界有爱心的普通人用心去滋养、传颂,成为众心供奉、万古长青的理由。
回想起在印度所见的种种,我也已然深信,菩提树,也肯定长在每个印度人的心里,融入了他们的血液里,所以,他们才会在面对万千世相时,不忧不喜,不憎不惧;并用超然物外的境界和智慧,引渡此生,享受世界。
由此,我知道了,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得意抑或失意;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在心里栽一棵菩提树。而在我们的周围,只要我们肯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一片片菩提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