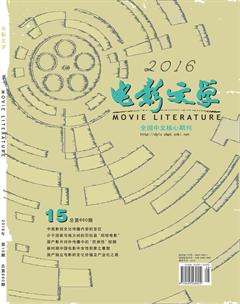《地下铁》的叙事机制
谭敏
[摘要]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地下铁》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成功地运用了电影叙事机制,通过巧妙组合画面、音乐、声音、语言等多种电影叙述材料,成功地实现了从文学叙事到电影叙事的过渡和转换。通过创造性地在情节和画面、音乐、文字之间建构一种微妙的结构,这部电影既保留了小说原著的内涵,又能引导观众产生新的认知,堪称文学著作改编成电影的成功典范。
[关键词]朱利安·巴恩斯;《地下铁》;电影叙事机制
朱利安·巴恩斯是驰名当代英国文坛的小说家,他的首部小说《地下铁》(Metroland,1980)是一部充满思考和想象的小说佳作,英国导演菲利普·塞维尔(Philip Saville)于1997年将其改编后搬上大银幕。巴恩斯是一位以后现代实验风格著称的小说家,因其多思、睿智而被称赞为一位“聪明的小说家”,将他的作品搬上银幕绝非易事。但该影片上映后获得了广泛好评,欧文·格雷伯曼(Owen Gleiberman)在《每周娱乐》上给该影片评价是A,称其为“一部富有内涵的、沉静的、不矫情的电影”“非常罕见地诚实描画了幸福婚姻中人的复杂欲望”[1]。一部思想内涵深邃、故事情节发展平缓的小说如何被转化为一部成功的文艺类影片,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正如阿尔贝·拉费在其著作《电影逻辑》中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世界与它紧密相伴,它(电影叙事)怎样才能像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一样灵活自如呢?”[2]本文认为该影片成功地运用了电影叙事机制,巧妙地实现了从文学叙事到电影叙事的过渡和转换。通过创造性地在情节和画面、音乐、文字之间建构一种微妙的结构,这部电影引导观众产生新的认知。
一、叙述者和叙事机制
根据传统的观点,任何叙事都意味着有一位叙述者,文字叙事的叙述者很容易辨认,但电影中的一切声音和画面似乎都是在自我呈现,叙述策源地对观众而言是隐匿的。当前电影叙事研究基本一致认为,在电影中存在一个基本的叙事机制,即承认有影片叙事陈述负责人的存在。拉费将电影中观众看不到的叙述者称为“大影像师”,他认为(电影)叙事由一个“画面操纵者”、一个“大影像师安排”。“大影像师”并非指一个具体的人或物,而是一个看不见的叙述策源地,一种操纵画面的机制。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在回答“谁讲述影片”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基本叙述者、影片叙事交流的负责人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机制,他操作各种各样的影片表现材料,对其作出安排,组织其叙述方式,制定其活动策略,以此向观众提供各种叙事信息。”[2]安德烈认为,通过策略性地组合画面、音响、话语、文字、音乐这些材料,完全可以构建一种所谓“影片话语化的程序”的“叙事体系”[2]。受此启发,本文试图通过捕捉“大影像师”的踪迹,即解读该电影的叙事机制,来深入解析该影片,并比较其与同名小说叙事之间的联系和异同。
电影《地下铁》由三个完整的情节段落构成,基本对应巴恩斯的同名小说,但打破了小说的时序。电影从1977年在伦敦郊区过着平稳乏味的婚姻生活的克里斯接到儿时好友托尼的电话开始倒叙,躺在床上的克里斯开始追忆1968年在巴黎与女友的邂逅、亲密同居到分手的过程,其中数次闪回至1963年,追溯学生时代的克里斯与托尼充满叛逆的青春。这样的处理似乎把小说中按时间顺序进行单线叙事的结构变成了嵌套叙事,诱使观众假设克里斯作为叙述者。但其实这只是一种观众的假设,事实上,克里斯本人同影片中其他人物一样从外部被展示,和其他人物一样都有自己的声音。根据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的电影叙事理论,电影在第一层次总是在讲述,而呈现出来的视觉化的叙述者进行的是“讲述下的讲述”,视觉化的叙述者从事的叙事活动是次叙事,影片唯一的真正的叙述者只能是暗隐的“大影像师”。[2]因此,克里斯这样的人物角色其实是“代理叙述者”或 “第二叙述者”,他的讲述活动是“大影像师”安排的叙事机制中的一部分。那么“大影像师”如何将小说文本中的叙述者变成电影中的“代理叙述者”?“大影像师”如何将小说原著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在银幕上呈现?下文拟分析《地下铁》中“大影像师”通过音乐、声音、语言、文字与画面的组合构建电影叙事的过程。
二、音乐、语言与画面
音乐艺术对电影叙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时一段成功的配乐或一首成功的片尾曲为电影获得的赞誉甚至超过影片本身。一般来说,电影音乐分为两种:现实性音乐和功能性音乐。前者也叫客观的音乐,这类音乐在画面上有声音来源,包括在电影的场景中出现的各种音乐,如电影人物或情节中制造的音乐,这类音乐是由剧作家、导演事先在文学剧本中安排的;后者也叫主观音乐,这类音乐在画面上没有声音来源,一般是由作曲家转为电影创作的,着重表现画面中所没有或不能被表现的内容,如人物的心理活动。
电影《地下铁》的片头和片尾曲是由苏格兰吉他手兼词曲作家马克·诺夫勒(Mark Knopfler)创作的同名歌曲,可以说许多观众是为这首精彩的电影歌曲而慕名观影的。伴着吉他弹奏的《地下铁》清新、明快的旋律,影片拉开帷幕,展现的是伦敦郊区克里斯夫妇的平静生活状态。这首乐曲昭示了故事伊始,伦敦郊区中产阶级生活宁静又稍显沉默、单调的生活氛围。儿时好友托尼的造访,勾起克里斯对往事的回忆,并诱惑他浅尝了放纵的滋味。在经历了一场平日压抑的欲望与婚姻道德伦理的挣扎和冲突后,克里斯最终心甘情愿地回归了平日的“平静”状态,继续单调的中产阶级生活。故事结尾,难以入睡的克里斯夜起披衣徘徊于屋外街道,在幻觉中看到前女友安妮可款款走来。幻觉消失之时,妻子玛丽安来到他的身边,问他“什么是幸福?”克里斯面带微笑,平静地回答:“幸福就是,如果现在不抓住,就再也没有了。”两人携手回家,这时响起了马克·诺夫勒用那略带嘶哑的嗓音低声吟唱的片尾曲《地下铁》:“……梦见昨日的欢笑/魔鬼和爱人齐来嬉闹/但梦醒之后是清晨/追逐体面的笼罩/在白日/我抓住了真实的东西/这是我的归属/我知道……” 如果说结尾的对白过于简短、直接、粗略的话,马克·诺夫勒吟唱的歌曲则更能曲折、细致地传递那种集复杂、纠结和清醒、理智于一体的情感状态。这首精彩的片尾曲属于作曲家为电影量身定制的“功能性音乐”,意欲表达主人公复杂的、用对白和语言难以表达的心理活动,是“大影像师”叙事机制的一部分。这段音乐契合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配合画面,婉转、细致地传递了影片要表达的主题:复杂的人性欲望终将臣服于婚姻的道德伦理。
影片中的音乐形式多样、种类丰富。除了属于“功能性音乐”的脍炙人口的片尾曲,影片中还有多首由剧作家或导演在剧本或镜头中安排的“现实性音乐”,如托尼带克里斯参加鼓吹性自由的疯狂聚会上演奏的朋克音乐。朋克音乐诞生于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故事发生的年代,大放异彩。这种音乐风格的特点就是“反叛”——反叛传统,反叛制度,反叛日渐枯燥、毫无激情和意义的生活。朋克音乐用简单的和弦表达简单的情感,他们诅咒战争,却在生活中充满愤怒;他们生活靡乱,但对未来充满向往。这些特点无一不契合托尼的风格,无一不映射了青年时期托尼和克里斯度过的疯狂岁月。将朋克音乐楔入影片中一群放纵的青年聚会的场景,“大影像师”成功地呈现了小说中需多段文字才能解释清楚的“愤怒的一代”的文化,让观众在音乐和画面中体会那种失去理智的疯狂,与托尼后来回归的平静生活形成一种强烈的比对。不仅引导观众选择正确的伦理向度,也触及了艺术与生活的区别这一主题,借助于音乐和画面的组合,“大影像师”将小说中克里斯的心理独白进行了生动传神的呈现:“我们有罪恶感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对艺术的热情是源自生活的空虚。这两个概念如何才能相容?哪儿是平衡点?生活可以是艺术吗?……”[3]朋克音乐曾经将它的愤怒燃烧了英伦三岛和美利坚,但于70年代末接近尾声,因此像克里斯那样曾自诩为“愤怒的一代”的人回归平静的生活似乎也是时代的必然。
三、声音、文字与画面
相对于电影,小说中叙述者的声音定位比较简单,通常用代词就能明确指示发出声音的叙述者,用时态就能指示发出声音的时间,但在电影中,因为要通过演员——人物的声音才能确认演员——叙述者的声音,难以像小说那样轻松表达叙述者声音的语法和时态。但声音的音色可以作为电影叙述的标志,通过声音音色的变化,我们能够察觉外加声音怎样变成画内音。
小说《地下铁》中屡见大段的文字描述主人公克里斯在平静生活的表象下内心的焦灼。如第三章“地下铁II(1977)”开篇就是一段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独白:“想想我伪装得这么好也真是够让自己吃惊的。年龄:30/ 婚姻状况:已婚/ 孩子:一个/工作:一份/房子:一幢/是否有抵押:是……”[3]这样的文字如何搬上银幕呢?《地下铁》的“大影像师”是这么处理的:画面上的克里斯夜不能寐,披衣而起,一个人深夜在街道散步,这时响起了外加声音:“克里斯,为什么你起床出门溜达?”“没什么,我只是想一些事情。”“想什么事情?”“没什么,就是想些关于过去、将来、生活意义之类的事情。我在头脑里列清单。”“什么样的清单?”“你知道,有的人晚上睡不着觉就数羊,我却靠列清单。”接着就是从小说中直接移植上段引文中的清单,这时,画面转回到克里斯夫妇卧室的床上,此时观众才明白,原来这段对话发生在克里斯与玛丽安之间,电影通过夜不能寐的克里斯深夜外出的镜头表现主人公内心的焦灼,但究竟为何焦灼呢?“大影像师”则通过对话,将外出画面拉回到前一个镜头,此时对话又变成了画内音。他向妻子坦言自己焦虑,却不知为何焦虑,于是通过列清单的方式让自己入睡。通过声音与画面的分离,旋即又拉回画面,“大影像师”巧妙地将人物的复杂心理搬上了银幕,保留了小说原著的思想内涵。
影片还通过原生内听觉聚焦的方式来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原生内听觉聚焦”是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在《什么是电影叙事学》中提出的概念,因为电影中有时难以对声音发源地进行辨识,不容易知道声音是否经过某一人物耳朵的过滤,因此“大影像师”将声音发生某些畸变(如:水下游泳者呼吸困难的特殊声音),造成一种特殊的听觉,将一种不可见的机制表达出来。以另一个克里斯夜不能寐的镜头为例,辗转难眠的克里斯耳边响起了安妮可的声音,“大影像师”故意将安妮可的声音加上浓重的回声效果,一为怀旧,二为表示听觉聚焦者克里斯此时正处于精神恍惚状态。安妮可问他:“我原以为你去巴黎是想成为艺术家的。”这时,画面上突然出现了托尼坐在克里斯的床边,接着安妮可的话,同样是用特殊技术处理过的声音诘问克里斯:“看看十年以后的你在做些什么吧!你的住处离你长大的地方不到一英里,干着一项让你自己都感到鄙夷的工作。”一个原本简单的画面,通过加入叙述者幻听幻觉的声音和影像,呈现了原著小说中叙述者在平庸生活中饱受内心挣扎和折磨的过程。通过画面和声音的巧妙结合,传达了深刻的思想意蕴。
四、结语
虽然巴恩斯的小说《地下铁》中含有大量关于人生的哲学思考,其小说叙述者用心理独白、意识流或自由间接引语等方式呈现大段复杂的心理活动,但改编过的电影基本保留了原著的思想内涵,这是“大影像师”灵活运用电影的多种叙事材料成功构建一个合适的叙事机制的结果。《地下铁》的电影改编可称为文学著作改编电影的成功典范。
[课题项目]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现实·现代·后现代:朱利安·巴恩斯的创作风格研究”(项目编号:TJWW13-038)的成果之一;中国民航大学科研基金(项目编号:2012kyh02)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Metroland(film)[OL].Wiki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troland_(film).
[2] [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 Barnes, Julian.Metroland[M].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