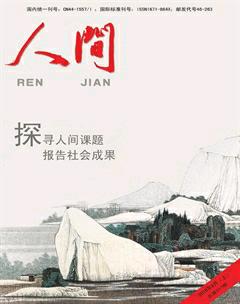庄周“逍遥”的境界之辨
冯磊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庄周“逍遥”的境界之辨
冯磊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一提到庄子,就不得不说庄子的逍遥游,一说到逍遥游,就不得不讲鲲鹏、蜩与学鸠的故事。物各其性是不论大鹏鸟、鲲鱼,还是蜩与学鸠,翱翔九万里是逍遥,决起而飞也是快乐,逍遥和快乐在境界上是有不同的,正如西方哲学所追求最高的善,即至善,也是没有庄子所说的逍遥游的境界高。
庄子;逍遥;逍遥游
逍遥游已经成为了道家的境界高地,特别是庄子的代名词。西晋庄学的研究大家郭象在对《庄子》一书作注时,这样写道,“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1],郭象理解的逍遥游大概是鲲鹏,蜩与学鸠,都有体积大小之分,鹏的背几乎几千里,翅膀像云彩一样。虽然体积有大小之分,但是他们的逍遥只有鲲鹏、蜩与学鸠自己才会体会,鲲鹏有鲲鹏的逍遥,蜩与学鸠也有他们自己的逍遥,快乐。
逍遥应当是只有鲲鹏的翱翔万里,才可以称之为逍遥,纵横万里。当然,蜩与学鸠的快乐是应自由,如果称之为逍遥,确有不当,庄子的思想和他的文风一样,汪洋恣肆、天马行空。我们是猜不透、抓不着,就像庄周梦蝶一样,是蝴蝶在梦我,还是我在梦蝴蝶。鲲鹏之大我们只能遥想,不可比划,所以说,这样的情形,似乎只有庄子才可以想得出来。
一、“逍遥”境界之源
大鹏鸟的志向在天池,因此它会不远万里,长途跋涉,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它进取的目标,而蜩与学鸠在自己的生存模式下,只需要吃饱,徜徉于它的领地即是快乐的。虽然蜩与学鸠的快乐的获得,比鲲鹏获得的快乐看起来简单得多,但是它们可以“物各其性”,从而获得快乐的形式有所不同,其实它们各有各的快乐。对于快乐的理解,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这样写到,“既然快乐被一切生命物追求,这就表明它对于所有生命物是最高善”[2]。西方哲学把追求所有的目的,叫做至善,快乐也就和善的可以划约等号,而东方哲学中,特别是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逍遥境界是比快乐更高一层的,所以我也可以给“逍遥”做另一个西方式定义,那就是“至乐”,以此来区别西方式的“至善”。
庄子的逍遥境界,不仅是超越现实,更是超越未来。在那个农耕的奴隶社会,温饱基本上是人们的普遍追求,只有诸侯贵族们或许才会享受生活。而庄子这样的哲学家就去思考人生,感受人生,实属不易。或许正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庄子在寻求一种出仕的人生态度,我们现在看起来道家是消极避世,我更愿意说庄子在寻求另一种超脱的生活。
二、“逍遥”境界之辨
庄子的内篇——逍遥游,为我们讲到了鲲鹏之大,迁徙至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2]庄子通过极其夸张的手法,把鹏的状态为我们展现在眼前。或许庄子在他那个时代也是道听途说有鲲鹏这样的巨物,但庄子借物表意,给予我们无尽的想象。庄子认为,一个人应当突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使精神活动达到优游自在,无牵挂、无阻碍的境地。全篇以奇特的想象和浪漫的色彩,用寓言和比喻的方法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使人的精神活动入乎优游自在、无拘无束的境地,必须顺其自然,超脱现实,明“无用之用”,臻于“无己”、“无功”、“无名”之境,将自己与万物混为一体,而切不可为外物所役,为功名利禄、权势尊位所束缚。
晋代的郭象和唐朝的道士成玄英,都是是研究庄子的大家,他们研究的角度和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在解释《逍遥游》中的鲲鹏与蜩、学鸠的对比上,二人的理解大致相同,都主张物各异其性,性各异其情,不应按照一个统一的要求来衡量是否逍遥自由。大鹏抟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虽然远近相差很大,在适性方面来说是一样的,各自都能尽己之能,取得自由。故而,“虽复升沉性殊,逍遥一也。亦犹死生聚散,所遇斯适,千变万化,未始非吾。”应当说,这样的解释是违背了庄子《逍遥游》本旨的。后人多承袭两人的观点,是没有理解透庄子的思想在达观中蕴涵着进取。《逍遥游》中所讲的明乎“小大之辩”。人不论能力大小,只要善于积累,立志高远,那么即使如蜩、学鸠般决起榆枋,如芥为之舟般游于坳堂,也是以积极态度的态度入世。“天生我才必有用,直挂云帆济沧海”。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终有展翅高飞的时候。
三、“逍遥”之境界
庄子的《逍遥游》中是开篇是这样来介绍他的逍遥境界的。庄子运用寓言的笔法,大笔挥洒,以描写神奇莫测的巨鲲大鹏开端,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雄奇壮丽的画卷:在那无风洪波百丈,溟溟无端崖的海中,有一条“不知其几千里”长的巨鲲,它竟又变化为一只大鹏,当它腾空而飞之时,断绝云气,背负青天,垂阴布影,若天边弥漫之云。这只鸟并不甘心在荒凉的北冥蛰居,它向往“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自由翱翔,它向往南冥的生活,于是,它振翅奋飞,击水三千,然后盘旋而上,高飞九万,飞至半年,到达天池,才满志而息。在文中,他先是以大鹏形体之大、飞翔之高、凭借风力之厚和蜩与学鸠形体之小、飞行之低、凭借风力之薄作对比,描绘了不畏艰难险阻、执著于自己的追求、展翅翱翔的大鹏形象,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安于现状、不知进取、没有追求的蜩与学鸠。“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九万里而南为?’”对于学鸠的嘲讽,庄子斥责曰:“之二虫又何知!”。接着,庄子转而从生命的长度上来论述见识的差异。他展开想象,虚构出了以“五百岁为春,以五百岁为秋”的冥灵甚至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并提出了“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观点,并由此得出结论:此小大之辩也。他善于运用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毫不吝惜,却又真诚无比。
逍遥是一种优游自得,无拘无束,不受羁绊的生活。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一切相对价值观念,如尊卑、贵贱、高下、大小、美丑、善恶、得失、是非……所引生的惶恐和争斗。耳目的错觉和欲望的纷驰都会被净化,因之,一切人为加诸于人类身心的羁绊也都解除,人生便能获得自在逍遥的境界了。
[1]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庄子集释卷一上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 2013
[2]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 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290页.北京,中华书局 . 2015
[3]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庄子集释卷一上第5页.北京,中华书局. 2013
B223.5
A
1671-864X(2016)08-0150-01
冯磊(1992-10-14-), 男,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专业: 伦理学,研究方向:陕北、关中民俗伦理道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