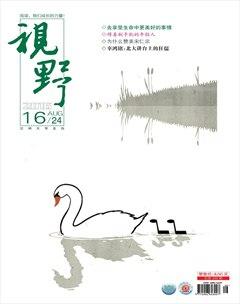古老的宇宙人
犀牛大哥
朋友夏楠说,印度人是古老的宇宙人。
讲一个我在印度遇见的最“印度”的段子:朋友下楼去要水,带着空瓶子和一只保温杯(在印度喝水只能喝瓶装水),到柜台跟酒店员工用英文说,我要一瓶这个,还有热水。
那个员工面有难色地看着她。
啊……好的。

说完印度员工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用托盘捧着一只瓶装水进来,躬身递过来,您的水。
她接过来一摸,热的!
不知这位瘦高的旁遮普小伙儿用什么神奇的方法加热一瓶矿泉水,反正他办到了。
一次过满足两个要求,嗯哼。
我记得看过一个关于昌迪加尔的视频,里面拍到一个给人剃头剃胡子的老人。
黑白片粗颗粒的画面里,一段残墙前挂着镜子,旁边是宽广的林荫道,没有人。
今天我在突突车上探出身子时也真切地看到了那样一个角落,只有0.5秒,滴答滴答,滴的一声,红砖墙,方块镜子,一把深棕色的木头椅子,一个戴太阳帽,浅粉色衬衣,白色马甲的中年人站在那。
就那么一瞬间,相隔几年的两个点就连接上了。
早上醒来,明白窗外的气味是近似七岁回安徽老家时闻到的味道,一种属于乡下的味道,由泥土、粪便、家禽、枯叶和植被混合而成。大约五十米外,一个男人坐在天台中浅色塑料扶椅上沉思,在他对面,是另一户家的媳妇带着孩子在阳台上踱步。打开窗能听见远处的汽车发动马达,小贩骑着单车吆喝着兜售蔬菜,尾音拉长,居然有些像中文。鸟叫声都集中在两百米外的大树上面,开窗探头,一楼厨房里,两个杂役,一个谢顶一个戴红色太阳帽。
因为进食太多豆类,肚子整天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鼻子塞了一半,呼吸声用力,嘴里发干,吞咽唾沫。周围都是声音,翻书声,身体转动时裤子的声响,还有,墙壁真薄,隔壁房间搬进新住客,叽里呱啦的讲话听得一清二楚。每个人都有胃气胀,打嗝声也加进来,远处的狗又开始叫,院子里有人在地上拖动煤气罐,电台音乐听起来都差不多,有反复播放的错觉。在这儿你躲不开音乐,它是印度人生活中最便宜的娱乐。
这里不卖酒,饭馆里只有汽水,有酒吧,但没人建议去一趟,你只有在音乐里一点点麻醉自己。
我记起白天在街道角落里看到的一对母子,儿子还小,在母亲的纱丽中爬行,母亲一脸冷漠地盯着远处,两条法令纹镰刀刻出一般。她的世界里好像没有多少色彩。
在印度无所事事的人太多了,他们的生命有意义么?还是那意义就是为了等候下一次轮回,如果时候到了,你会变成自己见过最幸福的那个人。
有板球比赛,而且是很重要的比赛,巴基斯坦对阵印度,于是所有的印度人,不分员工还是客人,都挤去酒店隔壁房间看直播。他们发出我辈子听过最激烈的哀怨和叫好,撕裂喉咙的尖叫。我躲在房间里看电视,电视播放电影前有非常长的广告,告诉你烟酒对人的害处,认真得好笑,但结合在这里看到的实际情况,又感觉佩服——印度的自觉很有上世纪中国的印记,每个人都知道底线是什么,在哪里,自觉维护,自我监督。
现在的中国不是没有底线,是底线越来越低,标准越来越复杂,变成没有标准。
晚饭前下楼散步,一个老头拉着我聊天,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他的英文口音太重,我听不懂,情急之下他塞给我一张名片,指着自己的名字念给我听。我问印度当地朋友阿班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杂货店啦,他是想跟你做生意。
再往前走有一所小学,学生就快下课了。在那里,阿班指着马路对面,那是我上中学的地方。我们往回走,我问起婚礼的事——就是听说可以参加婚礼我才下决心跑到印度跨年的。阿班说有的,过两天就是,结婚的是我的邻居的儿子,我的邻居是老师,就是刚才那所小学的老师。
她教什么?
什么?
她……是教什么科目的?
她什么都教。语文,数学,英语,什么都教。
两点,小学放学,街上跑过一群穿深蓝色校服的孩子,有个小锡克族包着白色头巾,头巾在额头上方扎成一个小包。很多孩子都直接跑到邻居家,说是来补习。阿班妈妈问我们要不要过去和孩子们打个招呼。孩子们特别激动,过来跟我握手,主动打招呼,要求拍照。
邻居家新装修过,深棕色瓷砖贴墙,柠檬黄的墙壁非常亮眼,新沙发,门口上方摆着一匹金马奔腾,底座有四个中文字:“马上发财”。
我们都笑了,她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
啊……就是,很快,有很多钱。
我在回程的飞机上重看《少年派》,绿色鹦鹉、大象、猴子、山猪,都是平时在印度肉眼所见甚至可以接触的动物,调过色的画面饱和湿润,是焚天的另一个梦。
片头倒影,水中老虎出现,李安的名字也出现,真是恰到好处的心机。
飞机整体新净,但我头顶的阅读灯不亮,找空乘要求解决,重启,还是不亮。乘务员答应回头再试,我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不会再解决了。有人放屁,浓烈的咖喱味儿不知从什么地方一次次地腾起。空姐一脸疲惫地递过饮料和袋装小饼干。
晚餐极难吃,发干的鸡肉卷,古怪的番茄馅儿面包,烧豆饼,没水分的面条,做成呕吐物模样的甜品,没加奶和糖的红茶……进入一个新的文明,了解一个新的国家,就像进入一段婚姻,好坏参半已算幸运了。想要了解,就得先学会妥协。
这顿飞机餐让我真正开始想家了。想家是怀念熟悉的环境,注意,是熟悉而不是便利。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最后一次问空乘灯能修好吗?
他摊手,修不好。
好吧,无用的诚实也很好。
临近降落,我站起来加入到最后一次去洗手间的队伍里。刚站定,飞机恰好倾斜到一个角度,太阳,对印度来说是夕阳,对中国来说是朝阳,正浮在云层之上。云层如玻璃般平滑,是橘红色与灰色的两层玻璃。窗边的印度人也在看,然后,他转身发现了我。
这样的对视在印度发生过多次,但这一次,发生在香港上空的这一次,最简单,也最复杂。
(杨一山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