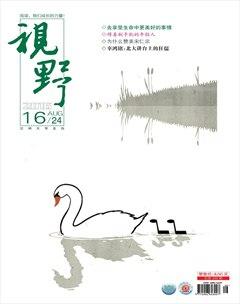古人如何下毒
唐山
翻开史籍,下毒记载比比皆是,但用“毒”代称有害物,或是受外来语影响。
据《说文解字》称:“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可见,古人所说的毒源于植物,可能指的就是乌头(一种植物),以乌头汁液制膏,涂在箭头上,即成毒箭,《魏书》中说匈奴宇文莫槐“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乌头又称射罔,即射后可令鸟兽迷惘。
在英语中,toxic(有毒的)与中文“毒”的发音相近,而toxic出自希腊语,意为箭毒,与东方人的认识竟不谋而合,这或者意味着,“毒”的说法可能来自游牧民族,分别向东、向西传入亚欧。
在先秦典籍中,“毒”常作“害”“治”“征伐”“奴役”解,用作“毒药”反而少见,在甲骨文中,人们常用“蛊”来表示毒药,或者是随草原文明影响增加,“毒”压倒了“蛊”,成为标准称呼。
“蛊”真的那么可怕吗
在毒药中,最传奇的莫过于蛊。
《左传·昭公元年》中说:“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这是史籍中有关蛊毒的最早记载。
汉代之前,蛊多指毒虫,但到了汉代,蛊则成了巫术代名词,指为加害别人而模仿制作的桐木偶,隋代以后,又出现了精神性的蛊,如猫鬼,自唐代始,蛊突然变得复杂、神秘起来。
据《隋书·地理志》称:“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
古人无抗生素,消化道疾病是致死主因,由于无法解释细菌引起的急性腹痛、腹泻等,往往推为蛊,如《说文解字》即称蛊为“腹中虫也”。唐代医学进步,据5100个墓志铭统计,人均寿命达59.3岁。医盛巫弱,巫师需炒作新概念来维持生计,定义模糊的“蛊”恰好契合了他们的需要,制蛊、下蛊、解蛊之说日渐成熟。
其实,不同虫毒化学成分不同,彼此相噬,毒性并未有效累积,不可能获得更强毒性。然而,唐代南方始大规模开发,全国经济中心渐向南偏移,北人对湿热、植物种类多样的南方有恐惧心理,常附会以“蛊”“瘴气”等,柳宗元便称柳州是“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
蛊多靠笔记小说流传,现代人知道蛊,亦与金庸小说有关。
鸩究竟是什么鸟
在用毒史上,鸩的名声不亚于蛊。
古籍中称,鸩是一种鸟,以蝮蛇头为食,肉和羽毛有剧毒,能致人于死,但可用来治疗蛇毒。据郭璞说:“鸩大如鵰(同雕),紫绿色,长颈,赤喙。”而《名医别录》中又说它:“状如孔雀,五色杂斑,高大,黑颈,赤喙。”从古籍看,鸩四处皆有,鸣声如“同力”。
鸩之说在甲骨文中未发现,但在春秋则很普及,据说用鸩的羽毛泡酒,可“入五脏,烂杀人”,无数名人死于其下。配置鸩酒需专业的“鸩者”在犀牛角、兽皮保护下才行,因鸩毒性太大,它的羽毛划过酒,即成剧毒,甚至鸩洗过澡的池塘水也能毒死百兽,但只要犀牛在其中洗一下角,其毒顿解。
鸩酒出现得离奇,消失得也离奇。南朝陶弘景曾说:“昔时皆用鸩毛为毒酒,故名鸩酒。倾来不复尔。”西晋“衣冠南渡”时,“时制,鸩鸟不得过江”,此江应指长江,从此鸩鸟便似乎从历史中消失了,后代虽有鸩酒之说,但只是用来代称毒酒,与鸩鸟已无关。陶弘景曾说鸩鸟“状如孔雀”,唐人则否定说“陶云状如孔雀者,交广人诳也”。
有学者认为,鸩可能是一种已灭绝的鸟,但也有人认为,鸩即今东南亚尚能见到的黑鹤,它也以蛇为食,但无毒,可能是古人以鸩羽拨毒入酒,令人误会为鸩有毒,但更多学者认为,鸩只是一种传说。
水银与黄金有毒吗
在小说中,有用水银下毒和“吞金而死”之说,《水浒》中的宋江死于前,《红楼梦》中的尤二姐死于后,但均属小说家言。
水银不溶于水,进入人体后无法被吸收,汞蒸汽和汞盐会给人带来伤害,但前者需要在1—44毫克/立方米的较高浓度下,人体暴露4至8小时才能中毒,后者常见形式为硫化汞,即朱砂,曾被认为是补品,唐代医家则认识到,朱砂有毒,不能长期服用。
黄金亦不溶于水,甚至不溶于普通的酸碱,黄金制品上多有尖刺,可能刺伤内脏,这会带来较大痛苦,但曹雪芹笔下的尤二姐却又明明是安详地死去。
为什么曹雪芹会认为金有毒呢?因为史书上有金屑酒,是一款名毒,妒后贾南风即死于此,刘禹锡在《马嵬行》中说:“贵人饮金屑,倏忽蕣英莫。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称杨贵妃也死于金屑酒。(此处刘禹锡有误记,史籍明确说明杨贵妃系“缢死”)
显然,曹雪芹在此望文生义,将“药金”误为黄金。“药金”是古代方士提炼出的一种类似黄金的金属,一般指黄铜,在相当时期,“药金”被认为是黄金的一种。古人认为黄金不朽,服之可以延年,但黄金太贵,亦以“药金”替代,可炼制“药金”要使用水银和雄黄、雌黄、砒黄等硫化物,如处理不善,就会成毒,“杀人及百兽”,这才是金屑酒的原材料。
砒霜一统江湖
宋代以后,下毒方法渐趋简单,因砒霜崛起,一统江湖。
砒霜源自天然砒石,以江西信州(今上饶市部分地区)质最优,其中色红者即“鹤顶红”,号为毒物之王,宋代竟“每一两大块者,人竟珍之,不啻千金”。
但,宋代医家甚少关注砒霜,《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均未载,直到《开宝本草》才列入砒霜,也仅称“味苦,酸,有毒。主诸疟,风痰在胸膈,可作吐药。不可久服,能伤人。”李时珍曾奇怪地说:“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雀鼠食少许即死,猫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钱许亦死,虽钩吻、射罔之力不过如此,而宋人著《本草》,不甚言其毒,何哉?”
这或与加工方式有关。宋代制砒霜,是“取山中夹砂石者,烧烟飞作白霜”,这种升华法产量低、质量差,如采用煅烧法,则毒效立增,即砒石末加明矾烤制,明矾遇热融化,裹在砒石末上,防止其中有效成分挥发,成品毒效倍增。
据《天工开物》载,煅烧制霜时,“立者必于上风十余丈外。下风所近,草木皆死。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徙,否则须发尽落”。
《水浒》中,武大郎死于砒霜,但砒霜不易溶于水,用汤药灌远不如混在食物中。砒霜用量小、价格廉,乌头、野葛等已无法与之匹敌,不仅潜入潘金莲这样的寻常人家,连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亦用此药。
(周志明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