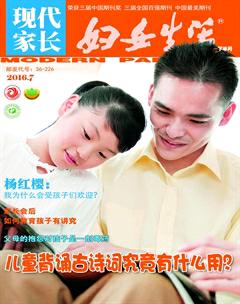尖子生缘何被莫名的头痛困扰
金建云
上小学五年级的孙淘原本学习成绩优异,三四年级的时候经常在奥数比赛中获奖,是老师、同学眼里的尖子生。两年前,他突然得了一种怪病,经常感到头痛,去了多家医院就诊都查不出病因。因为头痛,他不得不经常请假,学习成绩下滑,甚至在关键的奥数比赛中因为突发头痛而放弃考试,令老师非常失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淘的各科成绩都明显下滑,渐渐由尖子生变成了“问题生”。而且,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有时头痛得在地上打滚,可依然查不出病因。后来,医生们都怀疑他的头痛是因为心理问题引发,建议他看心理门诊。
强势的母亲与缺席的父亲
孙淘第一次来咨询,是在他姨妈的陪同下。从他姨妈口中我们了解到孙淘原生家庭的一些情况。孙淘的母亲性格急躁,喜欢掌控。其父离婚前在远航船上工作,极少回家。孙父性格温和,当妻子发火时,他不是退到书房,就是埋头玩游戏,反正不接招儿。
孙淘的爷爷奶奶不愿帮忙带孙子,外公身体不好,看病花了不少钱,孙妈妈一边操持家务一边兼职会计工作。当她辛劳地将儿子带到上小学的年纪时,竟发现丈夫有了外遇,而且对方已经怀孕。
孙妈妈几乎崩溃,一直走不出阴影。两年前,夫妻俩离婚,孙淘由母亲抚养。
离婚后,妈妈以孙淘为“武器”,经常威胁前夫说“再不许你见孩子”。偶尔对方来看孩子迟到,她就带着孩子去别的地方,让前夫恼火。孙淘的爸爸没给儿子买礼物,或是没按时交抚养费时,孙妈妈就会勃然大怒,打电话威胁要到法院去申请取消他的探视权……孙妈妈使用这种最古老、最具杀伤力的情感勒索方式,让身边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场没有胜利的可怕战争。
姨妈无奈地说:“我姐也在接受心理治疗,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助我的外甥,疏导他的情绪,让他不要那么痛。每次看到他头痛得吃不下饭,我们都好担心……其实,这孩子真是清华、北大的好苗子,因为这个耽误学习太可惜了……”
从她的讲述中,我们可以判断孙淘的成长过程中父爱是缺席的。即使父亲在孙淘身边的时候,他给儿子的感觉也是非常消极的——这种消极并不是内心平和,而是因为痛恨自己的伴侣,所以用“沉默不语、躲避退让”来惩罚伴侣和全家人。这种消极的手段在中国家庭非常常见,消极者通过拒绝沟通来挫败、伤害、羞辱那个试图通过沟通将事情变好的一方。这就传递给孩子一种感受:“我爸都受不了我妈,我还能指望谁呢?”
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孩子,易对挫折感到无能为力,缺乏独立精神,甚至会把这种病态心理带入成年后的夫妻关系中。他一方面对妈妈很反感、很失望,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妈妈更强烈的依赖,在“依赖—失望—希望—再失望”的怪圈中不断寻找母爱的温暖。
而妈妈呢,在常年的付出与丈夫的最终背弃中,变得像压路机一样粗鲁——只要儿子有一点不合她的心意,她就一根筋、呼啸着毁灭一切;她使用过激反应来宣泄情绪,而不会表达真正的、根本的、合理的需求。
直面头痛的根源
孙淘是个很清秀的孩子,面部表情不多,看起来很酷。他不承认自己有咨询的必要,他说:“我想知道为什么头痛,是医生在找借口,还是我得了绝症别人不敢告诉我。”他承认晚上总睡不好,还说,“我的确偶尔会向同学动怒,有点暴力倾向。”
我首先对孙淘进行了“情绪词语”的测试与自我检查。我给了他一份情绪词语的测试表格,让他在常有的情绪词语上打钩,比如羞耻感、压力、受挫、折磨、害怕、愤怒、无能、憎恨、软弱、自怜、抑郁、无助等,并检测以上词语带给他的“身体感觉”和“生理反应”,比如脖子痛、肌肉紧张、头晕眼花、喉咙里泛酸水、心绞痛等。
我告诉孙淘,身体会透露真相。当我们说“我还应付得来”的时候,其实发现自己的脸已经很红了;当我们说“一切都正常、我没事儿”时,其实脑海里已经思绪万千了。孙淘渐渐愿意向我打开心扉,回忆他“很想彻底忘记”的事情。比如他说:“我小时候,我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她常常一边用电脑工作,一边监视我。有时候她很忙,就让我坐在固定的地方看书,一动都不能动。如果我动一下,她就会尖叫:‘回去!不许离开我的视线!”
我问:“是不是当你重新一动不动时感到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呢?”
他点头:“嗯,那时候我只有三四岁,但那种感觉记得特别清晰。我的头开始痛,就像里面有一只手在抓来抓去。我坐在那里简直无法呼吸,因为整个头都是僵硬的……”
可以看出,孙淘把“被逼着不许动”的愤怒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体上。因为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肚子痛、头痛、难受,是比“恨妈妈”“恨自己”更容易的。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每次在生气或无助的时候他都有类似的身体反应。
在后续的催眠治疗过程中,孙淘不止一次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情绪,说:“头里面好紧啊,就好像有人在后面用东西戳我的脑袋,我感觉魔鬼在往外面跑,我想说难听的话,还想冲妈妈吼叫!我想杀了她……我想做一些事,证明在这个家里我是老大!没有人可以命令我!我头痛得受不了了!头里面有东西在磨啊磨,我的心快跳出来了……救命啊!”
“空椅子疗法”帮他宣泄情绪
为了让孙淘宣泄情绪,我带他到附近一个学校的操场边,找到一个跟他小时候很像的小男孩,让他想象那个男孩被粗暴对待的样子,然后指导他如何妥善处理自己的不良感受,并让压抑已久的愤怒情绪宣泄出来。我还带他用拳击、打壁球、搏击等略带攻击性的运动缓解身体的紧张与愤怒。
几次治疗以后,我要求他口授一封不会寄出去的“给父亲的信”,将自己的痛苦写出来。
这种表达是主动的、安全的,我允许他用很过激的词语,甚至是诅咒来宣泄情绪。他写道:“当你那天把我一人扔在公交车站,跟那个女人扬长而去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人家踩在脚下的虫子……我真想找个洞钻进去,再也不用去面对妈妈那张暴怒、讨厌的脸……我永远不原谅你,你看不起我们……”
我让助手把这封信打印出来,然后用“空椅子疗法”,让孙淘想象父亲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把信的内容大声念给他听。
这个过程中,孙淘几次头痛得几乎坚持不下去,我一直鼓励他。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孙淘说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跟同学发怒了。其实孙淘对同学的怒气是他对父母愤怒的一部分。治疗中我引导他用积极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积攒的敌意与愤怒,是非常重要的。
用心理自救法学会和妈妈相处
接下来,我建议孙淘将妈妈对他的负面评价一条条写下来,并在每条下做详细的备注,比如做事没效率、拎不清、智商低……当他把这些评价与相应事件写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面存在逻辑错误,根本对不上号。比如:当孙淘事情没做好时,妈妈说他“毫无用处”“窝囊废”;当孙淘展示出能力时,又被妈妈贴上了“自以为是”“太骄傲”等标签。
我让孙淘意识到,与其在妈妈的评价下无所适从,不如撕掉妈妈贴的标签,另寻评价标准重塑自我。
我让孙淘用另外一种颜色的纸,写上别人对他的评价。孙淘发现,这与妈妈给他的评价大有不同!他意识到妈妈对他的种种评价,根本不能反映他真实的样子。但是,这种可笑的评价之所以能够成为“压死骆驼的稻草”,是因为妈妈整天喋喋不休。所以,孙淘需要在脑海里用“正面的评价”建立一座城堡,想象每个正面的评价都是一块砖、一片瓦。
我让他承诺:每一天都要确保脑海中这座城堡的存在,并且让它越来越牢固。当妈妈乱发脾气、口不择言的时候,将她的话语想象为敌人扔来的石头,无法击穿城墙,无法伤害到他一丝一毫。
此外,我还教给孙淘一个“SOS”的心理自救方法:当你快要被“头痛”的感觉笼罩时,立即发出一个信号stop / observe / strategize(停下来争取时间\观察\有策略地选择远离压力)。比如,给小姨打电话、去找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去外婆家住一夜、得到妈妈同意后去同学家玩……
孙淘在经过2个月的治疗后,头痛症状明显减轻。孙妈妈也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努力调整心态,改变与儿子的互动方式。如今,孙淘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每周按约定到学校心理辅导老师那里进行巩固性复查。与此同时,他的学习成绩稳步提升。孙淘的姨妈高兴地告诉我们,孙淘有希望重返学校的奥数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咨询师手记:
病理学(pathology)一词源于希腊语pathos,而pathos一词的意思就是身体和心灵的痛苦。其实,负面情绪对孩子身体的影响并非我们以为的那么短暂、脆弱。即使许多人的周期性抑郁和焦虑是大脑生化失衡的结果,但因为这种伤害而造成的“自我贬低的信念”仍能对各种疼痛推波助澜。
很多因离异而心灵扭曲的单亲妈妈,在过一种“双输”的生活——她诋毁孩子的价值,让周围的人沉浸在内疚之中。最可怕的是,她对此毫无察觉——甚至觉得自己在维持秩序、教孩子做人。所以这些人特别需要孙淘姨妈这样的第三方来帮她们理顺亲子关系,改变生活模式,进入人生下一个明媚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