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 盛可以
我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 盛可以
转眼成了一个写了十三年小说的老作家。“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活得越老,越了解世界的庞大复杂、人性的幽深险恶,对细微的事物、卑微的生命就越是纤细敏感。作为一个生活的观察者,或者说,作为一个偏爱书写悲剧命运的人,内心的脆弱与坚强其实是相等的。面对世界,既有一颗如石头般冷静的心描摹残酷现实,也暗藏着近乎黛玉葬花的神经质的忧愁感伤。
现代化的生活像流水,点到为止,就像无数的新闻、短讯、微博、事件在不断地发生,迅速地被折叠、覆盖、遗忘,人们在痛苦,在遭遇,在变化,那么,小说就是展开这些皱褶,挖掘隐藏的、幽暗的、真实的以及种种可能。
粗略回忆过去的写作,不乏草率与粗糙的处理方式,过于散漫随兴。意识到该这么写,不该那么写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唯一能做的是,更谨慎,更有耐心,像一个出来觅食的动物初出洞口那样,敏感戒备,四下嗅察,避免鲁莽地一下子就跳进危险的处境里。
这些年我所积累的,有很多关于失败的写作经验,我知道自己每一部作品的缺憾,也记得每一篇作品的缘起。我想提一提我的故乡,也就是我的文学的发源地。所谓故乡,只是我出生的村庄与小县城。如果贫穷无助也是一种肥料的话,我倒是得此滋养。当了作家,注定要在困苦落后、民不聊生的灰色底子上写字,提起笔,故乡的人物自然就跳到了纸上。也就是说,在写作之前,就形成的一种感情态度,可能是今后永远无法超越和挣脱的。故乡总有一些怪异、费解的人和事。比如长得好看的女精神病喜欢唱革命歌曲;性格阴郁的瘸子暗恋某一个女人;刚过门几天的新媳妇突然中了邪,不吃不喝;一个经常被丈夫打得皮开肉绽的女人从没想过离婚……
我零碎地知道一点背景,但不去求证模糊的部分,而是去揣测、虚构、处理这个模糊地带,用想象力构建“事实”。几乎每次回乡,都能从乡人的八卦闲聊中获得文学人物与事件。比如长篇小说《北妹》的缘起,听乡人聊起村里那个性感丰满的矮个小姑娘,怎么在村里弄得鸡飞狗跳,最后跟姐夫睡出麻烦后离开村庄。我想象一粒性感的肉丸子到处滚动,新鲜热辣,她会遇到一些什么动物,面对那些要咬她的嘴巴,那些要吃她的人,她会怎么办。于是我就让她一直滚,从乡村滚到县城,从县城滚到现代化大都市,从一种工作滚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男人滚到另一个男人。我扛着摄像机跟在她后面滚。所以《北妹》谈不上写作技巧,也没故事结构,就是一粒肉丸子在路上滚。我从没想过去采访那些姑娘们,我相信我想象的,可能要比她们的回答更丰富、更复杂,甚至更真实,我看到了她们的部分生活,她们的日常,她们那些在报纸上,或者我的耳朵边发生过的事件,但在我的想象中还有更多可能发生。
2008我开始写《死亡赋格》,男主人公在一片水域失踪,那个一望无际的湖就是洞庭湖,我要写洞庭湖的美,洞庭湖的险,但我唯一一次瞥见洞庭湖,是在十岁左右,除了风浪和浊黄的水,再无别的印象。有人建议我先去洞庭湖看看,实地考察一番。我没有兴趣,一方面是担心实景制约想象,二是真的觉得巨大的冒险完全可以来自内心,没必要去看真实的八百里洞庭,大脑里的美和风暴胜于真实。但是毫无疑问,想象又是基于某种印象,我在回忆中放大了童年对洞庭湖的那一瞥,放大了洞庭湖的浊黄与风浪,几十年前的那一瞥,依然至关重要。
小时候对事物的印象与认知令人惊讶,比如会觉得那条小河无比辽阔,对岸的屋影遥远,去代销店的那段几百米的路程似乎很难走到头……所以只要遁入童年,几乎能自动获得一种陌生化的文学效果。童年是一座永远挖不空的魔山,同时也是一座虚无之山,我并不确定,我从中挖到了什么,我为什么写他们,我说了什么。
20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野蛮生长》,依然是基于童年印象的想象。写一个家族,就像一株植物,人物如枝茎向四面八方蔓延伸展,最终成为一堆枯枝败叶。在这部小说中,我对童年印象进行了一次“翻箱倒柜”。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民间说书人,想起他坐在地坪上说书的腔调。他的语言平白易懂,以我五六岁的年纪就能听得入迷。所以我选择用土话,用一种现成的、“拿来用”的语言来讲这个家族故事。
以前写作,更在乎词语和句子,过于追求炫目的语言、精辟的比喻,觉得那才是写作的才华,迷恋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当然我不想否定过去的语言,只是现在厌倦了过去的腔调,厌倦了刻意雕琢,移情于简洁与朴实。
我曾经想过以不同的方式,收回最初写作时所蜕去的、丢掉的东西,但是没做到,因为年龄、阅历、经验、观念都在发生变化,这些都潜移、融化到写作风格里。事实上,我也只是那么一念想,无非是对最初写作时那股目中无人以及无所顾忌的眷恋。回过头,犹如看风在水面上运动,一股无形的力量吹起水面的波纹,我依然感觉自己受了优待。
尘土飞扬的时间,是可以洗心革面的——如果我给洗心革面加个双引号,只是为了表示我确实理解这个词,字典里的解释是,比喻坏人物彻底悔改——但是我不想加引号,凭什么好人就能洗心革面?又比如一个人,不论是好是坏,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产生了变化,他的内心与精神跟过去相比,截然不同,那么,这也是一场无声的洗涤与革命。
文学发展到今天,留下来的技术空间似乎已经饱和,艺术创新比中六合彩还难,幸好世界还在继续,时代在更替,人还在各式各样地活,各式各样地死;幸好人还有精神,还有灵魂,还有虚无,还有困境。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需要文学艺术,动物不需要。
身为作家,并不是肩负多大的使命感,一心想着拯救世界,或为人类解决什么难题。我的焦虑在于,创作构思能不能让自己欢欣雀跃,怎么才能突破自己,怎么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十年前,我读了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个诗人送的,全书是A4复印件。我记得当时画了很多杠杠。后来多次搬家,复印本丢了,书也买不到。写作困难的时候,想到这个书名,摸着了自己的病因,知道焦虑,这也意味着认识了自我的局限与不足。最初近乎狂欢的写作终结,速度缓慢,停滞,自我怀疑。在那么多经典名著的重压下,你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存在有什么价值?怎样才能提供新的文本经验?怎么才能石破天惊?于是在焦虑中持续阅读。
2015年3月初,我开始雄心勃勃地创作第八部长篇《福地》,叙事者是一个白痴少女。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认为傻子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形象,他甚至说,“骗子、小丑和傻子开始了欧洲现代小说的摇篮”。我想这并不夸张。我们很喜欢那些经典的疯傻文学人物, 《阿甘正传》,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福克纳的班吉……因为傻子常常具有正常人所不具备的美德,有理想,有勇气,有正义、纯朴、宽容、善良。这是现代社会稀缺的品质。当我打算在新小说中塑造一个新时代的傻子人物,以一个白痴女的视角呈现世界新的荒诞时,心里有一股非同寻常的创作激情,似乎胸有成竹。但写起来才发现非常有难度。作为作者,一方面你必须化身为白痴,进入她的世界,了解白痴的思维逻辑、价值判断,甚至她内心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你还得像个会通灵的巫婆,有智慧附体,让笔下的白痴具有文学意义上的生命活力。难度大得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要么不小心显露了叙事者的操纵,要么真的傻了,蠢起来不知所云。这一角色设定甚至剥夺了部分写作过程中的乐趣,比如对比喻、隐喻等修辞的迷恋,以及对人物的刻画、揣度,对各种心理的描写,在这儿几乎用不上,这对写作造成了巨大的钳制。
沮丧中暂停写作,备了些宣纸笔墨,画画换脑筋。一幅画画完,就能迅速发现问题。画面表达的内容过满,于是去掉一块石头,一所房子,或者一棵树,心到意到,但不形诸笔墨,画面简洁干净,意境反倒悠远了。我意识到我在那部小说中犯了同样的错误,越是用力呈现人物的傻痴,越是暴露了作者的虚弱,增加了作品的臃肿与无力。
重读《喧哗与骚动》,试图进入班吉的世界,甚至模仿班吉,双手抓着充满铁锈味的铁栅栏,望着外面的世界。班吉的视角与感知,就像国画里的白描,没有烘染,没有点缀,集中突出画面的重点;又像一束强光灯,照见舞台所呈现的独特事物。班吉对事物的认识是片段的、零碎的,他的反应简单直接,他的感知、触觉、嗅觉、意识一片混乱,思绪从这个跳到那个,没有现实的有秩序的时间和空间,场景转移就像电影蒙太奇的剪辑,但是有某种内在微妙的关联使它们在班吉的脑海里衔接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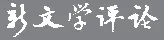
北京酒仙桥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