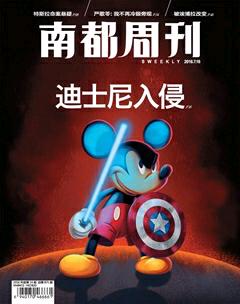被埃博拉改变
小菲

2014年8月15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一位母亲在埃博拉隔离病房里照顾孩子。
菜市场里卖着烟熏猴子肉
在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一片泥泞的土地上坐落着露天农贸市场。市场里人声鼎沸,随处可见简陋的摊档,海运箱改装成的临时货品柜,还有载满内衣或者木薯块的手推车。潮湿的空气里有一股烧煤的烟味,还混合着香料的芬芳和垃圾腐败的臭味。被雨水冲刷而成的浅水洼里,赫然躺着一条已经泡得发胀的死狗。
再往里走光线变得昏暗,那里摆着一溜放着肉类的案台:炸鱼、鳗鱼,爬着苍蝇的羊头。旁边还有丛林肉,刚开始有点难辨认是什么,但肉堆上一只蜷着手指的猴子的手给出了提示。
早在2014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之前,利比里亚已经遭受重创—贫穷、腐败、饥荒。丛林肉是廉价蛋白质来源,却把那里的居民跟可怕的埃博拉病毒联系到了一起。两年前的疫情始于靠近几内亚的一个边远村庄,当地的森林遭到掠夺性砍伐后,村里一个幼童接触了携带病毒的动物,很可能是野生果蝠之类的。接着疫情很快蔓延开了,超过28000人染病,其中11000是利比里亚人。
如今利比里亚已经禁止丛林肉买卖,但在蒙罗维亚的数百个农贸市场,每天仍在贩卖这种非法肉类。丽贝卡·科里亚是一个肉档主,她面前摆着被切成四块的烟熏猴子,她说:“我卖这个已经20年了,但我没有得埃博拉。”

2015年1月28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一名利比里亚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正穿上防护服。
每10万人里只有1个医生
尽管埃博拉疫情引发了恐慌,但仍有很多利比里亚人并不清楚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机制。在疫情暴发之前,利比里亚全国有400万人口,却只有少得可怜的50名执业医师,没人知道现在医生的数字还剩多少。利比里亚是世界上第八穷的国家,它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列为脆弱国家。对于一个如此弱小和分裂的国家,控制疾病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今,距离埃博拉疫情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一年半了,汇集到这里并最终控制住疫情的一大批外国疾控专家、保健工作人员和危机响应小组都已经离去。但病毒不断抬头。在西非首次宣布埃博拉疫情结束之后,2015年5月又有10例新发病例,其中3例在利比里亚。专家认为病毒能够在感染症状消退后的几个月里持续通过性传播。
生态健康联盟的新病种专家、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威廉·凯勒什说:“有些地区很可能会出现感染病例。”他认为可以像地质学家描绘地震风险地图一样,制作一张传染病风险地图。风险最高的是那些土地用途新近被改变的地区,比如利比里亚这种因为贫穷和战乱,树木被大量砍伐,人们深入丛林捕食野生动物的地区。他说:“我们要做好预案。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地震,建筑标准被更改了。我们也应该做点什么来应对可能发生的疾病。”在疾病高风险地区进行更好的教育和推广早期筛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疫情暴发。
今天的利比里亚在防疫工作的很多方面仍然跟埃博拉疫情前一样准备不足。尽管利比里亚已经淡出了人们视线,但流行病学家认为新的疫情再次暴发是有可能的。一旦疫情死灰复燃,就不仅是西非的问题了。全球商旅可能让疫情前所未有地蔓延各地。
留作种子的粮食都被吃掉了
在蒙罗维亚郊区的金斯维尔,列维·里尔威利蹲在他小棚屋的泥地上,指着四周拥挤的棚屋说:“这里很多家庭的生活都很苦。在埃博拉流行期间,你甚至不能出门访友。留在自己家,也不能伸手去碰其他人,连拥抱自己的孩子都不可以。人人都感到非常害怕。”在埃博拉蔓延时,飞往蒙罗维亚的航班都全部取消了, 跨国贸易办公室关闭,学校和市场也都不开门。最终,人人留在自己家里。农民们吃完家里储备的粮食,开始吃原本打算来年播种的种子,吃完种子之后就没有东西可吃了。
里尔威利踢着脚下的泥土说:“我大部分家人都死于埃博拉,11个人。”
埃博拉仍然像幽灵一样盘亘在蒙罗维亚。在大西洋和梅苏拉多河交汇处的贫民窟西点,一所学校在疫情时被征作临时治疗中心。一场大雨过后,学校周围的小巷里满是雨水和污水。一个当地妇女就在学校旁边用铁桶给一个小女孩洗澡。疫情暴发后学校被清洗干净,地板重新铺过,还粉刷一新,跟小巷周围破败不堪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但学校几乎是空的,学生们大多避而远之。

2015年1月24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一名男孩头顶炸鱼在街上售卖。
埃博拉响应小组发不出薪水
隔壁的理查德·科伊科伊是西点埃博拉响应小组的成员,在疫情爆发期间,他负责把染上疫情的病患送到救治中心,也会把罹难者的尸体运走。在疫情最开始的疾控战略失败之后,国际专家们支持了像科伊科伊这样的当地埃博拉响应小组,是这些小组在遏制疫情扩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埃博拉响应小组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地815名医护人员,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疫情过后这些小组大多解散了,幸存下来的工作人员也找了新的工作。
科伊科伊的小组理论上保留了下来,他们还有一条热线电话。但就像西点很多居民一样,他感到被遗忘了。 他问道:“我们现在要把患病的人送去哪里呢?就在昨天,我们收到了一例埃博拉疑似病例报告,但是我们组没有办法跟进。连我自己的薪水都被拖欠两个月了,所以我现在才坐在这里。”
1月,就在利比里亚第三次宣布埃博拉疫情结束几个小时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附近的塞拉利昂发现一例病例。到了3月,一名埃博拉幸存者传染了另外一个人,继而又传染了10个人,其中8人不治身亡。而管理部门在两名患者死亡之后才知道这件事。威廉·凯勒什说:“我们知道埃博拉病毒仍然在西非传播。事实上,没有新的人类感染病例,并不意味着疾病已经消失。”
九成农田在疫情中荒弃
从蒙罗维亚出来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卡车突然急转方向坠落路边。卡车撞入了路边一个拥挤的院子里,撞坏了房屋。人们冲向冒着蒸汽的卡车残骸,混杂着女人们的尖叫声。
利比里亚一位农业专家佩德勒·克雷格正在洛法州调研粮食安全问题,他看到车祸连忙跑过去看,他喊道:“人还活着!”尽管这是个奇迹,克雷格看起来却颇为忧虑。显然司机知道卡车的方向盘有问题,但他还是冒险把车开上路了。他解释说:“有很多人愿意做同样的工作。”
往后的几公里路也修得很好,但是在发展项目结束的地方,路况马上变差了。克雷格还在回想那个卡车司机:“人们是自愿那么做的,为了维持生计没有别的办法。”双向的车流都小心地绕开路上的坑坑洼洼,车子一直在上下颠簸。
最后车子经过了一个旧营地,以前那里住着内战流离失所的人。尽管洛法州曾经是该区的粮仓,在内战期间农业却减产了四分之三,而且至今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利比里亚如今大部分粮食依靠进口。现在洛法州的很多农民收成的粮食仅够自己糊口,碰上粮食减产或者缺乏必要储存设施,他们自己都要购买昂贵的进口粮食。克雷格概括说收割前的“雨季”是缺粮的原因。
今年,粮食缺乏有演变成饥荒的趋势。在埃博拉疫情的高峰期,隔离措施让农民无法参加传统的合作社耕作,连续几周目睹身边的人不断生病和死亡,促使很多人逃离了该区。

2015年1月27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一名护工在由于埃博拉病毒肆虐而关闭的幼儿园内。
一个西非政府间合作组织,马诺河联盟农业和食品安全项目组的成员肯耶·巴莱说在2015年春播期间,洛法州大概90%的农田都被丢荒了。
在通向洛法州主路边的一个小村子加拉买里,应克雷格要求,镇长召集了一些人来座谈。一个叫墨菲·史密斯的农民第一个发言:“这里的事情越来越糟了。”很多人清理了土地上原先的自然植被,但是又没有种子去种农作物。和洛法州里大多数人一样,史密斯一天只吃一顿饭,通常在深夜做饭,才不至于因为饥饿睡不着。
镇长嘎麦·托克帕是个瘦削的女士,她身穿绿色传统裙装,她说:“我们在清理灌木丛,但是我们缺少作物种子。”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说他们上一次在当地分发赈济粮是在2014年12月,通过合作伙伴基督复临会发展与救济局操作的。类似的分包工作很常见,也容易导致权责不清。要么那些赈济粮从未分发放到位,要么是参与座谈的人都在说谎。无论是哪种情况,当地居民都还在生存线上挣扎。托克帕听说沿路的另一个镇北岩,收到了救济金和粮食。史密斯问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匀一点给我们呢?”
起不到长期效果的救援工作
在北岩镇的检查站,路上拉起了一条绳子,旁边是清洗桶。因为埃博拉病毒通过液体传播,经常洗手是一个有效的预防方法。镇长科鲁巴·阿格维站在一棵巨大的棉花树下避雨。一位妇女坐在旁边的树根上照顾一个枯瘦的婴儿。阿格维说:“没有,世界粮食计划署没有在这里分发过食物。”当地政府也没有发过救济粮。“我们压根儿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沿途的萨拉耶镇也是同样的情形。镇上人口众多,但居民生活并未恢复正常。当地农民弗洛默·班纳说:“你能看到载着食物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卡车开过,但他们不停这个镇。”(而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档案记录,他们于2014年12月在萨拉耶镇分发过食物。)班纳认识的人里没有人收到过赈济粮,他说:“我们都不知道赈济粮去哪里了,有传闻说去了北岩镇。”
农业司地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多米格·科利正在往家里走,他在路上停了下来,说:“农民要得到粮食并不难,因为现在是收割季节。如果他们告诉你自己很满意,是因为他们觉得从你这里得不到好处。”但他说不出多少农民已经返回了自己的土地,又或者多少农民有种子播种。他说:“埃博拉疫情之后就没给我发过汽油,我还要自付油费去考察农场。”这限制了他下乡考察。
克雷格说:“我曾在天主教救济会工作,看见过工作人员偷窃食物。朋友们都住在很大的房子里。因为薪水足以负担我的生活,我安于工作。但他们说我很愚蠢。”数十年的贪腐和缺乏社会监管,社会价值观已经扭曲,诚实反而变成了不可靠的品质。
尽管克雷格的家人在疫情中保持了健康,但他仍然过得很艰难。利比里亚的严重危机—战争和埃博拉,引发了持续的混乱。政府和国际救助预算花掉了,却没有起到长期效果。比如,埃博拉疫情期间分配给利比里亚的382辆救护车, 根据总务署最新的统计只剩下268辆,其余的不知所终。
就利比里亚粮食问题询问不同的人,听到的回复都很糟糕。尽管利比里亚现在并不算经历大饥荒—大饥荒的标准是每天有万分之一的死亡率—但据粮食和农业组织最保守的估计,多达63万利比里亚人没有足够的食物。世界粮食计划署说该国超过一半的人口在粮食安全线边界或者之下。
即便在最好的状况下,实时数据也很难获得。伊丽莎白·格里芬研究基金会一位负责全球卫生安全和传染病的国际项目经理加文·麦格雷戈-斯金纳说,利比里亚极其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他坦承:“这表明国际社会的努力正在土崩瓦解。数据不应如此难获取,肯定是哪里出错了。”通常,在灾难响应的最初24小时内,救灾人员会挨家挨户去问灾民他们需要什么。然而在利比里亚,灾难发生两年后,一个全面的评估却都还没完成。他说:“人们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

2015年1月25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民众在海滩休闲。
去年夏天,在曼哈顿大都会博物馆的顶层,全球卫生响应和恢复联盟的协调员迈克尔·麦克唐纳率领一组救灾专家在此讨论西非问题。该小组从联合国国际埃博拉重建会议中分离了出来,随便提起一个30年内发生的灾难,小组里都能找出去过灾后重建的人。
把权责下放给当地居民,是最近在救灾人员中流行的想法。世卫组织埃博拉响应负责人彼得·格拉夫说,让当地人监控潜在的埃博拉受害者,并进行防疫宣传,是埃博拉疫情最终得以遏制的原因。 “埃博拉证明了本土化的决策过程在疫情响应上是很有效的。”
采用上述策略的其中一个组织是国际关怀项目。卓林·穆林斯在埃博拉疫情暴发时任该组织的利比里亚负责人,他介绍说他们与700个镇的领导和传统医师合作,为居民提供有效的卫生建议。因为是由当地人,而非外国的专家或者承包商在民众中进行宣传,人们相信他们的建议,这些城镇中95%的人都没有埃博拉感染病例。
而且权责下放到社区还可以减少他们对国际援助和本国政府的依赖性。援助方式发生任何变化,都会受到来自当地政府和原有援助提供商的阻力,特别是当涉及到资源变化时,会触及既得利益者。显然,惯性的力量阻碍了西非的灾难救援工作。利比里亚弱小又分裂,以至于传统的危机响应不奏效。
健康合作伙伴组织利比里亚负责人布赖恩·墨菲-尤斯提斯说:“如果你跟我一样相信,埃博拉病毒瞄准的是一个破碎的卫生系统,那只有重建并长期巩固卫生系统才能奏效,除此以外任何方法都不行。”到今天为止,约三四成的利比里亚人口缺乏医疗保障,跟疫情发生前相比没有任何改善。而现在国际医疗援助的预算被用在了新的国际危机—寨卡病毒上,只剩下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还在运作。墨菲-尤斯提斯说:“埃博拉进一步打击了人们对卫生系统的信心。”他说新的严重卫生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在疫情暴发时,“大规模的预防接种活动被推迟,以免公众聚集。”传染病药物分发被打乱了,导致了诸如耐多药结核病的死亡率增加等问题。
国际投资让事情有了一些改善。格拉夫说:“实验室容量扩大了”,尽管还做不了一些先进的检测。在3月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抬头时,一位专家还要飞往当地指导基因测序工作。当地医疗工作者接受过分诊和快速识别埃博拉早期症状的培训。但墨菲-尤斯提斯指出,从长远来看未来依旧不乐观。
就拿洗手这么简单的事情来说,记者随机访问了几个利比里亚人,发现捐赠给他们的肥皂都已经用完了,捐赠的水桶则散落各处,被改作装菜或者装碗筷用途。
格拉夫说:“从统计上看,幸存下来的人口中可能爆发更多病例。”他指着道路旁边的镇子说:“这些地区应该要预备着埃博拉卷土重来。”

2015年2月1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儿童在为一个芭比娃娃整理头发。利比里亚政府表示该国已接近“消灭”埃博拉病毒,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陆续恢复正常。
防疫出路在哪里?
去年在蒙罗维亚的可口可乐广告展望了利比里亚的未来,一个广告牌上印着:“我相信,利比里亚会更好更幸福”,另一块广告牌上写着:“我期待明天会更好”。还有一块广告牌上是埃博拉幸存者的照片,高举双手作出表示胜利的V字,眼睛直视镜头,广告语是“我成功了,我相信”。
就在一块广告牌旁边,埃博拉的幸存者珍内·盖图从医院的窗户望向外面的暴雨打在停车场的救护车上,她刚开始接受心理辅导。她说:“疾病夺走了我的丈夫。发病4天后他就去世了。我们刚刚将他下葬,我儿子的皮肤就开始发烫。”盖图把年仅3岁的儿子从乡下带到了蒙罗维亚求医。“我们当时坐在出租车上,儿子就在我的膝盖上咽了气。我紧紧抱着他的尸体,不让人知道那是埃博拉病毒。”盖图随后致电了首都负责处理埃博拉病例的医疗队,但没有人出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就跟儿子的尸体一起待在蒙罗维亚一栋空房子里。最终她也病倒了,自行前往了一个救治中心,等待死亡的到来。但她没有死。她说:“我活下来了。但我感觉像变了个人,变得跟别人不一样。现在连我自己的亲人都不要我了。”主治医生的助手伊曼纽尔·巴拉递给她一张纸巾。巴拉跟同事在医院里的无国界医生组织门诊工作,治疗几百个埃博拉幸存者的身心问题。
巴拉说:“埃博拉幸存者被严重污名化了。在埃博拉治疗中心接受救治的患者经历了可怕的事情。但离开治疗中心,这些幸存者面临的挑战才刚开始。”他在大厅跟另一位幸存者阿莫斯·杰西打招呼。当巴拉介绍说自己的很多病人也在接受其他组织的援助,杰西插话说:“实地调查一下,亲自问问幸存者他们是否得到了救济。疫情过后的生活比埃博拉病毒本身还要糟糕。”
(来源:《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