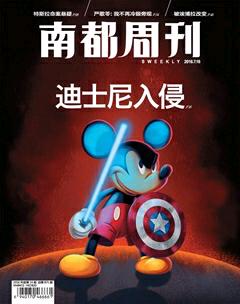严歌苓:我对中国社会不再只冷眼旁观
河西

刚刚卸任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严歌苓就出现在她的最新小说《舞男》发布会现场。
白色短袖连衣裙,蛾眉淡扫,略施薄妆,头发简简单单在脑后挽了一个发髻,显得清新大方,又不落俗套。
1958年出生的她,今年已经58岁了,可是严歌苓在旁人看来,年龄似乎已定格,永远是美丽中略带忧郁的少女模样,将人生悲喜,藏在心中。
年容未老,心已沧桑。
严歌苓当然是个“有故事的人”,否则,怎么能将那么多人世间的男女、生死、人性的挣扎、苍凉与繁华写得入木三分?
“大概因为我善于讲故事,也喜欢刻画人物吧。”她淡淡地说。生于上海,在安徽长大,12岁当兵学舞蹈,20岁做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的战地记者,从军13年。进入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时,和莫言、余华是同班同学。90年代末,一场不圆满的婚姻之后,赴美学习,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那一年,她已经32岁。一边刷盘子,学叉子、西餐和咖啡,捋顺了舌头学英语单词,敏感而痛苦的年代。
这些经历,从她的小说中一眼就看得出来,《穗子物语》《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都是军队题材的作品,《少女小渔》中刚到美国、像一颗小小台球感受着中西两种文化碰撞的小渔,何尝不是她当年苦苦奋斗的泪水化成?
也许是太有故事性的缘故,她的小说似乎特别容易改成影视作品并大获成功。
现在,严歌苓透露,她的新作《舞男》,影视改编权的争夺可谓异常激烈。一个光怪陆离的上海滩舞场,地位悬殊、文化背景悬殊、年龄悬殊的两个男女,演绎了一场曲折生姿、柳暗花明的情感大戏,还暗藏着她对中国社会新阶级的观察,怎么说,都有很多卖点,让人异常期待。
我喜欢给陈冲口述故事
南都周刊:上世纪70年代,你曾经是成都军区一位年轻的舞蹈演员,那时,每次去阿坝草地的军马场演出,都会经过汶川地区,那一段经历是否也影响到你写《天浴》?
严歌苓:是的,汶川是我非常熟悉的小城。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是个小女兵,是1972年。后来还去过许多次。写《雌性的草地》时去过一次,采访留下的知青。第三次去草地,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骑马,跟那些牧马班的女孩子放过夜牧。写《天浴》的时候,一闭眼睛,草地的味道都回忆起来了,所以我是幸运的,很小就走了那么多地方。
南都周刊:在你所有改编成电影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天浴》。
严歌苓:我自己也很满意陈冲导演的《天浴》,不论是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还是对人性的思考,都和我非常非常接近。我觉得当时她之所以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是因为她清心寡欲,没有什么杂念,自己投资了40%,现在这种精神也挺少见了,可能20出头的年轻导演还有这种劲头,有这样纯粹的追求。
南都周刊:是怎么写《天浴》的呢?
严歌苓:《天浴》的短篇小说是得了奖的。中文得了台湾的大学生小说奖(因为那时我还没有读完硕士),英文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奖。在写小说之前,我把这个故事口述给陈冲听,她说她都能看见画面了。然后她按照小说写了个电影大纲,我们就是从那里开始合作这个电影的。我常常喜欢把故事口述给陈冲,《小姨多鹤》的故事我好多年前就讲给她听了,她说是个好小说。记得当时一位朋友送了我一件日本女人的和服,她还说,穿上它去写那本小说吧,找点感觉。
南都周刊:和陈冲是怎么结识的?我知道你们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据说和陈冲一碰到就整天黏在一起玩,吃饭、逛街、买衣服?
严歌苓:和陈冲的最初结识是通过我父亲和我继母。那时候陈冲的哥哥陈川和陈逸飞常到我爸爸住的宾馆去玩,有几次把陈冲带来了。陈冲的第一部电影《青春》是和我继母俞平一块演的。现在我们已经不怎么逛街买衣服了,在美国大家都是牛仔裤T恤,穿得太漂亮像是挑衅大众似的。我们在一起烧菜比较多。
老在原单位待着不是挺乏味吗
南都周刊:1980年,你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该片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你是怎么会去写电影剧本的?
严歌苓:当时我爸爸在写电影剧本,他周围的叔叔都在写电影剧本,包括白桦、叶楠、梁信等等长辈。我总是受我爸爸的影响很深,跟他学,他干嘛我就干嘛。
还有就是,写电影马上就被电影厂抽调出去,到电影厂的招待所住着修改剧本,这样就可以离开原单位。老在原单位待着不是挺乏味的嘛。到了电影厂,没有领导看着,又可以和一帮像自己一样的年轻人在一块狂妄、自由、海阔天空地瞎侃,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不是最理想的吗。电影拍了当然好,不拍,也如愿以偿了。
南都周刊:当时你写了很多剧本,《残缺的月亮》《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大漠沙如雪》《父与女》《无冕女王》等大多没有正式投拍,是什么样的原因?
严歌苓:因为当时的制度是没有导演、光有编辑,只听编辑的意见,一遍一遍地改剧本。一个电影怎么可以是编辑的主旨,不是导演的呢?等你按照一层层编辑的意见改完了,那剧本还能看吗?哪一个有才华的导演会看上这样的剧本,来导演它呢?这是一个谬误的创作程序。
南都周刊:你是好莱坞专业编剧,在好莱坞编剧的报酬是否也比在美国写小说要高得多?
严歌苓:好莱坞的编剧协会每一次罢工,都会把协会会员的最低稿酬闹得高一些。但中国编剧的稿酬也在上升中。国内没有这个协会,所以编剧的权益没有受到保护。其他电影行当也一样,没有业内人自己的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南都周刊:刚刚到美国定居以后写作和生活方面是否一帆风顺?在美国如果只是用中文来写作,那么你写的小说主要还是给台湾发表和出版?
严歌苓:我是作为留学生到美国的。留学生的生活都非常艰苦,但非常有趣,有时候还挺刺激。朝不保夕,充满未知,充分调动你的生存原动力、生物的生存力和智慧,不是很刺激吗?当时我写出的小说在台湾、香港发表,主要是因为我要挣美元生活。国内的稿费那么低,又不能换成美元,我就是写,对于我在美国的生活不也还是杯水车薪吗?所以存在决定意识是一点没错的。生存的大命题往往决定一个人相应的举措。
南都周刊:1995年的《少女小渔》是刘若英电影成名作,影片获亚太地区电影展最佳故事片奖。导演张艾嘉是怎么看中你的这篇短篇小说的?据说是李安看中了转给她的?
严歌苓:是的。我并没有跟张艾嘉直接联系过。只跟李安通过几次电话。当时我在芝加哥读书,他在纽约,所以最初买版权和后来怎样改剧本的事情,都是在电话上谈的。剧本我写了两稿,张艾嘉和另一个编剧又改了几遍,最终拍摄用的稿子跟我的第一稿差别挺大的。
作家笔下的女人比男人更难忘
南都周刊:你说:“我喜欢写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漂亮的衣服、首饰都是给女人的一样,写她们很过瘾。”《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个题目基本上可以视作你的小说写作的一个宗旨:为女性立传,从一个女性的人生历程来折射历史的变迁。对你来说,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种独立的女性意识来创作小说?有没有考虑过以男性视角来写作一部小说?
严歌苓:岂只是我爱写女性!不说国外的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家,光看国内当代的男作家,包括苏童、莫言、毕飞宇等等,他们笔下的女人比男人更难忘。尤其是苏童。
其实我也写过男性为主角的小说,比方说我的中篇小说《倒淌河》《拉斯维加斯的谜语》英语小说《赴宴者》,等等。但因为自己是女人,写女人对于我更加自然。
另外就是我的女朋友很多,女朋友告诉我她们的女朋友的故事,有写不尽的题材。我觉得有趣的是,女人谈论女人比谈论男人要多。这样我得到有关女人的素材就比得到男人的要多。不过也说不定我冷不防就会写一本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
南都周刊:《有个女孩叫穗子》是你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小说可以独立成章,但是串在一起的就是一个叫穗子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的身上是否也有你本人的很多影子?
严歌苓:是有一点我自己的影子。童年时候有一些故事是听来的,有一些是看来的,但都只是一点因子,被想象力发酵,补充,完整了。参军后的故事里面,我们确实有过那么一只狗,许多细节也是真的。还有那个西藏女孩,很多细节是真的。我多次说过,细节很难编。
我的美国教授说,写什么不重要,怎样写就是小说的一切。我还要加一点:一篇小说“说”的是什么,也非常重要。这个“说”就是英语所指的小说家通过小说发送的“message”,是字面下的。一篇小说怎样写是文字的问题,而“说”什么往往是一个小说家的全部素质决定的。国内好故事满天飞,但不是每一个好故事都能被写成一个好小说。这要看小说家们怎样说这些故事,以及用这些小说“说”什么。
南都周刊:《小姨多鹤》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你还为此去了日本。写《第九个寡妇》这部长篇你也到河南去,看他们怎样吃喝、穿戴、过日子、闲谈,生活的细节是否决定了你的小说的走向、长短和结局?
严歌苓:当然是在当地待的时间越长越好。细节可以观察到,但一个地方的神韵,那地方人的神韵是要靠长期体味的。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没有这个条件,允许我待得更长。我除了做小说家,还有其他的责任,比如做妻子和做母亲。不过我是尽了力了。
南都周刊:我记得一位朋友对我说过,你搜集了很多档案,其中有没有《寄居者》中那位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呼风唤雨的犹太大亨的原型?
严歌苓:史料里没有杰克布这个人物的原型,这是我虚构的人物,除了小说的戏剧构架,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都是虚构的。这是一部纯粹虚构的小说。就像我的绝大部分作品和绝大部分作品中人物一样,都是我虚构的,只不过虚构的成分有多有少。做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调查—无论调查得多细致得到的资料多真实丰富,目的都不是为了省去“虚构”这一小说创作的第一重要手段啊。
这是我最有把握的一本书
南都周刊:你说写小说“我也算是快刀手”,哈金说,他的小说反复修改多遍,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是要字斟句酌?
严歌苓:我写东西很快,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快。我是个图痛快的人。任何事情有激情就一气呵成地做。所以写小说就是这样,抓住一种感觉,找到一种语气,对于一篇小说的创作非常重要,假如感觉和语气断了,再重新找,很困难,有时干脆就找不着了。我的一些小说流产,就是因为感觉和语气断了。
我觉得现在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说搁下一篇小说就要搁下,我就特别怕这样把一篇原来写得很好的小说感觉、语气给丢了,所以有一段相对集中稳定的时间就争取一口气写完,这就是我为什么显得写得那么快。
但我做一篇小说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长时间的,有时候需要十来年。我读D.H.劳伦斯的传记时,发现他写小说也很快,所以就对自己的创作习惯放心了。一个人有一个人创作的习惯。
南都周刊:那现在出了这本新书《舞男》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写《舞男》是怎么样的初衷?
严歌苓: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的大表姐,她向我介绍了这样一种生活,在十几年前的上海,有一些富有的海归寄居者,使得我有这样一个机会,了解到上海的另一面。
想写这个故事也有很多年了,这些年里,我也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写这个故事?我的书最后写成,往往和我在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有关。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总编辑魏心宏先生问我:“你怎么老不给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写本书啊?”年年碰到我都问我:“什么时候写出来啊?”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觉得不写说不过去,我就给他写出来了。也觉得每次到上海都去跳舞也跳出感觉来了,就写了这部小说。
南都周刊:这部小说的主题是?
严歌苓:我用上世纪30年代一个在百乐门的舞男鬼魂的视角来看今天的男女、今天的爱情、今天性的关系,他来看今天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的身份关系,他想人们是不是不会像他们那个时代那样恋爱?
在写作的过程中,除了文学性的一面,我也有一些社会性方面的思考。我觉得中国社会新的阶级正在形成,阶层矛盾和分歧也在形成,现在的上海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的上海,和过去的上海大不一样。我对现在上海的不同阶层——讲英语的海归、本地土著以及那些漂泊在上海、底层的外来者,他们的不同命运都感兴趣。
我原来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社会的旁观者,现在我觉得我参与其中越来越多了,比早两年写中国本土的故事要自信得多。我每隔两个月都要回来一次,我不再是侧目而视的那个人了,这样,我写的时候就非常有激情,牢牢把控着故事、人物和氛围的把握,应该讲,这本《舞男》是我写当代生活最有自信、最有把握的一本书。
南都周刊:你的很多小说都改编成了电影,那这本《舞男》呢?
严歌苓:这部小说还在电子稿的时候就已经被一家公司买走了电影版权,但是后来有一家和导演有挂钩的公司也想要买,我就和原来那家商量,说是不是可以让出来,因为我觉得有导演挂钩的,比较可以掌控电影的质量。而小说正式出版之后,对它电影版权的争夺就非常激烈了,我也在考量,看哪一家才是最合适的。它得了解上海生活,它还能请得动好的演员,有的导演很好,但是不一定能请到很好的演员,我对电影的摄制和制作都没有控制,因为我不喜欢控制任何东西,我也不喜欢控制任何人,喜欢控制人的那些人在我眼里都是很令人讨厌的。
但关于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我觉得现在电影很热,好像文学就得依靠,要找到电影这个寄居体才能存活,这是让我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