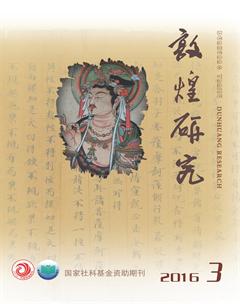汉简反映的汉代敦煌水利刍论
马智全
内容摘要:新刊布肩水金关汉简记载的汉宣帝时以诏书穿渠敦煌的事件,以及悬泉汉简记载的汉代敦煌郡的穿渠文书,反映出汉代敦煌水利建设事业的兴盛。简文记载的汉宣帝甘露年间的穿渠活动,说明汉代敦煌的穿渠对于西域开发具有重要意义。简文记载的各类治渠文书,不仅反映出汉代敦煌水利建设持续时间之长,而且说明了屯戍修渠与民间修渠的不同形式。汉代敦煌水利的管理,有都水长、平水史、东部水等不同职官。水渠的命名,有第一、第二、左、右、内、外、东、西等不同编号,说明敦煌水利管理的系统化特色。
关键词:敦煌;水利;穿渠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3-0103-07
Abstract: The newly published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from Jianshuijinguan contains some slips which record that Emperor Xuan of the Han dynasty ordered that irrigation ditches be dug at Dunhuang, a mandate confirmed by similar records found at Xuanquan. Both archives reflect the developed state of water conservancy at Dunhuang in the Han dynasty and indicate that water conservation at Dunhuang wa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Various passages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ditches found in these bamboo slips demonstrate that there were ditches constructed by both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that water conservancy work was conducte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at Dunhuang. The thorough systematization of local departments, official titles, and names of irrigation ditches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 management of projects related to water use was highly prioritized at Dunhuang.
Keywords: Dunhuang; water conservancy; ditching.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因其据两关、控西域的重要地理位置,是汉王朝着力开发与重点驻防的关键地区。汉代敦煌气候干旱少雨,四周又为戈壁沙漠,因此水利建设就成为农业种植与军事戍守的必然要求。由于敦煌文书的出现,唐代敦煌水利建设状况,已经有学者作出了深入的研究[1];汉代敦煌的水利建设,汪受宽《甘肃通史·秦汉卷》[2]、郑炳林、李军《敦煌历史地理》也有概括性的论述[3],但总体来看,史料不足是制约汉代敦煌水利研究的主要因素。上世纪以来敦煌汉简、悬泉汉简等汉代简牍的出土,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如高荣《汉代河西水利建设与管理》就对汉代敦煌水利有很好的研究[4]。近几年来汉简资料不断刊布,特别是肩水金关汉简中的一件诏令文书,说明了汉宣帝时“以诏书治渠敦煌”的事件。张德芳《汉帝国政权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对丝路交通体系的支撑》也披露了数枚与敦煌水利相关的悬泉汉简,并对汉简反映的敦煌水利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5]。结合已有汉简资料对汉代敦煌水利问题作出集中性的勾勒研究,还是可以取得一些新的认识。敦煌出土简牍特别是悬泉汉简还没有全面刊布,因此本文的论述也只能算是刍论而已。
敦煌地区发展水利,有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南有祁连山余脉三危山、鸣沙山,西南有阿尔金山山脉,北有北山山脉,境内有党河与疏勒河两大河流。《汉书·地理志》:“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6]氐置水即今党河,发源于敦煌县东南祁连山中,从南向北贯穿敦煌境内,后汇入疏勒河。又《汉书·地理志》:“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6]籍端水即今疏勒河,出南山后,西北而行,经玉门、瓜州折而西流向敦煌南境。党河与疏勒河培育了敦煌绿洲,也为敦煌水利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一 史籍记载的汉代敦煌水利建设
史籍记载的汉代水利建设,兴盛于汉武帝时期。特别是由于关东漕的凿通,黄河瓠子决口的堵塞,掀起了各地水利建设的高潮。“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7]武帝塞瓠子决口是元封二年(前109)间事。汉代敦煌郡的设置,依据郝树声考辨,是于后元元年(前88)从酒泉郡分设而来[8]。武帝时河西、酒泉的引川谷以溉田,也反映出敦煌水利建设的状况。
汉代敦煌水利的开发与建设,首先是农业开发的必然要求。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征河西,匈奴休屠王降汉,“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7]3167,于是实行移民徙边的措施。《汉书·匈奴传》:“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6]3770可见汉代经营河西的主要措施是“通渠置田”,即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敦煌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关于敦煌引水灌溉农田的情况,史书也有记载。《三国志·仓慈传》引《魏略》:“敦煌初不甚晓田,常灌溉滀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楼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9]“初不晓田”,反映了汉代敦煌早期开发的耕作情况,“常灌溉滀水”,说明当时农业种植主要依靠水利灌溉经营,而且对灌溉用水的需求量颇大。“使极濡洽,然后乃耕”,是说当时的灌溉方式是引水将农田进行充分浸泡,而后进行耕作,可见汉代敦煌水利灌溉的广泛性。
汉代敦煌地区的水利建设,除了农业开发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西域开发有密切关系。《汉书·西域传》记载:“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6]3907这是汉宣帝时为征讨乌孙而作的一次准备。事件原因是乌孙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乌孙亲匈奴势力得势,因此汉王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到敦煌准备征讨。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所谓“遣使者案行表”,是派遣使者作考察标记。王先谦《汉书补注》引何焯说:“《沟洫志》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注谓表记之,今之竖标是。”[10]可见“表”是有专长治水的人作标记,用以标明水渠的规制及水道的走向,这往往是水工才能做到的事。“行表”的目的,是为了“穿卑鞮侯井”。关于“卑鞮侯井”,颜师古注引孟康说:“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徐松《补注》说:“胡注谓时立表穿渠于卑鞮侯井以西,案今敦煌县引党河穿六渠,经县西下流入疏勒河,归哈喇淖尔,淖尔西即大沙碛,岂古六通渠遗迹欤。”[10]5852可见“穿卑鞮侯井”是引党河水而进行的水利工程。敦煌文书《沙洲都督府图经》记载:“大井泽,东西卅里,南北廿里。右在州北十五里。《汉书·西域传》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讨昆弥,至敦煌,遣使者按行,悉穿大井,因号其泽曰大井泽。”[11]王国维《西域井渠考》据此考证,认为:“是汉时井渠,或自敦煌城北直抵龙堆矣。”[12]可见“穿卑鞮侯井以西”,是从敦煌引水直至西域的活动。张德芳考证:“‘卑鞮侯井也称‘都护井,地在今敦煌广武燧以西的榆树泉盆地,是丝路交通中从敦煌到楼兰这一最艰险的路段中一处重要的水源供应地。过了都护井,再经三陇沙、白龙堆,继续向西,就到了楼兰。”[5]90也说明“穿卑鞮侯井以西”对于敦煌水利开发的意义。旧解“穿渠”为修治井渠,王国维《西域井渠考》释为“乃穿井若干,于地下相通行水。”[12]620不过《西域传》所说是“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徐松《补注》:“通渠转谷,欲水运也。庐仓,谓建仓。国朝雍正中,大将军岳钟琪于党河议行水运。”[10]5852可见当时修治水渠的目的是为了水运,特别是解决粮食运输的问题。汉代出征西域,特别是李广利两次西伐大宛,“道远多乏食,士卒不患战而患饥”,因此能够通渠转谷,对于西域戍卫具有积极意义。至于居庐仓,徐松的解释是不可取的,居庐仓即居庐訾仓,是汉设在西域的仓储名称,罗布淖尔汉简和敦煌汉简都有记载。当然,这次行动因楚主侍者冯嫽劝说乌就屠降汉受小号而结束,“破羌将军不出塞还”,但这件事却充分说明了敦煌水利建设对于西域开发的重要意义。
二 汉简记载的宣帝甘露年间的穿渠活动
《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宣帝时破羌将军至敦煌以及“欲通渠转谷”的事件,在悬泉汉简中也有具体记载,对于认识汉代敦煌水利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简1: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与世等,敢言之。V92DXT1311{4}:82[13]
这件文书是酒泉郡乐涫令上报查找走失马匹的情况,涉及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等重要人物。简文中“破羌将军”,即指破羌将军辛武贤,“使者冯夫人”指《汉书·西域传》所载的冯嫽。“穿渠校尉”是武职,不见史书记载,当是临时因事而设的职务。《后汉书志·百官一》:“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14]穿渠校尉也当是秩比二千石的官员,职主“穿渠”之事,充分反映出水渠修治活动的重要。
这枚汉简的时间是甘露二年(前52)四月十八日,值得特别关注。依照《通鉴》系年,“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是岁,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通渠积谷,欲以讨之”为甘露元年事[15]。但是乌就屠袭杀狂王,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宣帝征见冯夫人,汉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长罗侯常惠至赤谷城,汉分立乌孙大小二昆弥,这一系列事件不是一年之内所能完成的。因此袁延胜提出《西汉分立乌孙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辨》,认为事件如下:甘露元年,乌孙内乱,乌就屠自立为昆弥,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带兵至敦煌,欲征讨乌孙。冯夫人说服乌就屠,汉宣帝征冯夫人到长安进行询问,已是甘露二年。汉宣帝决定派冯夫人为使者,到赤谷城分立乌孙大小昆弥。甘露二年四月,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则此时宣帝一方面派冯夫人出使乌孙,一方面派破羌将军辛武贤和穿渠校尉拥兵敦煌,以为呼应,为汉朝分立昆弥作坚强的后盾[16]。果如此,则汉王朝分立乌孙大小昆弥事定在甘露二年四月之后,“破羌将军不出塞还”亦在此后。从简文分析,这一论证是有道理的。简文中的“通渠校尉”与史书记载的破羌将军在敦煌“欲通渠转谷”事件相符。张德芳认为简文中“穿渠校尉”首见于此,大概为破羌将军西进所专设[17]。此时乌孙大小昆弥尚未分设,通渠校尉已经西行,作为破羌将军的随行者,甘露二年四月到达敦煌。这枚汉简充分证明穿渠校尉活动的重要,敦煌水利建设已成为汉代西域开发的有机组成部分。
简2:穿渠校尉丞惠光私从者杜山羊西。V92DXT1312{4}:21[5]90
该简也记载了穿渠校尉,具体涉及穿渠校尉丞惠光的私从者名叫杜山羊。这枚汉简出自悬泉置,应是私从者经过敦煌的记录。依《汉书·百官公卿表》,西域都护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二人,戊己校尉有丞一人,因此穿渠校尉丞是辅佐性的职官。该简说明穿渠校尉西行,当有不少随从及属下参与穿渠活动,反映出穿渠活动规模不小。
简3: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富平侯臣延寿、光禄勋臣显,承制诏侍御史□,闻治渠军猥候丞承万年汉光王充诣校属作所,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各一人,轺传二乘,传八百卌四。御史大夫定国下扶风厩,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Ⅱ0214{3}:73A
□□□尉史□□书一封,十一月壬子人定时受遮要…… Ⅱ0214{3}:73B[13]40
这枚汉简的时间是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其中记载了“治渠军猥侯丞承万年汉光王充诣校属作所”,所谓“校属”,当是西域校尉的属所。这是西去西域的使者,其中“治渠军猥候”,意为专门负责治渠事务的众候。因为该简与前述“穿渠校尉”至敦煌时间相距仅有半年,很可能二者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简4:甘露四年六月丁丑朔壬午所移军司马仁
这枚汉简出自肩水金关探方九,是新近刊布的一件重要诏书。肩水金关是河西地区人员过往的登记要地,简文记载了“龙起里王信以诏书穿渠敦煌”的事件。简文有明确纪年,是甘露四年六月丁丑朔壬午。甘露四年是公元50年,六月丁丑朔壬午是六月六日,即公历7月28日。该简是要移书军司马仁。司马,武官名,《汉旧仪》:“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鄣塞烽火追虏。置长史一人,丞一人,治兵民。当兵行长领。置部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19]该处的“军司马仁”,很可能是敦煌郡的司马,那么,这件文书当是有太守府或都尉府发出。简文的主要内容,是说“龙起里王信以诏书穿渠敦煌”。王信,人名,他以诏书穿渠敦煌,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很可能是“遣使者案行表”一类的人物。“以诏书穿渠敦煌”,则是汉宣帝专门下诏书,要在敦煌进行穿渠活动。如前所述,破羌将军辛武贤至敦煌“欲通渠转谷”,是甘露元年的事。甘露二年四月,穿渠校尉到达敦煌,乌孙分设大小二昆弥。那么,敦煌的穿渠活动最终是否进行,是否因“破羌将军不出塞还”而终止?这枚出自金关的诏令文书证明,二年以后,即甘露四年六月,即有王信“以诏书穿渠敦煌”的事件。则敦煌郡的穿渠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是以朝廷诏令的名义进行,说明敦煌郡的穿渠,不仅是敦煌一地的事务,而且具有全局战略性的意义。
上述汉简主要反映了汉宣帝甘露年间在敦煌的治渠活动。宣帝时对水利建设颇为重视,《汉书·沟洫志》记载宣帝地节年间对黄河渠道的修治活动:“地节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邪直贝丘县。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东,经东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6]1687史籍及汉简记载的宣帝甘露年间在敦煌的治渠活动,具有特殊的政治及军事意义。甘露元年,为了防止乌孙乌就屠的反叛,汉政府制定了“通渠转谷”的政治措施。甘露二年四月,穿渠校尉经过敦煌,穿渠校尉的丞及私从者也到达敦煌,甘露二年十一月,又有治渠军候经过敦煌。由于冯夫人及常罗侯常惠的杰出外交才能,乌孙分立为大小二昆弥,破羌将军未出塞而还,但是敦煌的治渠活动并没有停止。甘露四年六月,有“龙起里王信以诏书穿渠敦煌”,说明敦煌的穿渠活动,仍然在政府组织下进行。
三 汉代敦煌的穿渠与修堰
除了政治军事上的穿渠活动外,敦煌地区水利兴修最主要的用途还是农业灌溉。党河自南向北流经敦煌绿洲,因此具有修治水渠的条件。《汉书·地理志》效谷县颜师古注引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以为县名。”[6]1615可见汉武帝元封年间敦煌已有农业种植。据《地理志》,西汉末期敦煌郡有户11200,人口38335。这么多的人口要生存,还要供应数量不少的屯戍士卒,以及途经敦煌的各类军队使团、商胡贩客,这就对农业灌溉提出了客观要求。汉简中对汉代敦煌郡的穿渠活动也有记载。
简5:□月己丑朔庚寅,县泉置啬夫弘移渊泉府,调穿渠卒廿一人。
Ⅰ90DXT0116{2}:117[5]90
这枚汉简出自悬泉置,简文是敦煌悬泉置对渊泉县的移书。简文中涉及了“啬夫弘”,依据目前刊布的悬泉汉简,啬夫弘有元康三年(87-89C:6)[13]102、神爵二年(Ⅰ0309{3}:215)[13]147的活动纪年,可见啬夫弘主要任职于宣帝前中期。与上述宣帝甘露年间的穿渠诏书相联系,进一步反映出宣帝时敦煌水利建设活动的兴盛。渊泉,县名,位于敦煌郡东境,疏勒河中游。这枚汉简是悬泉置移书渊泉府,要从渊泉府调配穿渠卒21人。穿渠卒是专职修治水渠的人员。渊泉县有数量不少的穿渠卒,可以调配至位于效谷县的悬泉置,说明敦煌水利有专职人员进行建设。
简6:初元三年正月,戍卒省助贫民穿渠冥安名簿。V92DXT1410{3}:50[5]90
这枚汉简为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正月,简文是戍卒省助贫民穿渠冥安的名籍。简文反映出敦煌郡冥安县的一种治渠形式,治渠活动的主体是贫民,也有戍卒省助穿渠。据居延汉简可知,省助活动一般有候官、都尉等组织机构,是一种集体性的劳作活动。这一枚汉简记载的省助,自然也是屯戍机构的活动,是屯戍修渠的一种组织形式。另外这枚简反映的地名也值得重视。冥安,以及简5记载的渊泉,都是疏勒河流经的地区,灌溉条件便利,反映出敦煌地区水利建设的普遍性。
简7:民自穿渠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水门广六尺袤十二里上广丈
Ⅱ90DXT0213③:4[13]55
这枚汉简记载了民自穿渠的活动,是民间自发性的穿渠行为。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是水渠的编号名称。水门广六尺,即宽六尺,依每汉尺23.1厘米计,为今1.386米。袤十二里,即长十二里,依每汉里415.8米计,为今4989.6米,近5000米长度。简文还记载了水渠上部宽度,惜已残而不得知。
简8:续穿第一渠东端袤二里百步,上广丈三尺二寸至三丈二尺八寸,深二尺七寸至八尺V92DXT1312{3}:17[5]90
这枚汉简未见之前刊布,说是续穿第一渠,东端长二里百步,为今969.6米,近1000米。其中渠道规格,上部较窄处约丈三尺二寸,为今3.0492米,较宽处三丈二尺八寸,为今7.568米。渠道深度浅处为二尺七寸,为今0.6237米,深处为八尺,为今1.848米。从渠道规制可知,水渠修治并不规整,上部宽自3米至7米不等,深度也从0.6米至1.8米不等,反映出水渠修治的草创状态。但是简文对水渠修治的登记如是详明,又反映出水利管理的严格。而“续穿第一渠”,同时反映出水利建设的有序状态。
这枚汉简出自甲渠候官,上下残缺,影响了文意的解读。简文记载有3485人,可能是戍田卒的人数。简文还记载了“敦煌郡”,则这些人员与敦煌郡有一定的关系。最有价值的是简文记载了“发治渠卒”,说明有专门的水渠修治人员“治渠卒”。由于简牍上下残缺,简文的性质还不太明确,很可能与敦煌郡的水利修治相关。
除了水渠修治外,堰坝修治也是水利建设的重要内容。汉简中还没有检到堰坝修治的例子,不过敦煌文书《沙洲都督府图经》(P.2005)有汉代修治马圈口堰的记载。
马圈口堰,右在州西南廿五里,汉元鼎六年造。依马圈山造,因山名焉。其山周回五十步,自西凉已后,甘水湍激,无复此山。[11]8
马圈口堰是党河进入敦煌绿洲的第一道拦水、分水堰坝,地理形势重要。这件文书说明汉武帝元鼎年间就在此地修筑堰坝。从时代背景分析,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出兵深入河西,开拓了西至酒泉的道路。元狩三年(前120)秋,于敦煌捕得渥洼野马,武帝为此作《天马之歌》。元鼎六年(前111),在河西置张掖郡、酒泉郡[2] 489。而马圈口堰就修治于元鼎六年,可见西汉敦煌水利修治时间之早。
以上简文及敦煌文书反映出汉代敦煌水渠堰坝修治的史实。汉武帝元鼎年间,已经开始了马圈口偃的修治,汉宣帝时有穿渠卒在敦煌进行穿渠活动,汉元帝时有戍卒助贫民穿渠冥安,可见西汉中后期敦煌渠修治的持续。而水渠的修治,又可分为戍卒修治与平民修治两种形态。贫民修治水渠有困难时,则有戍卒进行省作帮助。这些简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敦煌水渠修治的广泛与频繁。
四 汉代敦煌水利的管理
汉代的水利管理,中央有大司农所属之都水。《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6]731《后汉书志·百官志五》:“其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无分士,给均本吏。”[14]3625敦煌是边郡,水利主要有大司农所属之都水管理,而郡县也有掌管水利的长丞。汉代敦煌的水利管理,敦煌地区所出汉简也有记载。
简10:□通,都水长常乐,知火再举,逢未下,吏收葆不得行,而使卒传送客许翁卿敦1363 [21]
这枚汉简出自敦煌酥油土,其中记载了都水长常乐。都水一职,是专职的水利管理官员,正是《百官公卿表》所载的都水。都水长,也是“随事广狭置令、长”的反映。《通典·职官九》:“秦汉又有都水长、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自太常、少府及三辅等,皆有其官。汉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以领之,至汉哀帝,省使者官。”[22]这枚汉简出自敦煌酥油土,简文又记载了烽火事务,所反映的应该是敦煌当地都水长的设置情况。
这是敦煌郡发出的一份邮书登记簿,其中有“二封水长印诣东部水”的记载,说明敦煌郡设有水长一职,也是史籍记载的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的反映。水长,正是专门管理水利事业的职官名称。所谓东部水,当指东部都水,也是水利主管机构。疏勒河在敦煌境内自东向西流过,东部都水,当是东部水利事务的主管吏员。
简12:出东书四封,敦煌太守章:一诣劝农掾、一诣劝农史、一诣广至、一诣冥安、一诣渊泉。合檄一,鲍彭印,诣东道平水史杜卿。府记四,鲍彭印,一诣广至、一诣渊泉、一诣冥安、一诣宜禾都尉。元始五年四月丁未日失中时,县泉置佐忠受广至厩佐车成辅。即时遣车成辅持东。Ⅱ0114②:294 [13]92
这枚汉简也是邮书传递的登记簿,记载了“诣东道平水史杜卿”,涉及东道平水史这一职官。这枚汉简记载的邮书都是敦煌郡发往下属机构,东道平水史也当属于敦煌郡,专门管理东部的平水事务。《后汉书志·百官五》:“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14]3625平水主要负责平治水利事务。《三国志·杜恕传》裴注引《魏略》:“(孟康)事无宿诺,时出塞行,皆豫敕督邮平水,不得令属官遣人探候,修设曲敬。”[9]506《隋书》记载有平水署:“少府卿,位视尚书左丞,置材官,将军,左中右尚方,甄官,平水署。” [23]敦煌郡设有平水史,正是掌管水利调配的职官。东道平水史,只管理东部平水事务。疏勒河自西向东流过,可见当时水利管理有东道平水、西道平水。
这枚汉简出自敦煌郡,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简文下半残缺,影响了简文的阅读,不过大意还是清楚的,是说永平七年(64)正月十八日,当时有春秋治渠各一通的活动,要求出块粪三百余枚,以及谷十石。而名叫文华的人,出块粪有所缺少,不足于修渠的要求,因此要折合计算,若干亩以上折合胡谷十石,文华有田若干亩,可折合若干石。为进行相关活动,文华还要沽酒旁二斗。
这枚汉简的主要价值在于揭示了敦煌当地的治渠特点,所谓春秋治渠各一通,意即春季治渠一次,秋季治渠一次,反映出治渠活动的季节性特点。而出块粪三百柒,当也与治渠有关。此外,这枚汉简记载了东汉永平时的治渠活动。汉明帝对水利修治颇为重视,曾于永平十三年(70)“行幸荥阳,巡行河渠”,令“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继世宗《瓠子》之作”[24]。该简说明,东汉永平之时,敦煌地区有春秋治渠各一次的活动,自然十分重要。
此外,通过前述敦煌治渠的两枚汉简,可以发现汉代敦煌水渠修治的系统化,如“民自穿渠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水门广六尺袤十二里上广丈”,说明渠道的系统编号,有第一、第二序列号,下又有左、右、内、外的区别。简文“续穿第一渠东端袤二里百步”,也说明有第一、第二、东、西的这种编号。正是这种系统化的渠道网络,才保证了汉代敦煌水利灌溉的有效实施。
从以上零星出土的简牍材料来看,汉代敦煌郡的水利有都水长、水长进行管理,相关的职官还有平水史,而且依据水渠位置,又有东部水、东道平水等职官。汉代敦煌的水利建设,体现出系统化的管理特色。水渠划分有第一、第二、左、右、内、外、东、西这样的编号。东汉永平时,水渠修治还有春秋治渠各一次的季节性特点。这些记载都反映出汉代敦煌水利建设的成就。
以上基于有限的汉简材料对汉代敦煌水利的研究还只是粗略的勾勒。悬泉汉简的内容还没有全面刊布,相关的信息还很零散,因此本文的研究并不能反映出汉代敦煌水利的全貌,仅是管中窥豹,但也可见汉代敦煌水利建设的一斑。
参考文献:
[1]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J].中国史研究,1986(1).
[2]汪受宽.甘肃通史:秦汉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225-226.
[3]郑炳林,李军.敦煌历史地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298-299.
[4]高荣.汉代河西的水利建设与管理[J].敦煌学辑刊,2008(2):74-82.
[5]张德芳.汉帝国政权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对丝路交通体系的支撑[G]// 甘肃省文物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甘肃五处世界文化遗产.2014:76-92.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14.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14.
[8]郝树声.汉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辨 (续)[J].开发研究,1997(3):60-61.
[9]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1:513.
[10]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852.
[11]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8.
[12]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621.
[13]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41.
[14]司马彪.后汉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3564.
[1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883.
[16]袁延胜.西汉分立乌孙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辨[J].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3):21.
[17]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J].文物,2000,(9):94.
[18]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肩水金关汉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0:230.
[19]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152-153.
[2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M].北京:中华书局,1994:198.
[2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1:271.
[22]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69-770.
[23]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725.
[2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