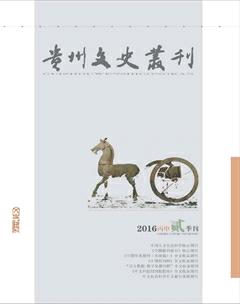浅论黎焕颐随笔散文
黎 洌
(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 贵州 遵义 563002)
浅论黎焕颐随笔散文
黎洌
(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 贵州 遵义 563002)
黎焕颐的随笔散文,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索,一往情深的故土情结,对诗歌创作及现象的思考,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和自我的深刻审视,蕴含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批判精神,颇具启迪意义。同时,也使他的散文具有独特的视点、观念和个体化身份。
黎焕颐 随笔散文 内容特征
黎焕颐1930年生于贵州省遵义县沙滩村一个文化世家, 1953年开始发表诗歌, “平生无所嗜,惟诗与文章。诗文无所求,惟求品骨存钙。”①黎焕颐:《诗欢文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版,封底。1957年后,被流放青海荒原,“在那场奇寒之中——历史的风雪线上,我的青春夭折了,理想受伤了。”②黎焕颐:《诗欢文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版,第 123页。直至1979年平反,才重新“起飞”。先后出版了《迟来的爱情》《起飞》《在历史的风雪线上》《春天的对话》《黎焕颐抒情诗选》等作品,以激越的歌喉抒发被长久压抑的诗情,并大声宣告:“我骄傲:我是中国诗的子民。诗之于我,犹如母亲的乳汁。我之于诗,犹如虔诚的教徒。我只是属于有着五千载渊源的皇天后土,有着列祖列宗为之流血、为之流泪、为之流汗的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当歌我歌,当补我补,当痛哭我痛哭,当贬伐我贬伐,当诅咒我诅咒。此乃我爱爱仇仇、善善恶恶、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灵魂所系。”③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95页。以澎拜的激情歌咏狂泻的性灵,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诗歌风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诗的子民”黎焕颐转入随笔、散文写作。将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思索、醇厚绵长的故土情结、对诗歌的不舍与忧虑,流入笔端,理性地展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和自我的深刻审视,显示出作者的赤子之心和人文情怀。这些作品,结集为《流放与直言》《我爱·我恨·我歌》《和你面对面》《诗欢文爱》等集子,颇具特色,其蕴含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批判精神,极具启迪意义。下分而述之:
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从1957年起,黎焕颐被流放青海,经历了从人到猿的磨难。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青海,对黎焕颐来说,是“生命、智慧、理性、情感的”“最个性、最本色的故乡”,在这里,有他既属于历史,也属于个体生命的聚焦,那个叫1527的编号,那被暴风骤雨阻断的爱情,那本该三十而立、却立在世界屋脊的风雪线上的孤独,那被枷锁在高原雪域的理想和诗情,那躺在无情的塞外风雪中永远回不来了的同志……二十二年的经历,永远难忘,值得回顾和追问。“祖国啊——我的亲娘,你既然给了我春的希望,又为何剪去她翅膀?你啊!既然给了我满天星斗,为何又给我们天狗吃太阳?”①黎焕颐:《迟来的爱情》,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21页。从青藏高原的劳改农场平反回来后,耿直而单纯的黎焕颐面对自我人生,写下了他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反思,在《流放与直言》中,《流放青海二十年》《母难日》《再生的维纳斯》《爱情浪漫曲》等篇文章,都是这段生活的反映。当然,对此记录得更为真实和全面的,是他的长篇回忆录《从人到猿》,唱出了他身陷炼狱、青春被葬送的悲歌,深深地控诉了那黑白颠倒、人猿不分的时代罪恶。
但是黎焕颐的悲歌并不悲情,被关押审判的监狱生活,流放青海孤独苦难的日子,非常人所想。从不解、不服,到抗争无效,甚至想到死。然而,他坚强地挺了过来,以一种坚忍不拔的韧性熬过最艰难的日子。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家人没有抛弃他,哥哥写信勉励他,和他同龄的侄子黎培仁全力的支持他,侄女黎培燕无条件地邮寄米、油、香肠,同为难中的朋友扶持他,这一切,都给与他走过艰难人生以最大的支撑。最重要的,是他从小所受的儒家文化教养,“居陋室,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②陈蒲清注译:《孟子注释》,花城出版社.2008版,第5页。正是传统文化的引领,使他心定神明,坦然接受生活的磨练。“我爱我们民族超越世界的五千年的文明”③黎焕颐:《家书手稿》,《登大雁塔放号》前记。“朝气蓬勃的生活现实给我以光明的诱惑力”,④黎焕颐:《家书手稿》,给黎培仁信。一句话,对祖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使他对这段历史愤而不悲,痛而不悔,“青藏高原的群山雄突,君临宇宙,顶天立地的气概,则给我生命中的文化情结补钙。一句话,青藏高原是我文化情结中的重中之重,离开他,我就无法承受生命之轻。”“我十分重视属于我文化情结中山河之恋的生死情节——特别是青藏高原给我的风、沙、雪、雨的诸般提炼。老实说,没有当年那些岁月的磨砺:陇秦道上的沉重,西牦牛山、柴达木滚滚飞沙,千里风雪,我的生命之链是无法得到深化,我的文化情结是无法享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不息的激越之气的。因此,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阻力,碰了钉子,我总是回首青藏高原……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群羊阵马,那里的芨芨草,那里的干巴柴,那里的边声牧唱,那里的帐篷炊烟,那里藏族同胞的热情慷概,那里苍鹰的高天滑翔……不是吗,这一切的一切,都从我生命的苦恋中化为我取之不尽的文化情结。”⑤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10页。他写青藏高原,“写我二十二年从人到猿的历历如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谏世,才能珍惜从猿到人之不易,杜绝历史的返祖。”所以,“1979年的早春,我得到平反通知。队上的干部,场里管教科的科长,马上就改口,称呼我为同志。历经二十二年劫数,这充满温馨的‘同志'二字,随着他们的手伸出来和我紧紧相握,我悲喜交集,霎那间热泪横流……”⑥黎焕颐:《流放与直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版,第16页。对祖国真诚的爱和希望,使他用自我的经历“谏世”,希望社会或人们从中吸取可资借鉴的东西。他的心灵深处,是永远的潜藏的最深厚的人文情结。历史,只是必须的路程,必要的锤炼,而青海,也只是昨天的底色沉淀,今天表达的背景。
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思索
散文随笔是思想者的文字。每一个作家都生活在现实的土地上,面对现实生活的感应与思考,反映出作家的个性、良心和责任感。黎焕颐不是一个吟风弄月聊以自慰的作家,他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关注社会存在状态,作为一个诗人、文化人,他更多地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风尚与人文生态、道德准则和价值追求。他认为:“任何一个历史社会的道德风貌,都是那个历史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风尚的好坏有如温度表,它从本质上体现了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历来如此。风尚的厚薄、道德的高低,对于一个人是高尚与堕落的界定,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则是兴衰的契机。”①黎焕颐:《我爱·我恨·我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18页。对社会文化问题做出反应和思考,既是黎焕颐随笔散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随笔散文一个重要特点。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化人,黎焕颐与同时代人一样,把对祖国的关爱、对社会的思考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胸怀强烈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参与社会建设,参与时代的文化构建,坦率地表达自我的思考与见解。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深圳和广州的改革风起云涌,面对上海的落后,他呼吁“倘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去其禁锢而诱发之,则戴在上海人头上‘名为稳健实为保守'的盖顶帽必将扔之于太平洋。”②黎焕颐:《我爱·我恨·我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20页。坚信上海能重领“敢为天下先”的时代风尚。
城市建设体现出一个城市的精神。他认为:“市容建设,要和市态、心态联合起来综合规划,综合治理。一句话,要建设市容,首先要建设世态和心态。其中最关键的是心态建设。只有心态建设上轨,世态和市容的建设才有保证。”③黎焕颐:《我爱·我恨·我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27页。表面上看,黎焕颐是关心政治,所以杨明在他去世后说:“他关注时事政治,很敏感,有自己的看法。”④杨明:《黎焕颐:“歌哭从心”的真诗人》解放日报2010.10.11其实他的思考,根本着眼点在“人”。社会的现代化取决于人的现代化,对城市建设的关注,更多地是从人和文化层面进行思考。因为在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人的素质、社会风尚,在改革开放的长河中,即由过去的维权至上转到现在的唯钱至上的轨道时,成了二律背反——只要弄到钱,就不顾人品、文品、官品、乃至灵魂的起码修养,宛如红了眼的拜金狂?”于是,他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要立品。” “人无品不立,官无品必堕。”⑤黎焕颐:《我爱·我恨·我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33页。而“所有的立,都离不开一个字——诚,也就是说,必须以诚贯之,用流行术语来讲,就是不能耍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要认真地戒奸、戒诈,戒虚伪,戒假话、空话、套话、八股话、官场话。因为这些都有害于诚。而不诚,则无从实,一个人不诚实,他何以谈立品?”⑥黎焕颐:《我爱·我恨·我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30页。因此,“为官者,首先是要修身。”“为文者,要有基本的人格。” 面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恶习,作者深怀忧虑,“是不是经济增长、经济繁荣,就天下太平,隐患稀释,百病消除——礼仪兴而廉耻立,人心正而风俗淳呢?答曰,未必全然,要全然,求得长治久安,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积极地自上而下,由里及表,进行艰苦卓绝的、长期的、韧性的文化改革及道德重振。”⑦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58页。为此,他《问郭沫若》,置疑余秋雨,对大而无当的所谓政治抒情诗贬为“洛阳纸贱”;对田兵的越老越透明,陈沂的耿介,戴厚英的自省推崇备至。尽管他的思考尚不深邃,更多是建立在道德至上的传统观念上,但其热血沸腾的拳拳之心仍昭然可见,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当下现实和文化的真诚忧思与焦虑。
醇厚绵长的故土情结
故土情怀,是游子心灵中永远扯不断的丝线。故乡,是连接黎焕颐个体生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点。
贵州遵义沙滩是黎焕颐的故乡。对外地人来说,贵州在历史上的形象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而黎焕颐心中,“我生命的文化情结,是摇篮于遵义沙滩的夷牢溪……我生命的基数乃是贵州的山山水水。”⑧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31页。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赞誉贵州:“天无三日晴,意味着贵州的山不是童山秃秃,而是森林的葱茏;”“地无三尺平,意味着曲径通幽,崎岖的山势并没有被现代的工具理性削平、物化;”“人无三分银,意味着贵州人朴实、本分,并没有物欲化,为了一个利字,就豕突狼奔,丧失人性的原善。”对家乡的真挚情感溢于言表。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贵州的主体优势不是别的,恰好在他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蓊蓊葱葱的自在美。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这片没有污染的后花园,乃是沿江沿海的大城市、乃是西方后工业文明孜孜以求的圣洁领域。”“因而开拓交通,保护幽静的山水,发展旅游事业,这是贵州优势之所在。”①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69页。作《贵州赋》,歌颂贵州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更何况黎焕颐的家乡遵义沙滩不仅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朴的人情世界,还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张其昀在《遵义新志》中将其定位为一学术概念——沙滩文化。作为区域性文化,沙滩在历史上形成了以黎氏为主体、郑、莫为中心、黔北世宦书香人家相互沾溉,互相影响从而形成的社会向学思潮。这里曾经住过宅心仁爱的黎安理,以耕读为本,以孝悌立家,启后兹今;有沙滩文化的开创者黎恂,以进士为读书之始,购书建锄经堂,溉及乡里,最终使沙滩弦歌不断;有“黔之通人”郑子尹、莫友芝、黎伯庸,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将沙滩文化推向世界;有睁开眼看世界的黎庶昌,出使西洋和日本,首创“文化外交”;还有沙滩文化的最后一代传人黎梓,绍继祖风,受困乡里而诲人不倦……数典家族的发展与辉煌,实际上是理清文脉的延续与兴盛,跪拜在祖宗的坟茔面前,是要体认祖宗的风骨神韵、文化遗泽。
沙滩还有着黎焕颐的同胞亲族。黎焕颐在家中排行十一,他的长兄比他大近二十岁,从小对他宠爱有加,“他用双肩驮着我在人丛中穿来穿去(看花灯),看到高兴的时候,我童兴大发,用小小的双手抱着他的头在他肩上直跳。”“他常常以他的身体来掩护我去受父亲鞭打。”②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60页。但在文革中,哥哥受到牵连,被打成了反革命,原本木讷的人变得期期艾艾,“我为之泫然泪下”。而后哥哥去世,作者只能常返沙滩,回味兄弟情缘。还有情如兄弟的侄子黎培仁。“叔侄怡怡胜弟昆,平生数你最情敦。无边风雪君思我,不尽株连我累君。黄卷同温窗外月,青灯共读画中魂。而今肺腑凭谁吐?千古沙滩世纪心。”当初叛逆离家出走,只有这个和他情义深厚的侄子支持他,“他悄悄地将一部康熙时刻的《左传》版本交给我出售,换来一些路费。”③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64页。后来,当黎焕颐被发配到青藏高原经历难熬的三年自然灾害时,还是这个侄子,“他似乎看到我面有菜色,不时从思南给我邮来大包小包的食品,有腊肉,有炒熟之后磨好掺有白糖的糯米面……”④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65页。正是这些亲情,萦怀于黎焕颐的心中,使他故乡情怀依恋浓浓,不矫揉造作,不故发感概。在青海,他用书信问候家乡,表达对亲人的牵挂。平反回上海后,他以喷薄的诗情,在歌颂祖国新生的同时,也回报着亲人对他的期盼。他知道,身后的黎家人、沙滩人甚至黔北人、贵州人并不在乎他有没有权,也不在乎他有没有钱,而是在乎他有没有承续黎家的文脉,有没有传承儒家文化的道统,这种融家族希望与民族理想的期盼,强化了黎焕颐耿耿于心的故土情结,久久萦怀。“从1982年至2006年,年事渐高的焕颐不顾千里劳顿,或单身,或携妻带女,十四次回家乡。摸摸山,看看水,给父老乡亲提个醒,出个主意,希望家乡一年胜似一年。”⑤曾元沧博客:《诗外黎焕颐》, http://blog.sina.com.cn/zengyuancang.这是黎焕颐的报答。没有虚假,情真意切,感心动魄。
对诗歌的思考与批评
黎焕颐是诗人,诗的情怀可谓灌注了他的一生,五十年代初他两次参加革命,都半途而废,虽然伯父黎迈劝他不要做诗人,表哥黎以宁也多次劝阻他从事文学,但仍不改初衷,最后终于走上了文学之路。57年的狂风暴雨将他吹到了漫漫黄沙的日月山外,在生存、生命都岌岌可危之时,仍暗地创作。可以说,对诗、对文学、文化现象的关注和热爱已经沉淀到他的血液之中,贯穿于他的整个生命情感。他说“我是诗的子民”,喜欢李太白,喜欢苏东坡,喜欢袁子才,喜欢闻一多,在精神上与古典诗人和现代诗人息息相通,他的随笔常常写他与他们的精神对话。家族教养、沙滩文化的浸润使他对传统继承多于批评。从骨子里,儒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观成为他创作的准则。认为“诗为心声,非指诗人之歌哭喜怒,实乃历史和时代之灵魂呼号。”而以黎恂为代表的宋学教育,对诚、敬的笃信,以及沙滩文化特有的“道在师儒”的传统,又使他反复强调诗歌创作的真,他说:“诚实应该是诗人的首要品质。”“古今中外,凡是名副其实的真正诗人,大抵皆本色、皆率真、皆落拓不拘、皆敢于直面人生、皆敢于说真话、皆敢于言人之不敢言但又是真理的珠玑。”①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97页。同时也强调个性的保持和张扬,“没有个性的诗,不是好诗。”因为“诗,最讲究情感的流动,最富有自由的色彩;最尊重个性的发挥。”而好的诗歌,“从思想、情感,一直到语言的提炼,都必须富有感染力。”②黎焕颐:《我爱·我恨·我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87页。关于诗的思考,在黎焕颐随笔中,占取篇幅最多,《一粒复活的诗的种子》《我是诗的子民》《诗的断想》《读当代诗坛》《人间要好诗》《诗人和诗的个性》等等,对诗歌与生活的关系、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诗歌的特性、诗歌美学、诗与真实、诗人的品质等新时期诗歌中出现的问题,都一一对之进行分辨、思考,表现出一个诗人真挚的诗歌情感和强烈的反思意识。当然,不容讳言,也正是源于他受到的家学传统及对诗歌的挚爱,使他的诗歌观念固执而保守,对各种源于西方的诗歌思潮和新的诗歌形式,他更多的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对随着文化世俗化思潮而涌来的“各种新潮、各种流派、各种主义的所谓‘诗',”他更是目之为“那些扭曲文字的分行,那些天书秘诀似的符咒语,那些自恋的隐语,那些苍白得谁也无法心领神会的‘诗',难道不应当死么?这是文字垃圾、语言游戏,任何药方都无法使之起死回生。” 要“有胆识来清洗这些‘诗'的垃圾,有勇气来说一声:这不是诗!不论它打着怎样‘新潮'旗号。”③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300页。保守局限了他的眼光,保守也阻碍了他的吸纳和对自我的超越。
勤奋阅读、细心品评
黎焕颐好读书,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晚年后身体不好,难得走出家门,更以书为伴,“十岁左右,……主动读《千家诗》《唐诗别裁》和《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十三四岁,……不管是新诗旧诗我都看,凡是历史的书我都读。十六岁,我又进一步涉猎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④黎焕颐:《我爱·我恨·我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77页。文革中,“拼命地读马列的经典著作”⑤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94页。。晚年,再读《史记》《资治通鉴》及诗友的著作、邓小平讲话等,对黎焕颐来说,“读”是生命的一种形式,读是他看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读书是他“美其身”、“化气质”的重要途径,读书宗旨是要实现自我人格完善。其散文随笔不少是写他阅读中感悟,感悟中的阅读。
读史,是黎焕颐阅读的一个重要内容。《读书眉批》《读史有悟》《读史断想》《偶读偶得》《读史随想》《文化的乡愁》等等,漫步于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他既不像一般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也没有一般利己主义者的急功,而始终在思考这对当下的社会有什么启迪,这对当下的文化有何借鉴……因为经历文革后,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冲击,许多人忽略了道德情操的养成,“操守的价值观,前三十年是不分青红皂白遭到极左思潮的蹂躏,到文革时期,登峰造极。后十年,又受到西方自由化的冲击,举凡传统的价值观念,统统以国民的劣根性目之……就这样,气节也,操守也,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攻。而其后果,则是直接导致思想上的庸人——随风转,政治上的市侩——无所谓原则;经济上的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①黎焕颐:《我爱·我恨·我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34页。对此,黎焕颐感到深深的痛心,他认为,“情操,气节,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元素。”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气节情操,没有高尚的人格,就会“庙堂辉煌的诱惑,常让不少文化人内抗乏力,”②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179页。希望文化人讲求名节操守,敦品立格。他知道,“红尘滚滚,大千世界中的文化界,求浮名易,求文化悟性之真者难。求名而立品立格者尤难。”③黎焕颐:《和你面对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180页。所以他大力赞美陈沂,在陈沂身上,他看到了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血色本性;赞赏袁是德,看到了天道不孤;理解邵燕祥,看到一代人自我灵魂的审讯,希望殷鉴在天,不再有续笔。不管是读史还是读人,他都力求发现美,鞭打丑,为社会树立正气,希望以自己的呐喊,让全社会都重视气节、情操,“恢复他,发展他,充实他,对于社会风尚,对于提高人的精神所养,一定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黎焕颐真诚地去感悟、思考、质疑、反思,提出问题、将对问题的思考摆在桌面上,希望引起人们重视,希望出现的问题能得以改革和解决。这种承继家教中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一方面使他正气坦荡,富有真诚的情感和担当意识,另一方面,也使他的随笔与诗一样,充满浪漫的理想和激情,情感直率、强烈、外向,正如刘学洙所说,“以诗的热情入文,大气磅礴而又化繁为简。”“浪涛直泻,气势逼人”。“亦古亦今的纵横驰骋,情、理两个层面的交叉叙议,处处露出胸中的甲胄,但又决无干戈之声。”④刘学洙:《读〈和你面对面〉致黎焕颐》贵州日报2008.7.15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化,是处于一个大变革、且多元发展的格局中。黎焕颐关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走向,不仅注重生活和人生的思考,也注重文化的使命意识,加之他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他的散文具有独特的视点、观念和个体化身份。正如邵燕祥曰,“焕颐的豪情也是‘曲子缚不住者',兴来秉笔,常‘以文为诗',且不避文言,自成一体,自成一家,置之百十家中,一眼就可辨识。逐字逐句推敲,或难免感到粗疏,但掂量题材内容,那旷野的风沙和粗犷的心境也许恰恰相称。”⑤邵燕祥:《送别黎焕颐》http://www.ycwb.com/ycwb.
责任编辑:何 萍
To Talk about the Casual Essays of Lihuanyin
Lilie
Li Huanyin's casual essays, which gives a lookback and deep thinking on the historic tragedy from human being to ape of twenty -two years. To worry about deeply all kinds of evil habits of modern society, to call the moral behavior of oneself;he had the deep emotion with the hometown of Guizhou Province.He has deed feeling toward the Shatan Culture which fed him here, to emphasis that the poet should have his own characteristics.The poems should be honest and face to life. Reading the poems should have them as their good examples. He thought that “Moral deed and spirit,are the spiritual element of our nations. ”It makes his essays have special viewpoint, world look and his individual identity.
Li Huanyin;the casual essays;the content characters
I207.6
A
1000-8705(2016)02-99-104
黎洌,生于1987年,女,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地域文化研究。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黎焕颐创作研究”,项目编号:JD2014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