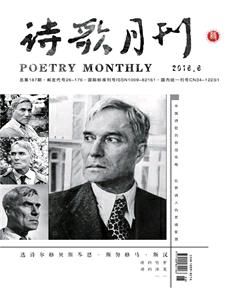炉边补诗话
陈先发
1、一个诗人真正需要的从来就不是什么知音,也并非一个对立面。在俞伯牙对面,钟子期只是假象。当诗人向外索求一个知音或对立面时,他想谛听的是哪边的丢失感更深。他会往那里去。正如一个盲者无须见得桃花也不必识得刘郎,但他会闯入“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巨大丢失之中。在那里,他看到自己并可互酬以涕泗滂沱的永恒情感。
2、诗是对已知的消解。诗是对“已有”的消解和覆盖。如果你看到的桦树,是体内存放着绞刑架的桦树,它就变了。如果你看到的池塘,是鬼神俱在的池塘,它也就变了,诗性就在场了。诗即是将世上一切“已完成的”在语言中变成“未完成的”,以建成诗人的容身之所,这才是真正的“在场”。
3、一个经典作家或诗人,并非人类精神领域匮乏感的解决者,而恰是“新的匮乏”制造者。制造出新的匮乏感,是他表达对这个世界之敌意的方式。换言之,也是他表达爱的最高方式。而且,他对匮乏的渴求、甚于对被填饱的渴求。
4、我们常常谈论现实二字,我觉得对诗歌而言,存在四个层面的现实:一是感觉层面的现象界,即人的所见、所闻、所嗅、所触等五官知觉的综合体。二是被批判、再选择的现实,被诗人之手拎着从世相中截取的现实层面,即“各眼见各花”的现实。三是现实之中的“超现实”。中国本土文化,其实是一种包含着浓重超现实体的文化,其意味并不比拉美地区淡薄,这一点被忽略了,或说被挖掘得不够深入。每个现存的物象中,都包含着魔幻的部分、“逝去的部分”。如梁祝活在我们捕捉的蝶翅上,诸神之迹及种种变异的物象符号,仍存留于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四是语言本身的现实。从古汉语向白话文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主导的缺陷性过渡,在百年内又屡受政治话语范式的凌迫,迫使诗人必须面对如何恢复与拓展语言的表现力与形成不可复制的个体语言特性这个问题,这才是每个诗人面临的最大现实。如果不对现实二字进行剥皮式的介入,当代汉诗之新境难免沦入空泛。
5、传统几乎是一种与“我”共时的东西。它仅是“我”的一种资源。这种——唯以对抗才能看得清的东西——裹挟其间的某种习惯势力是它的最大敌人。需要有人不断强化这种习惯势力从而将对它的挑战与矛盾不断地引向深处。如果传统将我们置于这样一种悲哀之中:即睁眼所见皆为“被命名过的世界”;触手所及的皆为某种惯性——(首先体现为语言惯性);结论是世界是一张早已形成的“词汇表”。那么我们何不主动请求某种阻隔——即,假设我看到这只杯子时它刚刚形成。我穿过它时它尚未凝固。这只杯子因与“我”共时而“被打开”,它既不是李商隐的,也不是曾写出《凸镜中的自画像》的约翰·阿什伯利(John Ashbery)的。这样,“我们”才有着充足的未知量。
6、即兴谈谈诗,切口很多。我眼中好的诗歌一般要满足三点,一是语言的精准度。这里所讲的精准,不是物理的、机械标尺那个意义上的,而指审美判断与想象力的高度契合。我们读一首诗,察觉到某个词的不可替代、某种物象的不可撼动,这就是精准度的实现。即便是想象力奇崛的非常态表达,其微妙意味与语调、语速、语境也有个“最佳咬合度”问题,比如,白发三千丈,你换成六千丈或三千米试试,味道就丧失大半了。我读诗,讲求“余响”与“况味”,如果我们抡着语言的锤子,如果砸不中,哪里会有咣的一声,遑论余响了。也正如一个厨师不能将他臆想的滋味精确地传递到别人的舌尖一样,精准度的普遍缺失,是当前宏观写作图景中的一个症候。二是语言的强度。有时一个诗人的方位与方式,都没问题了,如果他语言的强度不到位,那么,他很快会被同一方向上更具强度的诗人所覆盖。何谓强度,简而言之是他的语言方式对阅读感受力的冲击程度。事实上,许多时候强度不够,来源于思之不足。思的匮乏,是导致千人一面千诗一味的病根。云至天边,思到穷处,哪怕以最日常话语的面目出现,也是强悍的。三是文本具有的与时代境遇相匹配的某种复杂性、具有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力。相比而言,我更喜欢那些充满矛盾的、对立的、布满光与影的内在空间,甚至是一种病态的空间,与时代的某种特异气息相响应、相吐纳。当然,这种本质上的复杂性,有可能通过很简洁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复杂性呈现的外在方式越简单,就越高级。至少我的阅读范围内,还极少有诗人的力量足以匹配这个时代内在的混乱、断裂与变形。
7、父母命令我杀鸡。我不能拒绝这个被生活缚定的使命。我提着刀立于院中,茫然地看着草坪上活蹦乱跳的死鸡。我在想,我杀她的勇气到底来源于哪里呢?我为什么要害怕呢?突然间想起了戊戌刑场上的谭嗣同,一种可怕的理想冲至腕中。是啊,我使出当年杀谭嗣同的力气杀了一只鸡。这无非是场景的变幻,正如当年的刽子手杀谭嗣同时,想到的不过是在杀一只鸡。相互的解构,无穷的挪动,从具体之物的被掏空开始了。
8、美即有用动身前往无用。
9、尺子在物体上量出“它自己”,这如同我经常用自己的逻辑去揣度“我之外的”一切。当尺子显现时,它几乎类同于我:一种从未挨过饿、也从未被充分满足过的怪物。
10、过度地依赖间接经验使我们“观看”和“倾听”大大削弱了。我们目睹的月亮上有抹不掉的苏轼,我们捉到的蝴蝶中有忘不掉的梁祝。苏轼和梁祝成了月亮与蝴蝶的某种属性,这是多么荒谬啊,几乎令人发疯。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呢?目光所达之处,摧毁所有的“记忆”:在风中,噼噼啪啪,重新长出五官。
11、思想必须像绞肉机一样清晰地呈现出来。置此绞肉机于修辞的迷雾中,要么是受制于思想者的无力,要么是一种罪过。
让绞肉机自身述说——而不是由你来转达这个声音——“瞧,我在这里”!
以“思想着”和“共享着”的状态来克服思想所附生的深深恐惧。
12、远处的山水映在窗玻璃上:能映出的东西事实上已“所剩无几”。是啊,远处——那里,有山水的明证:我不可能在“那里”,我又不可能不在“那里”。当“那里”被我构造、臆想、攻击而呈现之时,取舍的谵妄,正将我从“这里”凶狠地抛了出去。
13、去年秋天我经过黑池坝,看见一个驼背老人,从湖水中往外拽着一根绳子。他不停地拽呀拽呀,只要他不歇下,湖水永远有新的绳子提供给他。
今年秋天我再经黑池坝,看见那个驼背老人,仍在拽出那根绳子。是啊,是啊,我懂了。绳子的长度正是湖水的决心。我终于接受了“绳子不尽”这个现实。他忘掉了他的驼背,我忘掉了我的问题。湖水和我们一起懵懂地笑着:质疑不再是我的手段。
14、看到街上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跑动。哦,他跑得那么地快。我想:他一定饿了,会扑向街角那个炸麻雀的油锅。可是——他并没有扑向它。这里面的真正玄机是,我饿了。饥饿的感觉从胃中升起,而且它蜕皮了:“饿了”这个词出现。词在跑动。
但在我的语言谱系中,“饿”这个词从不扑向“饱”这个词。
15、醉心于一元论的窗下,看雕花之手废去,徒留下花园的偏见与花朵的无行。有人凶狠,筑坟头饮酒,在光与影的交替中授我以老天堂的平静。谢谢你,我不用隐喻也能活下去了,我不用眼睛也能确认必将长成绞刑架的树木了。且有嘴唇向下,咬断麒麟授我以春风的不可控,在小镇上,尽享着风起花落的格律与无畏。
16、我看见词汇在我的诗中孤立地哭泣。不是别的诗,正是这一首。不是别的什么时候,正是此刻。它哭泣它们的孤立。世界即是一份硬而冰冷的词汇表。我们在词中的漫步又能解决什么?这么久以来,我竟然以为在这些词汇中搏动的是我的心。我竟然认为逻辑即是一种“搏动”。我竟然认为可以为这种“搏动”设立一个位置。我竟然认为这个位置就在我的紫檀座椅之上。我竟然认为自己即是那千杯万盏。
17、一首好诗,往往是只有去路、没有来路。我看到许多诗人忙于阐释,都企图将这“来路”讲清楚,瞧这是多么徒劳的一件事。写诗为世界增添神秘性,来源的混沌与爆发时的意外,是它最可爱之处。诗唯一无法解构的,是这个世界的神秘性。但又必须不断地去解构。这正如诗人之手,既是建庙的手也是拆庙的手。一首好诗,甚至不需要作者。从一首好诗去追溯一个诗人,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18、语言于诗歌的意义,其吊诡之处在于:它貌似为写作者、阅读者双方所用,其实它首先取悦的是自身。换个形象点的说法吧,蝴蝶首先是个斑斓的自足体,其次,在我们这些观者眼中,蝴蝶是同时服务于梦境和现实的双面间谍。
19、诗人应该有一种焦虑,那就是对奢求与集体保持一致性的焦虑。好的东西一定是在小围墙的严厉限制下产生的。一个时代的小围墙,也许是后世的无限地基。这种变量无从把握,唯有对自我的忠实才是最要紧的。写作时而是这样一种行为,即写作者在调适他本人与语言的、与周边世界的、与自身的各种危险关系,不是祛除这种危险,多数时刻是增强这种危险度,他自己才真正地心安。而从读者的角度,如果读一个人的作品,没有让你对世界或对语言本身产生某种新的饥饿感,事实上你完全没有必要再去读这个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