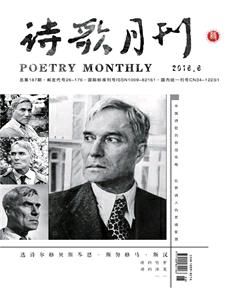宫白云的诗
宫白云
霜降
树上伏着稀疏的白云
在冷风中颤栗
曾有乌儿在那里的枝头鸣唱
村庄从未留住那些途经
那白发人,仿佛还在三十年前
挥着他的手臂
我看到的那霜白
一直在视线中闪烁
也许冰凉的暖,才是它的宿命
就好像菊花败了又开
这凉薄的节气替我翻看了一下那时的山水
在它往复的尘埃之上
我觉得已旧的血又再度新鲜
仿佛迎着朝阳的小孩
弥补我的衰老
直至静寂将我包裹
他将替我年轻
有些面孔
再也找不到了——
那片江水和某个夜晚,鸟落到水面的声音,
它们打开翅膀的位置。
最初的景致已隐藏,
就像有些面孔,尽管仍苍白地挂在什么地方,
却没有人在什么地方怀念。
当一个孩子用一个石子打破水底单纯的白云,
我忍着它的呼喊,吹一吹身边的空气,
一树一树的落叶苔藓一样
生在这个秋天。
植物之心
白露过后,秋风像一个卷裤脚的人
走过田野。空气里溢出
新鲜稻穗的气味。
四周的秋声比告别声多了些漩涡,
它们的发生,
没有确凿的时刻。
傍晚的金黄悬在半空,
这么多年,某根神经依然
一根筋地留在水中,在一些清晨和夜晚,
果实的气息触碰她的脸颊和手指,
秘密的呓语,如一株植物认出
另一株植物。
尘埃
像一些醒着的亡灵,搭配着世间的孤独,
在灶台、瓦罐、木盆、簸箕和铁器中浓缩自己
和人世之间那孤零零的牵连。
我能向它们询问什么,谁还记得那时的人,
那时的光鲜,那时的热气。
秋风运送着荒凉,赶路的人没再回来。
太阳疲倦地等待血管的衰老,
少年如何领略人世的薄凉,又如何变得隐忍。
时间浸透尘埃中的锈迹,却压不住一道
阳光漫过世人的额头。
一些温存只有写下来才更好,
才会看见微弱的存在。
晚风下的槐香
槐花一开
晚风的忧郁就散了
仿佛我们都有一些念想,朝着各自灵魂的方向
空气里总是藏着一些声音
当有些呼唤飞回来时
一只鸟
就是一座村庄
占卜者
嘴里念念有词
掐指算计着人来人往的前世今生
仿佛通晓所有的因果报应
而我也曾三生有幸
在另一个往世花好月圆
和爱我的人放牧过羊群
一起制造蜜糖、欢愉和传说
西风起,占卜者嘴角一圈光晕
我极目搜寻那片好看的山坡
一行泪水不知为谁所倾
花朵在自己的花蜜里打坐
虚妄蹲在自己的牢笼
占卜者蹲在自己的摊前
占卜别人的一生
太阳落山了
黄昏很美
美得我无从描述
异己者
取一杯酒,听鹧鸪唱歌
偏有不知趣之人破坏这一幕
掏出弹弓对准鹧鸪身上的黑白眼珠
手心捏一把汗
想象鹧鸪化成空气逃走
想象何其漫长
仿佛衰老的一生走在阴郁的街头
路遇树下的繁花
难免孤身凝视
那堆白雪在内心的呼应下
渐渐发出鸟的欢叫
十月
有宏大的主题和金黄的阳光
人们跟着它走
而村庄还站在原地
只剩下盲者
天空和他对弈
盲者从不盲目,只是一味地敬重一种东西
他守着自己的荒废
他的灰发
荒草下的一条
灰白小路
倒退者
常在江边走
鞋也湿了几双
大概还想遇到几个有意思的人
倒着行走的人把鞋
拎在手里
晚风又吹起来了
前方的小男孩牵着宠物狗
也在倒退着走
天空的蓝
褪色的比预想来得更早
落日的余晖烁烁地翻动江面
那些后退的潮水
青青涩涩
又涌了回来
风吹不走什么
秋风流水样过后,一些树荫正在远去,
悬着的都落了地,
没有谁去过问落下的卑微。
任何命运都有归宿,燕雀怀揣必要的幻想飞走。
风吹不动的人,
坐在孤独的树下,不愿意回望——
干涸的井水,老屋的伤疤,
黄昏的狗吠,隔三差五的葬礼,
一个村庄的荒芜。
立冬
没有预想的那么寒凉
树隙间仍有阳光晒着扫落叶的人
缓慢的江水也还在懒洋洋地流淌
我还在缓缓地把一束散发扎成马尾
我们都不急于奔向冬天
我们都还爱着这满地的金黄
眼眶里都还有着不可阻挡的温暖感动
季节的按部就班
我只须感知
从嘈杂的大街上走过
每一个人都是他们自己
奔向各自火热的生活
吃着热腾腾的饺子
等待日子
在遮盖一切的雪中变白
衰老者
每天拎着小马扎准时走出他的房门
太阳走,他也走
墙根,街角,向阳的台阶,公园的长凳
他仍需要身上撒些温暖的阳光
需要和一些老伙伴说会话儿
拍拍彼此的肩膀
一起笑一笑
努力活着
太阳落下山的时候
抱着自己的憔悴
嗓子眼里哼着一首微弱的老歌
边回家走边时不时地回头
黄昏的金黄照着
他的鼻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