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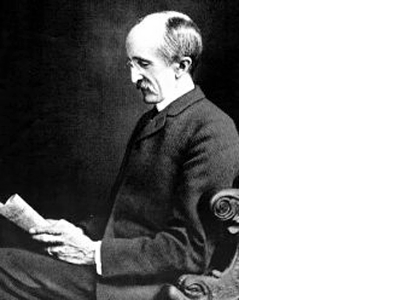
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发自上海、北京
车在前医生的日程井井有条。他供职于上海瑞金医院的急诊科。
通常,他早上5点50分起床,6点刚过出门,顺手带上自用的小药盒——他有医生中常见的高血压和腰椎问题。他半小时后到达医院,边吃早饭,边打开电脑,查阅病人的病情和化验单,再巡视一圈,与病人聊一会儿,避免漏掉重要信息。七点半,他与夜班同事交班,开始查房。
车在前负责18张病床,新来的和病情不稳的病人,需要格外关注。查房将近11点结束,他开始做的换药、穿刺、引流和血液净化等操作,都关系着危重病人的诊治。
下午四点,车在前开始接待家属。他本应五点下班,往往因危重病人而拖到七点多钟。遇上紧急抢救,他可能连续工作48个小时,甚至更久。
从1993年上大学开始算,车在前跟医生这个行业打交道已经23年了,大多数时候,他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不可能病人家属哭,我们也跟着哭。你要冷静下来,控制整个场面,安排医护人员抢救,同家属沟通,安抚他们的情绪。”偶尔,他也无法保持超然。
2015年9月15日,一位年轻人因为海鲜中毒入了院,下消化道大出血。医生忙着为病人做血液净化,父母在一边双手合十祈祷,面容悲戚。车在前反复向焦急无助的家属们强调,医生非常想救他:“24岁我们都经历过的,他太年轻了……”
病人稍有好转,但转天上午,消化道大出血,医生紧急从血库调血,用尽了所有医学手段。15个小时后,深夜23点,抢救终告失败,这个年轻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病人的身体机能逐渐消失,家属在走廊哭泣。车在前原本可以离开了,但他站在病床前,几乎是下意识地,一点点擦干净病人的血,做些清理。
对车在前来说,他有48个小时没法合眼,除了这位年轻的病人,他前后还得救治另外两位老年患者,虽然另外两位都抢救成功,但最终还是得遗憾地送走这位年轻人。医学的能力有限,车在前只能感慨:“你没得选啊。”
2016年6月11日开始,十集纪录片《人间世》在上海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每集一个主题,包括急诊室、急救车、器官移植、临终关怀……通过医学反映社会基层人与人之间的故事。这次抢救,出现在纪录片《人间世》第一集中。
“医生百分百愿意 让病人活下来”
周全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深度报道团队的负责人。团队的工作职责就是找题材、拍片子。
一开始他们想拍的是基层治理。编导团队走访过居委会、派出所,发现都不太好用纪录片的方式呈现。然后挑上了医院,基层医生、医改、看病难……一脉相承。
《人间世》的编导团队是四个小伙子,四位编导下到医院,分头带领八个摄制组拍摄,每组六七个人。
周全在《人间世》担任总导演。开拍前,团队就确定要在医院扎下去,希望编导和医生建立充分的信任。大家开玩笑,说要加上医生的微信,“看到他们脱下白大褂,放下手术刀,半夜两三点钟发出一条最真诚的朋友圈,能够参与他们朋友圈的讨论。这才足以开拍。”
上海市卫计委非常配合《人间世》的拍摄,组织了22家医院参与了协调会。此前,卫计委曾与东方卫视合作过急救真人秀《急诊室的故事》。
编导之一秦博在瑞金医院蹲守了超过一年半。他从前也因看病排队而焦虑,拍纪录片,才知道了长队另外一端的故事——秦博说,2016年7月4日到10日,瑞金医院仅内分泌科4间诊室就接诊3692人——平均每个诊室每天要接诊131人,而每个诊室上午和下午都只有一位医生。
瑞金医院的急救与心脏手术,一开始就吸引了秦博。2015年,心脏外科主任赵强做了七百多台手术。赵强的微信签名是“每天都要开心”,秦博“细思极恐”:他真的每天都要“打开心脏”。后来,秦博才知道,在医学界,心脏外科是难度最高和风险最大的科室。
每早七点半,秦博去旁听心脏外科的晨会。医生们对照心脏造影的X光片,现场讨论复杂病例。虽然不懂,秦博也慢慢悟出些门道,“至少能从医生讨论的语速,对于手术方案的争论,判断出这个病人的情况大概糟糕到什么程度。”
2015年7月,大队人马进入各家医院,《人间世》开始拍摄;三四个月后,他们大概对每集内容有了设想;又过了半年,才开始慢慢磨稿子。
在心脏外科,秦博起初想拍富有戏剧性的成功案例:“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经过生死抢救,奇迹发生,病人起死回生。”然而医生告诉他,这种情况概率很小。
赵强医生要主刀一台马凡综合征患者手术。马凡综合征是先天性疾病,临床表现复杂。这位患者的父亲,早年就因马凡综合征去世。而他本人的状况也极不乐观:主动脉随时会撕裂,大出血死亡。救治他的可能性只有一个:为他全身的主动脉换上人工血管。
救治全程,秦博都在场。他看到患者的整个身子被斜着剖成两半,几乎要呕吐出来。因为场面过于血腥,他们没有拍摄这场手术。
术后第二天,马凡综合征患者急性肾衰竭,不幸去世。母亲抱着孩子的头拼命哭喊,摄像师当场泪奔,实在拍不下去。大半天时间,摄像师一直不吃饭,情绪持续激动。
赵强花了16个小时拼下这台手术,手术方案设计齐备,手术也完成得很好,但病人发生功能性衰竭,最终过世,他实在不知道原因何在。“我如果知道办法就好了。”手术过后,赵强失落难耐,他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一个人待在里面,过了很久才出来。
摄像机也向人们展示了赵强兴奋的样子。历时五个小时后,一场极为特殊的心脏手术成功,他如释重负:“胜利了,胜利了,谢谢各位!”面对镜头,赵强难掩兴奋地和同事们握手。
“有时候,医生希望患者活下来的愿望,可能比亲属更为强烈。他们100%地愿意让病人活下来,因为这证明着医生的能力。”一位医生告诉秦博。这也是医生们的共识。
小白人和小黑人,天天打架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美国医生爱德华·特鲁多充满无奈的墓志铭,从19世纪开始,在医学界流传至今。
车在前曾在肿瘤科工作过一段,最直接地看到“医学的不可为”。“病人走向死亡的话,家属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车在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医生在做的,往往就是为家属保留这个接受过程。
几年前,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被送院抢救。留学生的狗跳进水池,池里电缆漏电,狗当即触电。他不明情况,下水救狗也触了电。留学生脑缺氧估计超过20分钟,已经没有救治希望。医生们还是投入很大精力,抢救四十多分钟后,自主循环恢复,维持了大约两天,让从俄罗斯赶来的家人,再看他最后一眼。
不久前,浙江丽水的一家三口吃野蘑菇中毒,远道转运到瑞金医院,紧急收治入急诊ICU。一入院,医生马上安排血液灌流,尽量把毒素清除。为方便护士照看三台机器,三口人起初被安排在一起。确认病人不再需要血液灌流后,医生们想来想去,把情况稍好的一个病人转去另一个区域——按照经验,类似中毒状况的死亡率大约95%。“我们觉得不能把一家三口放在一起,左看右看,都是亲人,如果去世,多吓人。”车在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经过救治,男青年和岳父先后出院,岳母不幸去世。“老头老太太都六十岁了,结婚早一点的话,夫妻感情起码三十年以上,老头看着老太太死去,太惨了。”时隔几天,车在前依然为老两口慨叹。
秦博还记得车在前在一位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离世后的沮丧。那时,手术失败后,车在前对着摄像机说:“好了,好了,不要拍了。”然后一个人扎进值班室里,想自己安静一会儿。“医生总会有这种状态。”秦博说。
治,还是不治,也时常考验着医生。有些病人,治疗难度大,经济条件又不允许接受更多治疗。“有很多东西,超出了目前绝大多数家庭的支付能力。”车向前历数着这些昂贵的心脏耗材:起搏器10万元,有的辅助装置,25万也未必够……
“老毛内心里面,有个小白人和小黑人,天天打架。小白人告诉他,这个病人没钱;小黑人告诉他,没钱就不看了吗?”车在前说,急诊科主任毛恩强要考虑救人,还要斟酌病人的承受能力,车在前能感觉到他的压力:“老毛一发话,我们就往前冲。”
自己抢救后去世的病人,车在前只要在值班,都会送出病房。他会跟家属握手、拍拍他们的肩膀,再和他们说几句:“你们尽力了,我们也都尽力了,但是真的没办法。”
“这是我给他们最后的一个安慰,更多的,我们做不到。”有时,车在前一直把病人送去“善别室”。这方空间在急诊大楼地下一层,25平方米。白墙上有句伤感的惜别之诗:“生命的凋零如秋叶之静美,不是结束,而是开辟了另一段旅程,请让每个生命安静、有尊严地逝去。”
病人去世后,车在前一般会主动留电话号码给家属,办报销、疾病诊断证明书等手续时,也许能帮上忙。2015年中秋节,那位24岁病人的家属发来短信:“您给予我们的全方位支持和帮助,我们都铭记在心。临床有各种风险,现实很残酷。中秋快乐。”
“很久没有得到这种理解和安慰了。”车在前说。
无解的医患关系?
纪录片播出以后,车在前一直没看。一次分享会上,他说自己“内心逃避,不愿看,不敢看”。
2016年7月,他和自己同为医生的妻子,也成了病人家属——他们的儿子生病了。起初,孩子持续发烧、腹泻,白细胞经查不高,父母工作忙,就在家里服药治疗;这段时间,孩子体温一直没降,再去检查,医生认为是肺部感染;7月5日早上,拍了张胸片,诊断证实,孩子住院输液。
照顾孩子住院,监督吃药……这一次,车在前的妻子担负起大部分责任。车在前尊重儿科医生的判断,没发表什么意见。“你没有深入地参与进去,还指手画脚,就不对了。我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干预治疗。”车在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说这话的时候,他还穿着一件绿色制服,套着白大褂,样貌斯文,声音平静:“我还算是一个比较合格的患者家属。”
然而在生死关头,没有几个患者家属能保持平静。
2015年9月28日傍晚,几名家属没法接受病人心衰危急的结果,在非探视时间闯进监护室。其中一个男性家属,一言不合就钳住了车在前的脖子。车在前猝不及防,忙用手挡,却还是被推后了几步。这段口角,被医院的监控摄像头拍了下来,剪进了《人间世》。父母知道他工作忙和累,但并不了解详情,一天突然说起:“你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车在前揣测,他父母可能已经看过了纪录片。
因为拍摄要征得家属同意,所以摄制组与家属的交集很多。此前,秦博并没什么特别的就医经历。拍摄期间,他才看到了别人的就医故事,和真实的医患关系。
有位母亲,从安徽到上海来看儿子。结果老人突发心肌梗死,室间隔穿孔,被送到瑞金医院抢救。抢救费用很高,小伙子不断地问医生,手术大概要花多少钱,老人在安徽买过“新农合”,能报销多少,医生说不出来。彼此都不愉快。
“中国的医保制度,就是一个省里都有区别。”秦博特别理解,别说医生,医务处处长可能也答不上来;但是小伙子的询问又是理所应当的:“我看病花几十万块钱,我能报销多少,当然要了解一下。”秦博揣度。最后,小伙子只好打电话去安徽,才掌握了报销情况。
有回在医院,小伙子碰上了母亲的主治医生。医生上午连着做了两台手术,刚下电梯,还没吃饭,疲惫不堪。两人讨论起老太太的病情,小伙子说,医生之前没跟自己说清楚医药费用;医生也有些恼火。两人话不投机,争执起来。“你站在彼此的角度,会觉得他们都不容易,但又毫无办法。”旁观的秦博,又一次试图去理解双方的困境。
老人昏迷一个多月,历经三台手术后去世。秦博陪了小伙子将近两个月,临走时,小伙子发来短信:你人还挺好,就是在医院待得时间长了,别待麻木了。
“我才在医院待了不到两年,看到这些还会有所感触。可那些医生,一待就是几十年。”秦博感慨,面对长期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能不麻木?
安徽母子的故事篇幅较长,秦博再三犹豫,没有放进成片。和这个故事一样没有放进成片的,还有更多的医疗纠纷,有太平间的守夜人、殡仪馆的化妆师……
特别遗憾的,是上海长海医院烧伤科的故事:烧伤病人的恢复过程极其漫长,需要反复植皮;有些重症病人,烧伤面积95%以上。目睹非人的痛苦,秦博寒毛直竖:“话说得糙一点,都跟‘鬼一样,但是他们想变为人。” ▶下转第26版
医生对医务的敏感,也让秦博吃惊。片中有一个细节,抢救时,画面边上有一位护士,抓紧时间去抢肾上腺素,为病人注射。也许碰到,也许疏忽,她一时没戴好口罩,露出一个鼻孔。编片子时,秦博根本没注意这个画面。审片时,院方放大画面观看,反馈:抢救没有成功,这个画面如果被别人看到,是不是会引起医疗纠纷?
医生们的担心,让秦博觉得不是滋味:“医疗纠纷,可能就是抠着你这点问题”。
“生和死的事情上, 我是一个 买了票的观众”
急救争分夺秒,医学还有另外一面。初到舒缓疗护病区,董路翔发现那里的节奏非常缓慢。“能走的都慢慢走,不像大医院,能跑就不会走。”设立舒缓疗护病区,主要为缓解晚期肿瘤病人的住院难题,让他们去世时享有尊严。
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舒缓疗护病区,有50名医生,58名护士和99张床位,是上海第一家。成立十年,那里送走了一千多位病人,最大的103岁,最小的只有3岁。绝大多数住院者,很快离开人世。
董路翔负责《人间世》的第二集和第四集的编导工作,前者讲救护车的故事,后者关注临终关怀。一快一慢。
蹲守近两个月,他发现病人大概分为几大类:肺癌、直肠癌和其他癌症。快三个月时,他开始怀疑自己生病,浑身不舒服。医生告诉他,自己在上学时也有类似经历,有时,每学一种新病,就觉得自己也得上那种病。
那时,董路翔自己租房住,一个年轻人在上海上班、闯荡,特别害怕孤零零地死在家里,晚上不敢睡觉。“没办法,太密集了,三五天死一个。”董路翔见过一个女人,癌症患者,30岁出头。第一次见,她坐在病床上,喊疼,母亲陪在一边;第二次见,她已经躺下了,没法再坐着说话;第三次再见,女人去世了。女人从生到死,只有短短一周。
在此之前,1989年出生的董路翔对死亡接触很少。仅有的印象来自家族里的一位老人。老人患了胃癌,大家商议要不要治疗。关键是钱和孝,如果不治,就是不孝。后来,老人接受了象征性的治疗,大家也获得了安慰。那时董路翔上小学,记忆已经模糊。
董路翔与医生们混得很熟,遇见病人和家属,却总也张不开嘴。病区里的病人,大都快要走完一生:“我没结过婚,没生过孩子,人生大事一件没经历过,跟他去讨论什么问题呢?我一点资格都没有。”
直到遇见王学文母子,董路翔才走出瓶颈。王学文是腮腺癌晚期病人,在舒缓疗护病区卧床五年。他每月洗头、理发一次;为医保结算,每三月轮换出院一次,周而复始。拍摄期间,王学文与母亲,分别过了50岁和80岁的生日。
“我一直在想,王学文五年到底送走了多少人,一个房间六个人,最慢一个月就会清一次的。”董路翔无法体会王学文的内心。但他逐渐知道,死亡有基本的过程:慢慢地不能下床活动,不能行走,不能直立,不能进食,不能睡觉,不能排尿,没法自己赶苍蝇……
“痛苦和恐惧不来自疾病本身,而来自人为什么有尊严,为什么人在死的时候要谈尊严这个问题。”董路翔觉得,病人觉察到身体中人的属性正在流失,就更加需要尊严。
以前,王学文在家中卧床,几天就睡出个褥疮。病区的护工小郑来帮他换药、翻身、整理被子,更换尿布,他诚恳地感谢对方:“谢谢小郑。”
董路翔和王学文聊天,他说:“这么多年,你就像一位观众,送走无数病友。”王学文回答说:“在生和死的这个事情上,我是一个买了票的观众,你们是没买票,站在门外的观众。”
王学文身体虚弱,但生命力异常顽强。他发高烧非常严重,拒绝检查,拒绝吸氧。他为什么能活这么久,现在病情怎样,医生全然不知。
左手边的病友离世。王学文静静地躺着,手里拿着病友外孙女送他的生日礼物。旋转木马形状的八音盒,因内里的灯光显得晶莹,慢慢转动,和着卡通片《天空之城》的悠扬配乐。“86岁那算是喜事了,如果让他这样熬着,他其实自己还是非常难过的。”他平静地说。
董路翔和王学文的母亲聊天,没说十分钟,就开始掉眼泪。董路翔从没亲眼见过一位80岁的老人落泪。与病人和家属相处,董路翔真切地感觉到他们的煎熬,无论年龄长幼,情理相通。很多病人家属跟他说过:“小董,我也仁至义尽了,真是想脱手。”
“我一定要站在家属的这边讲话,他们是勇敢的,不管怎么样,他们愿意最终把病人送到这儿来。”董路翔觉得,自己能够理解这些家属。
节目播出,很多人看完反馈:让他想起了已经去世的父亲。董路翔一一给片中的病人或家属发了短信,感谢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接触王学文这段时间,董路翔娶了这家医院的医生。他给王学文发了自己的结婚照,也送他喜糖。7月初,董路翔又去看望了王学文。每次聊天,他都问一句:“最近怎么样?”回复:“一切正常。”这是最令董路翔安心的回答。
2015年,这个舒缓疗护病区送走了145位病人。很多人接受舒缓疗护,董路翔觉得欣慰。白发苍苍的临终关怀专家施永兴医生,曾对他感慨:“小董,我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死亡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