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上,你不懂就闭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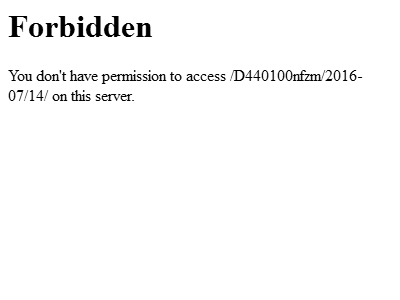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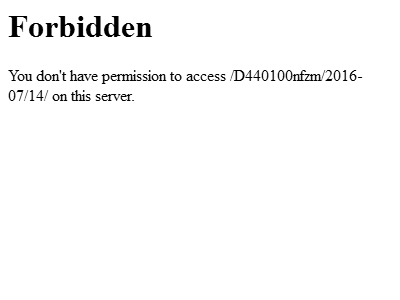
黄柘淞
公民巡视
基础题都不太会做,却非要去攻附加题,就算你答了一百道最后不也是0分吗?
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很快在国内形成舆论热点,多有网民嘲讽公投的愚蠢、民众的盲目,一度出现热门词汇“不错,这很英国”。脱欧是远见卓识,还是胡作非为,英国问题研究专家恐怕也难以当即定论,但我们的网民却偏偏技高一筹,不管了解几分英欧渊源,不管能认几个英文单词,却也能够目光如炬、洞见未来。当然,这是装的。
这正是社交网络的一个现象——许多人热衷于在缺乏知识背景的情况下跨界评点,言之凿凿,道路纷纷,如指诸掌,信手拈来,无论在语气还是修辞上,都看不出一点心虚的痕迹。所以你会发现,最喜欢讲转基因的是电视人,最喜欢评历史的可能是个医生,律师在谈武汉洪水为什么肆虐。广大网民的思路就更开阔了,从声光化电到子曰诗云,几乎没有哪个学科、哪个领域不曾留下他们的指点。
1933年蒋廷黻曾说:“现代人的知识或者不比古代人多,但真正的现代人知道什么是他所知道而可发言的,什么是他所不知道而不应该发言的。”他讽刺当时的现象:“未曾学医的人,忽然大谈起药性来;平素决不注意国际关系的,大胆的要求政府宣战。”蒋廷黻当时批评的是民国知识分子,但他应该未曾想到,这种越界讨论的情况到现今反而更烈——不仅是知识分子,就连一般网民也可以“大谈药性”了。
什么是可发言的?什么是不可发言的?这取决于我们的知识背景能否支撑我们的发言。咸甜豆腐脑哪个好吃,这种经验性的话题,人人都可以说说。但转基因食品安全吗?高压变电辐射可控吗?这些问题得问生物学专家、电力专家,而不是用自己在这些领域里知道的那少得可怜的信息(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去打嘴炮。
当然有人质疑权威:“科学家的研究就一定可靠吗?史学家都能确保还原历史真相吗?我没有发表看法的权利吗?”可是,如果科学家做那么多实验都无法认知的现象,史学家读那么多档案都无法梳理清楚的过往,我们作为外行,岂不是更无知?你也当然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但看法和知识是两码事,有“有知的看法”,也有“无知的看法”,跨界发言之前得掂量掂量自己,千万不要“心比天高,知比纸薄”。
之所以不建议跨界发言,是因为大概率会献丑。很简单的经验,每当我们听闻外行谈论到自己行业的知识时——比如电厂员工看到舆论对“电站辐射”忧心忡忡时,内科医生看到公众对“阿胶补血”趋之若鹜时——会觉得智商捉急。但一回头,当那个电厂员工和内科医生去剖析英国脱欧时,他们忽而又意识不到自己很可能也会智商捉急了。
有句挺鸡汤的话叫做:“你的问题在于读得太少而想得太多。”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读得多,我们作为凡夫俗子,读得少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但明明自己读得少还非要想太多,为难自己去弹射臧否,这又是何苦呢?基础题都不太会做,却非要去攻附加题,就算你答了一百道最后不也是0分吗?
当然,如果实在忍不住指点江山的欲望,觉得自己非思出其位不可,那也不妨先去查查学界研究、听听专家见解,再说话不迟,这也根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毕竟,如果自己不能提供真知灼见,那就不妨“拾人牙慧”,总比自己贡献出一地鸡毛要好。
说到底,社交网络的意义,只是将行业专家的意见便捷地传递给公众,而决不是把公众变成行业专家。术有专攻,我们要做的是传递自己最了解的信息,以及接收别人最了解的信息。舆论场不妨向科研界学习——别人说得更好,那我就引用,只有确定自己能提供增量知识时,才去写一点东西。
美国科学院院士、社会学研究专家谢宇教授曾说:“许多记者和学生问我对很多社会现象的看法,他们很奇怪我会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是没有,而是我不愿意公开我自己的看法。对于我没有做过研究的社会现象,我的看法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看法,没有学术价值,没有公开的必要。”
对于大部分话题,我们没有做过研究,发言也就没有价值,未必要对各种专业问题都去激扬文字,不妨克制自己要当“聪明人”的冲动,安静地做一个知识接收者、转述者。按蒋廷黻的说法,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可发言的,什么是不可发言的,那我们就还没有从“前现代人”进化成“现代人”。
(作者为清华大学研一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