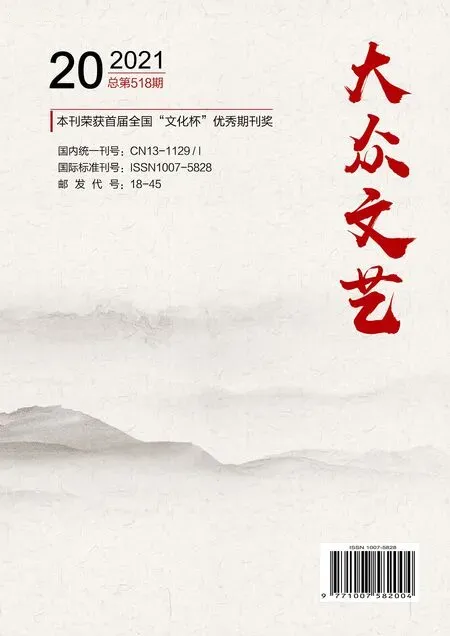论波伏娃小说《女客》中女性的“他者”地位
罗曼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510420)
论波伏娃小说《女客》中女性的“他者”地位
罗曼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510420)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20世纪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其在《第二性》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女性的“他者”处境理论。《女客》(又译《女宾》)是波伏娃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三位主人公充满实验性质的“三人行”爱情乌托邦模式,显露出女性的“他者”地位与男性的“自我”地位。本文试图运用波伏娃的“他者”女性批评理论来解读波伏娃《女客》中的男女关系和两性地位,并探究爱情乌托邦失败的根源。
波伏娃;女性主义;他者;女客;爱情乌托邦
法国当代女作家、存在主义文学家、女权运动的理论家、契约式爱情的发明者和社会活动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是二十世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其半自传体小说《女客》能充分体现女性在爱情关系中的“他者”的地位和被动的处境。女作家弗朗索瓦兹与剧作家兼导演皮埃尔交往八年,两人保持密切的情侣关系。不久,三人互生情愫,弗朗索瓦兹大胆地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恋爱模式——爱情乌托邦。随着交往的深入,格扎维埃尔愈发叛逆、疯狂、歇斯底里,皮埃尔疯狂的占有欲日益明显,弗朗索瓦兹则默默地吞噬着对二人的嫉妒,最终这一恋爱奇迹以悲剧告终。“三人行”爱情乌托邦这种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世间常见的男女纠葛,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具有探索价值的关系。然而,长期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会滋生不断的负面意识,即矛盾、不定、犹豫和断裂。女性的不自由、疯狂和受挫都反映出“他者”地位对女性意识的伤害,以警醒现代女性在男女关系中,需要保持平等的意识、自由的个性和争取应有话语权的姿态。
一、弗朗索瓦兹从“自我”地位沦为“他者”
故事最开始,弗朗索瓦兹的出场多么令人眼前一亮,为之振奋。她走在空洞的剧场里,暗淡的一切随即为之亮起了璀璨光芒,“要不是她来到这儿,这里的尘埃气味、半明半暗的光线、透着忧伤的寂静,这一切对任何人都不存在,全然不存在。而现在,她来到这里,地毯的红光如同一盏羞怯的长明灯穿透黑暗。她拥有这种权力:她的存在能使事物摆脱无意识状态,她赋予它们色彩和气味。”她的存在是那样的昂扬与饱满,比世上任何一人的存在都更加强大,她拥有着无比坚实的自我和超凡的主观意识。“这样的个体感觉良好,自信于力量的支持与安全的支撑,直到自认为不可摧毁,甚至自视不朽。”弗朗索瓦兹的自恋是一种无意识的心态,这有赖于生活中的物质与精神来支撑。但是,在三人行的关系之中,面对皮埃尔这位终身伴侣与格扎维埃尔日渐情深的现状,她意识的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被动之感,如同弗洛伊德所提及的“阉割情结”概念,波伏娃说道:“小女孩没有第二自我,没有被异化在一个物体中,所以她不可能挽回她的完整性。这使得她把全部自我变成一个客体,把自己树为他者。”弗朗索瓦兹在这段关系中从光鲜明亮的“自我”地位沦为被他人牵扯着的“他者”地位。
二、格扎维埃尔尝试摆脱“他者”地位
在事业和爱情双丰收的环境下,弗朗索瓦兹得以无所畏惧地、热情满怀地享受在优雅而浪漫的生活当中,与皮埃尔共同构筑着相互平等的二元情感世界,直至年轻少女格扎维埃尔的介入。最初格扎维埃尔的存在是微小且具依附性的,看见这个脆弱而美丽的小生命,仍然处于“自我”地位的弗朗索瓦兹深信她自有足够的能力控制她,然而,作为一个敏感的女性,弗朗索瓦兹觉察到她天真面目的背后深藏着的是女性特有的嫉妒心和占有欲,她开始在暗处延伸魔爪。她渐渐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女人存在于皮埃尔面前,在皮埃尔身上得到的是一种“他者”的认同,正如《第二性》中提到:“他者意识是一种依附意识,对于他来说,本质的现实就是那种动物型的生命;就是说,是另一种存在所给予的一种生存模式。”与皮埃尔的戏剧学习更是让她感受到自己有事可做,存在的价值日益明显,她在与皮埃尔的相处中得到的不仅是爱情,更是女人身份的获得,她沉浸在“他者”所带给她的“好处”之中而不能自拔,衍生而来的负面女性意识更是渐渐侵蚀着她的内心。
三、皮埃尔自始至终的“自我”地位
像所有在长跑爱情关系中逐渐懒惰的男性一样,皮埃尔无法拒绝这位年轻少女的天然和热情,与其相处时所获得的富有活力的新鲜感是和弗朗索瓦兹相爱时无法得到的别样感受,皮埃尔已经爱上了她,他无法克制地赞赏她起她的敏感与细腻,甚至她的自私。在皮埃尔的意识中,格扎维埃尔对于他而言是一个新鲜的玩物,“对于男人,她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殖者,一个性爱对象,一个他用以探索他自己的他者。”可是,当弗朗索瓦兹说这决定是三人追求自由的选择时,真正获得自由的只有皮埃尔一人,他可以自由地爱恋着两个不同的女性,不需要负上任何法律责任,他愈是感受到她们之间暗中的争夺和妒忌,他就愈发感到自身拥有优越感甚至征服欲。原本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的二人平衡关系转化为三角关系。而皮埃尔必然处在三角关系中的上层位置,牢固地霸占着“自我”意识的巅峰,犹如三角形的顶尖之处,与下层位置中的弗朗索瓦兹和格扎维埃尔构成了不平等关系,就如王安忆剖析道:“在这三人组里,皮埃尔其实一直是个中心,这个中心是有性和性别所决定的。事情并非弗朗索瓦兹所向往的那么平等。”弗朗索瓦兹和格扎维埃尔都围绕着皮埃尔形成了“他者”的地位,这种不平等关系与最初乌托邦平等、自由的构想是完全相悖了,因此,这种爱情乌托邦的模式在现实中仍是难以长久进行。
四、结语:对于女性“他者”处境的反思
在整个过程中,弗朗索瓦兹“一半是受害者,一半却是同谋”,她亲手将自己送进了人性的炼狱,在炼狱中接受着人性的捶打,在“自我”与“他者”的周旋之中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但是通过弗朗索瓦丝(或者说波伏娃)这样一位带有女性主义革命性意义的人物、一位代表新锐知识分子和时代先锋的失败探索,发现了女性在爱情关系中所处的“他者”地位,也警惕着现实中的女性们,不需要被性别、婚姻和家庭约束着自己的个人意志,不需要为了迎合他人而扮演相应的角色,每个女性都应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追求与其他个体平等的生活和宽松自由的两性关系。女人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大胆地追逐事业上的成就,大胆地选择生活的方式;同样的,男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装扮自己,而不是被既定的思维所束缚。只有在一种没有特定气质限制的社会中,不管是男人或者女人,所有人作为“人”的潜质才会被全部挖掘出来,社会才能朝着更健康、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周以光译.女客[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美]厄内斯特·贝克尔著,林和生译.死亡否认[M].人民出版社,2015.
[4]王安忆.男女关系的乌托邦[J].读书,1997(7).
罗曼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文艺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