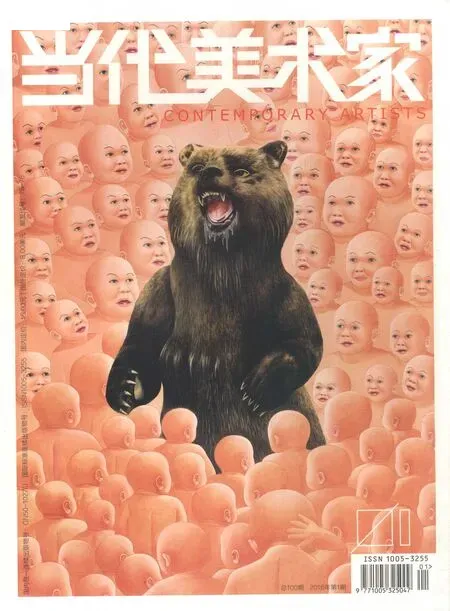前卫艺术的背后
——谈谈《大众文化中的现代艺术》这本书
吴毅强
前卫艺术的背后
——谈谈《大众文化中的现代艺术》这本书
吴毅强

1 迈克尔·阿舍 无标题装置 1981
摘要:一般认为,强调先锋、叛逆、个性和创造力的前卫艺术与大众文化来自于不同世界,前者稀有、短缺、珍贵,而后者则大众、常见、庸俗、普通。前卫艺术往往和精英主义、经典和原创以及天才等概念紧密相联,而大众文化则是民主社会、商业和消费社会的象征。但托马斯·克洛却从根本上质疑了这一二元对立,提出大众文化与前卫艺术的不可分割性,认为大众文化往往是前在和决定性的,并不是与前卫艺术完全割裂的领域。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当代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前卫,大众,现代主义,文化工业
前段时间,我在电视上看了一档流行音乐节目,说的是,青年歌手谭维维邀请来自陕西的五位民间老艺人,与自己同台演绎“华阴老腔”,一起合作完成了一首原创民俗摇滚歌曲《给你一点颜色》,整个歌曲将传统与当代、乡村与城市、大众与前卫进行了颇具创造性的融合,场面极为震撼,用崔健的话说:把我给看傻了!
然后,我就不自觉地想到了最近翻译完的这本书:《大众文化中的现代艺术》。
摇滚乐吸收民间传统音乐元素,转而成就了最为前卫和先锋的当代摇滚。这一现象似乎回应了《大众文化中的现代艺术》提出来的问题:前卫艺术和大众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严格的界限分明的等级制?还是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下面,我就谈谈这本书以及它所阐述的对于前卫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
《大众文化中的现代艺术》一书,是美国艺术史家托马斯·克洛(Thomas. E. Crow)1996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由我和陶铮通力合作翻译而成。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们在两种伟大的语言之间来回游弋匍匐,其中的艰苦曲折、快慰欢欣早已幻化成烟,融入了时间和生命,这里毋需赘言。但是,关于作者克洛以及这本书,我们却还是愿意花些笔墨作一番介绍,抛砖引玉,以飨诸位。
托马斯·克洛(Thomas. E. Crow 1948—)是美国著名艺术史家和批评家,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艺术史和考古学教授。2007年9月,被聘为纽约大学艺术学院现代艺术罗莎莉·索罗(Rosalie Solow)讲席教授。同时,他也是《艺术论坛》(Artforum)的特邀编辑,2015年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梅隆讲座(A. W. Mellon Lectures)主讲人。

2 罗斯·布莱克纳 大海 1984

3 西尔·比顿在波洛克的展览上为美国《时尚》杂志拍摄的测试照 1951
克洛以论述艺术在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的写作而闻名。他的研究方法与其导师著名艺术史家 T·J·克拉克(T. J. Clark)相似,都采用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和路径。克洛成长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晚期现代主义日渐式微,以风格语言和“知觉主义”(布列逊语)为特征的传统艺术史观日趋遭受质疑,而“新艺术史”观日益兴起,所以,作为美国“新艺术史”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克洛并没有遵循其前辈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迈克尔·弗雷德等形式主义者的现代主义精英立场(哈尔·福斯特用“纵轴”一词来描述他们试图维护艺术作品优秀的品质和历史的评判标准,以期获得某种历史的延续性),而是更多的从艺术作品的历史社会语境和社会接受情形,来研究艺术及相关问题(哈尔·福斯特用“横轴”一词来描述新前卫艺术试图扩大艺术的能力范围,也就是发展了艺术的横向的、社会的维度)。

1 杰夫沃尔 不 1983年
克洛在早期的的博士论文《路易斯·大卫1785年的〈贺拉斯兄弟之誓〉:法国绘画和前革命激进主义》(Jacques-Louis David's Oath of the Horatii : painting and pre-revolutionary radicalism in France)中就显露出了其对艺术与社会领域关系的关注。这篇论文重点研究大卫绘画《贺拉斯兄弟之誓》的社会接受情况,很多艺术史家把这幅画看作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一幅动员性政治作品,但克洛对此却持有不同意见。他对研究主题的理解和方法往往异于常人,而且非常执着。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常常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很大麻烦,当然也使他的研究成果至今饱受争议。
眼下这本艺术史论集,汇集了托马斯·克洛11篇重要的艺术批评论文,范围涉及前卫与庸俗、艺术与市场、摄影、特定场域艺术、视觉文化与概念艺术等诸多课题和领域。比如,他考察了19世纪巴黎大众文化中的马奈,对纽约画派中那些与媚俗商业杂志关系密切的画家做了尖锐的揭示,考察了波普艺术、概念艺术及其它现代艺术运动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质疑了一直以来被普遍认可的现代艺术与大众世界的对抗关系。当然,在这多个主题之中,全书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依然非常明朗,那就是:前卫艺术一定就持有与大众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吗?前卫艺术家们总是在象征意义上成为普通大众的敌人吗?
这些问题在当今艺术界非常盛行,尤其是近些年以来,当精英主义、经典杰作、天才原创等等概念遭受全方面质疑之时尤为如此。在这本极富启发力的书中,这位杰出的艺术史家向我们展示了高级艺术与现代大众文化之间强有力的联系。克洛认为,两者之间互相依赖、不可分割,前卫艺术和大众文化都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格林伯格所区分的那么绝对和严格,甚至,前卫艺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大众文化。他举了很多案例,从19世纪中期的巴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概念艺术的最新复苏,无论是印象派绘画中那些休闲娱乐场所、酒吧舞厅,还是20世纪60年代后波普艺术、大众摄影、广告进入前卫艺术领域;无论是绘画的主题题材,还是当代艺术的产生、传播和接受方式,种种案例都表明了托马斯·克洛持有的一个观念:大众文化从一开始便决定了高级艺术、前卫艺术的产生方式,大众文化是前在的和决定性的,而高级前卫艺术只是它的一个结果。他清晰而雄辩地论证了这一点。
托马斯·克洛的论证过程值得一提,他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特点非常鲜明的插曲来进行的。在前卫和大众之间,艺术家们穿梭自如。比如,杰克逊·波洛克是被他的第一个赞助人拉入了时尚圈,使得他的满幅泼溅画经常成为各种时装秀的背景板;安迪·沃霍尔60年代那些意图明确的作品,使得他一直葆有一种小镇情绪,他经常搜集挪用一些大众新闻事件图片来制造一些话题;斯图尔特文(Sturtevant),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女艺术家,她将波普艺术的策略反过来对付波普艺术家自身,而这一策略在20年后成为了新一代艺术家们习以为常的创作手段;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在他的复杂创作中使用了一些业余爱好者们的摄影照片;戈登·玛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去一些被丢弃的建筑中寻找雕塑的原材料;罗丝·布莱克纳(Ross Bleckner)用一些腐朽破败的维多利亚时代美国低俗作品来重新塑造自己80年代以来的绘画;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Christopher Williams)则用旅游产业的心理地图重新制作成高级概念艺术。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前卫艺术家们与周围大众文化之间的亲密关系。
在这些案例和插曲背后,托马斯·克洛对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详尽地探讨,尤其是在全书的第一篇论文《视觉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Modernism and Mass Culture in the Visual Arts”)中,他几乎将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他指出: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从一开始便具有天然的亲密联系,作为现代艺术承担者的前卫艺术不断在高雅文化和大众亚文化之间进行渗透,打破等级之间的平衡,从而形成与文化工业合谋下的现代艺术。这样一种现代艺术既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同时又表现出不可避免地妥协性。毫无疑问,这一论点为我们重新理解现代主义艺术提供了极富价值的视角。
在克洛看来,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图像符号等)之间存有彼此的身份认同关系。比如,马奈的《奥林匹亚》(Olympia),实际上是用一种当代的廉价符号,扁平化地再现了当年提香所画的那副《乌尔比诺的维纳斯》(Venus of Urbino)中所蕴含的色情意味;莫奈、德加们在娱乐休闲场所流连忘返,才有了那些赤裸裸地刺激视网膜的印象派绘画;马拉美、西涅克等人曾提出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之间发生的关系,只是一种策略性的临时战略,也就是说,现代主义画家们的确是从一些习以为常的大众材料中寻求描绘主题,但这只能算是他们工作的一个脚手架,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彻底的形式自主,这些大众材料最终因为目标的完成而遭到放弃。所以,本质上还依然是一种等级论。克洛把他们的主张同20世纪格林伯格关于前卫与庸俗的观念联系起来,这些观念都倾向于认为,在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是存在有严格的界限和等级的,这也是前卫艺术和庸俗艺术的根本区别。但克洛似乎并不赞成两者之间的对抗关系。
某种程度上来说,克洛更愿意站在夏皮罗的基本立场,来看待前卫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夏皮罗认为,现代艺术与消费社会具有某种共谋性,前卫艺术家们的审美习惯与他们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形成的习惯和欲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发现,这些习惯和欲望经常来自于社会上一些离经背道的群体,他们在一些公共空间里扮演着搅局者的角色,与既定的政治和文化规则形成一种对抗。他们所采用的一些符号对于前卫艺术感受力的形成至关重要。
前卫艺术与这种“顽固的亚文化群体”之间有某种同质性。二者都是从边缘化中开始的,作为批判性艺术的前卫艺术在整个广阔的社会战线中都是反抗性的,这种反抗性并非退回到审美自律的飞地,而是与艺术之外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克洛认为,前卫艺术和亚文化在一个共享的公共空间里表达对社会的对抗和不满,前卫艺术从亚文化中提取出了独特的前卫的视觉图像符号和识别机制(克拉克的艺术通过对惯例视觉机制的反抗和呼应来达致对社会的影响)。
另一个克洛提出的重要观点是,前卫艺术是文化工业的一个研发部门。他认为,前卫可以被看作是,高雅和低俗之间的一个中间代理人,同时又是文化工业用来研究开发的职能部门。通过从边缘大众文化中对日常图像及符号进行精挑细选的挪用,高级艺术家们从日益管理化和理性化的社会中寻找出一块保留有生动鲜活生活的社会实践区域。他们将其进行提炼和包装,以满足精英阶层和具有自觉意识的观众需要。大众文化通过制造差异和无序来开启抵抗和规避,试图反抗和讥讽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但文化工业则进一步通过弥合分歧、削除自主性来遏制和收编,试图控制商品的文化意义来配合金融系统的运转。而前卫艺术正是这二者之间进行转化的最佳通道。
克洛把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放在发生学上的同一层面来考察,认为二者是共生关系而非竞争关系。这对于打破我们关于前卫与庸俗的固有僵硬划分具有重大意义,他卓有成效地在前卫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来回爬梳,分析了两者产生关系的种种前提和路径,破除了关于两者之间简单对抗关系的种种误解,为我们重新理解现代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便到了今天,当我们在思考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当代艺术与文化工业的关系等等重大课题时,克洛的研究依然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
Behind the Avant-garde
Thoughts on Modernism and Mass Culture in the Common Culture
Wu Yiqiang
Key words:Avant-garde, Mass, Modernism, Culture industry
Abstract:Generally speaking, the avant-garde art, which emphasizes pioneer, rebellion, individuality and creativity,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culture. The former is rare, shortage and precious, while the latter is public,common, vulgar and ordinary. The avant-garde art is often closely assosiated with concepts of elitism, classicism, originality and genius. And common culture is symbol of the democratic society, business and consumer society. But Thomas. E. Crow questioned the binary opposition fundamentally, by arguing the indivisibility of the common culture and the avant-garde art. He believed that the common culture is in decisive territory, can not be completely separated from the avant-garde art. Thi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cognition the contemporary 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