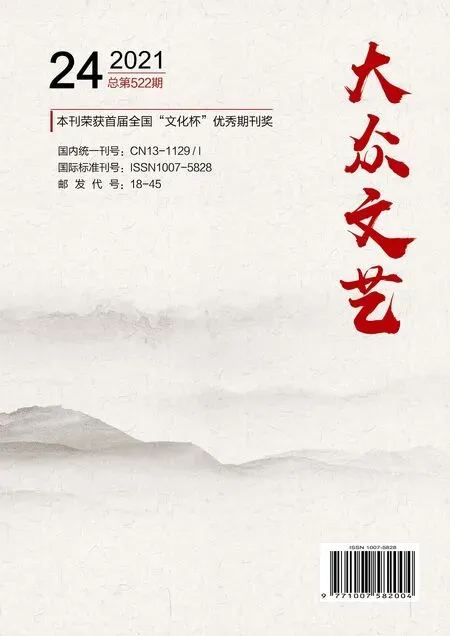中岛敦小说中的梦境与逃离
于凤艳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750000)
中岛敦小说中的梦境与逃离
于凤艳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750000)
论文以中岛敦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梦境入手,分析中岛敦小说中的梦境隐喻,并阐释其作品叙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共同的逃离模式。不论是英雄才子的逃离,还是小人物的逃离,个人与环境之间构成的激烈冲突通过逃离这一模式被不断强化,梦境成为一种隐喻性的表达,喻示着人物在他者的挤压下逐渐感觉到自我的丧失,并由此分析中岛敦小说对存在的思考与怀疑主义思想。
中岛敦 梦境 逃离 他者
中岛敦是日本大正时期重要的小说家,其作品擅长描写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中个体的孤独和绝望。在短短的创作生涯中,从《山月记》到《幸福》,逃离是其作品共同的主题。不论是英雄才子的逃离,还是小人物的逃离,个人与环境构成的激烈冲突通过这一模式被不断强化。在一系列的逃离故事中,梦境的隐喻表达,喻示了人物在他者的挤压下逐渐感觉到自我的丧失,急欲逃离。
《山月记》是中岛敦最早受到文学界关注的作品,发表于昭和17年的《文学界》。小说从唐传奇取材,但故事强调的并非是“成虎”这一离奇事件本身,而是李徵成虎的内在原因,也就是他自己对友人所言的“怯懦的自尊心与自大的羞耻心。”1在繁华鼎盛的开元全盛世,李征以他的才华在诗人辈出的时代却无法为自己博一份功名,竟然沦落到沉沦下僚的地步。于是,在愤懑的痛苦中奔逃而出,于旷野中成虎。中岛敦对李徵出逃一部分的叙述颇有意味,那是李征的自我叙述。
距今大约一年以前,我羁旅在外,夜晚宿在汝水河畔。一觉醒来,忽然听到门外有谁在叫自己的名字。应声出外看时,那声音在黑暗中不停召唤着自己。不知不觉,自己追着那声音跑了起来……等我意识到时,小臂和肘弯那里似乎都生出了绒毛。到天色明亮一些后,我在山间的溪流边临水自照,看到自己已经变成了老虎。2
这段描述,与其说是惊变,不如说是释梦。这分明就是一场恶梦,与卡夫卡《变形记》的开篇叙述何其相似。与卡夫卡的虫变不同,李征的压抑以放大兽性的竞争而变形,成为一个掠食者。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却无从反抗的命运。夜半醒来,循声成虎,那个遥远而又切近的声音是谁?还是就是内心压抑的爆发?那个成虎的梦,也许不知道已经在他的梦境中出现过多少次了。所谓无法自制的冲动,正是其内在的需求。李征以成虎的方式,逃离了他前半生所秉持的君子正道,向这个他所不满意的世界发起了兽性的屠杀。而这个似梦似幻的成虎之夜,正是其逃离的直观表现。他少年有才,不愿与鸡鸣狗盗,营营苟苟之人为伍,却被人看作恃才傲物,遭到孤立。但同时又对自己缺乏完全的信心,害怕自己并不具备自己所期望的才能。正因此,他才在成虎前最后的意识状态中要朋友为他保存诗稿,作为自己存在和才能的证明。
但自我并非是先天存在的东西。正是他者的出现,才有了自我的意义。任何个体的人都是在与他者达成的妥协中才求得生的平衡,这是自我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自我与他者的不断角力和不断妥协之中,自我才被赋予了意义的轮廓,获得了自我的尊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他者,也就没有了自我的存在,真正的万虑皆空的前提正是抽空了“我”与“他”之间的这种意义。
自我与世界的通路人为地被切断,使人物处于孤绝境地,是中岛敦小说惯用的叙述方法。《李陵》中的三个重要人物,李陵被构陷,苏武被囚禁,司马迁被阉割,这种隔绝都是被迫的,在他者恶竟的构陷中不得不活在云水中,活在孤独中,活在不完整的痛苦中。对李陵被俘的描写不像一场战争,倒更像一个恶梦。
早升的月亮已经落下……
李陵立马计算着摆脱敌人追击,在夜色中微白的平沙上疾驰而去的部下的数目。确信已超过百人后,他重又回到了峡谷入口处的修罗场。他身受数创,自己的血和所有敌人的血将戎衣浸得又湿又重;和他并肩作战的韩延年已经战死了。既失部下,且失全军,已无面目再见天子。他手握长戟,再次冲进了乱军中。在几乎难辨敌友的暗夜混战中,李陵的坐骑似乎中了流矢,呼的一下向前栽去。几乎与此同时,正挥戈砍向面前敌人的李陵在后脑上挨了重重一击,顿时失去了意识。3
挥舞的武器,战死的尸骸,血腥沉重的甲衣,在无声暗夜中的撕杀被凝缩成一幅画。这不仅是日本文学惯有的以形代声的方法,更暗示了李陵人生更大悲剧的开始,一场人生恶梦的开始。羁留塞外却无法自明心境,又在奸人的构陷和命运的误会中永远地失去了回到汉地的可能性。老母被杀,全族被戮,他在愤怒中接纳了匈奴的招降,然而当他面对着那个与恶意境遇始终战斗的苏武时,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小”。他在意世俗的评价,想击杀单于又怕不能带头颅归汉就得不到大家的认可;他为自己和家族不能被重用,没有得到理应的封赏就愤恨不已。这些外在的评价已经让他深陷在他人的眼光中而缺乏单纯热烈的自我意识。降胡与其说是反抗,不如说是逃离。但降胡并不能拯救他,他也并没有因此重塑自我。逃离自己的汉臣身份,他已经不再是他。他虽着胡裘,却在染着部下鲜血埋着他们白骨的黄沙中,既不能为敌所用,又无法回归故国,只能以一种近乎失语的状态存在,终于成为历史中被堙没的一粒沙。
小说中,李陵受单于之托去北海劝降苏武时,叙述同样极具画面感。
他们沿着姑且水域向北漂溯,从姑且河与郅居河的交汇处,再沿着西北穿越森林地带,沿着处处残留着积雪的河岸进发数日,李陵一行人总算是终于看到了北海湛蓝的水面出现了森林与旷野的对面了。在土著人向导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一间可怜的小木屋里。4
苏武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孤立于此岸世界的存在,甚至是与此岸世界切断了联系。它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但丁笔下那座孤处在大海深处的炼狱山,而住在这座炼狱山上的苏武超然物外,他的无欲无念无恨的状态完全不类似于人类的状态。中岛敦通过李陵和苏武的对立向我们揭示了自我的受难和失败,在中岛看来,在芸芸众生的生活中,永远也不可能去贯彻绝对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彻底的自我,也只有在与此岸相对的彼岸世界才会实现,而那又是一个死后的世界。当苏武听闻武帝已死的噩耗而号哭泣血之时,我们终于明白,原来苏武的所谓完整自我是将自我完整地植入到对武帝的崇拜中。武帝就是苏武存在的意义。换句话说,只有自我解体之后才能实现自我。
和苏武相比,司马迁也是一个没有完整自我的形象。作为一个受到腐刑的不完整的男性,他的自我是以写史的方式被转嫁出来的。和李陵与苏武一样,司马迁也彻底失语了。这种沉默与其说是他对恶意世界的对抗,还不如说是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逃离这个带给他屈辱却无法舍弃的世界。他的生,正是为了获得逃离的自由。
生的快乐彻底失去之后,唯有表现的快乐还可以残留下来。即便如此,他那彻底的沉默并没有被打破,风貌中的凄厉也没有丝毫缓和。在写稿的时候,每当不得不写下宦者或者阉奴之类字眼时,他就会不由得发出呻吟。独自在居室中,或者夜晚躺在床上时,屈辱的感情时而在无意中萌发。如同被烧红的烙铁炙烤一样,一种炙热的疼痛片刻间传遍全身。这时他会大叫一声跳起,一面呻吟,一面快步徘徊,然后再咬紧牙关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5
作为身负重写历史重任的史官后代,他不能死,作为一个身受奇耻大辱的男人,他却不想生。在生死的痛苦诀择中,他找到了延续自我的方法,那就是赋予他笔下人物本该属于他的情感。对自我的标榜是近代以来思想解放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但在中岛敦看来,彻底的自我实现根本无路可寻。李陵,苏武和司马迁都曾经强烈地体现了自我意识,但他们的自我在现世的受难中难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对死亡这一隐喻性的意象,中岛敦以他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向我们昭示,彻底的自我实现只存在于自我解体之后。那才可以不受侵蚀,不被割裂地独立存在下去。
审父是成长小说中惯常的话题。孩子们企图通过对父亲的审判来找到自我存在的依据,这也是中岛大多数小说的视角。但《盈虚》颠倒了这个视角,从父亲的眼光出发去打量孩子,以期对血源关系甚至存在进行新的思考。对于父亲而言,儿子是自己的化身。他们虽然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立人格,但由于种种原因和血脉的牵连,父亲的影响对孩子人格的塑造无法回避,父亲正是通过对儿子这一分身的审视来完成对自我存在的反观。在落难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相依为命,寄人篱下。父亲在憎恨和愤慨中对冷落了自己的王公大臣,拒不接纳自己的蒯辄,造成自己流亡的南子充满了仇恨,这种仇恨让他越来越刻薄。而儿子蒯疾身上也逐渐透露出了与年龄不相符的可怕的刻薄。长年的屈辱体验在父子两个人的身上表现出了同样的烙印。父亲的刻薄教会了儿子,把儿子塑造成现在的模样。从一开始流亡,公子疾就与母亲在他众叛亲离时投奔他,现在却反过来却要加害他。击杀浑良夫,与石圃一起将自己逼上绝路,这只是外在的表相,事实上,正是父亲在十几年的仇恨中逐渐塑造了儿子的个性,然后又被这种个性所伤。
《盈虚》中的梦境出现在庄公剻聩发现太子疾阴谋篡位之后。这个梦充满了隐喻性。
庄公冒出一身冷汗,从梦里醒了过来。整个心情十分不快。为了驱散不快,他起到露台上。正是晚升的月亮从田野尽头升起的时候。近乎赤贫铜色的、混浊的红月亮。6
浑良夫和伯姬让剻聩终于会重回故国成为卫侯。但在剻疾步步进逼并最终击杀浑良夫时,剻聩却不发一声,只是看着太子罗织罪名,终于在朝堂之上践踏了自己当初的诺言。这不仅是对父亲权力的挑战,也是父子二人在主从地位上的一场心理较量。中岛刻意强调了那个暗红色月亮的神秘梦境,就是他对自己人生恶运的预知。正是这样的预知让他深感绝望和命运的恶意。以这个古老的弑父故事,中岛敦不仅颠覆了代代相承的血脉的正当性,也再一次质问了人类存在根据的确定性。
《幸福》是中岛敦南洋时期的作品。小说进一步发展了他对世界的悲剧性思考。主人和仆人的梦境,以互文式的方法表达了他的思考:我们对幸福的认知来自于我们对世界的评价,也来自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态度。尽管天天锦衣玉食,主人在梦境中的苦难竟让他没有一天感觉到幸福,相反,受尽欺压的仆人则通过梦境重塑自信,构成了充盈的自我。外在世界的评价其实是我们的自我屈从于环境的表现,只有自我内心的充盈是抵御这种恶意压迫的唯一方法。相较于《山月记》中的李徵,仆人的幸福简单而质朴。他抱定内在的绝对自我,确定了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与他相比,主人内心的怀疑,恐惧彻底摧毁了他。他夜夜梦到自己丧失了优越的地位,受人奴役,从而在痛苦和焦虑中无路可走。幸福与不幸只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但相较于现实,梦境却似乎更真实而产生决定性的后果,以致于颠覆了现实。才使得别人眼中的幸福加重了不为人知的痛苦。
《弟子》中的子路是一个坚定的行动主义者,他坚信所有的道必须通过身体力行来实现。这正是他与其老师孔子的差异所在。孔子强调圆融中庸,而在子路看来,这正是老师无法实践自己理想的原因。中国文学中那个似乎有些莽撞的子路,被中岛敦赋予了更悲壮的气质,对老圣人的思想加以实践。当孔悝被胁迫,众人皆为苟活恭身听命之时,只有子路冲破封锁救主。正如他曾经质问老师的:“在这个世上,最要紧的是计较自身的安危,而不是舍生取义吗?一个人出处进退的合适不合适,比天下苍生的安危还重要吗?”7甚至在他临难之时,也要正冠而死。也正因此,当老圣人孔子听说子路的死讯时,才“伫立着瞑目良久,须臾潸然泪下。”8。任何时候,若没有为理想殒身不恤者,那么理想就终究只是空谈。这也是中岛敦将其作品命名为《弟子》的原因之所在。
作为中岛敦行动主义的尝试,《弟子》是他试图打破悲观意识而进入积极人生可能性的一次自我扣问,子路和孔子的关系印证了这种思考:纯粹人格如何进行自我提升。孔子是人格神,是偶像,理想,但同时也是对象,是参照物,是他者。子路在追随中发现了他的“小”,而中岛敦也在讲述中发现了行动主义者最终的悲剧。自我在与世界的对抗中越趋向于纯粹理想,则其在现实中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这是纯粹理想与庸俗现实的落差,是自我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必须承受的还击,更是理想主义的必然结局。故事的结尾,子路死后,老圣人再也不吃腌肉,不能不说是对子路纯粹人格的赞美和祭奠。
中岛敦家学渊源,对汉文化的研究和大正时期一般的作家绝不可同日而语。其中岛敦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这种逃离模式,与童年的不幸生活和殖民地的青少年时期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倍感压抑的生存困境中他无法选择,也无从选择,从而形成了其悲观思想。同时,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大正时期的战争阴云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促使他反思传统文化。从扣问文字的偶然性开始,表现了对存在与虚无的关注。他认为文明的弊端在于用华丽文字装饰过的表相隐藏着巨大的欺骗性,而传统文化对人的意志所构成的约束使人丧失自然强健的内心,受缚于他人的眼光,成为不完整的人。这一点在其描写南洋生活的诸多篇章当中都有涉及。在中岛敦看来,真正的成功是要获得内在的充盈,而唯有从形式的追求中退出,净心简行,万虑皆空。然而抽离不易。在这个遍布意义的世界中,如何才能让自己不被意义所左右,中岛敦以主人公的逃离,昭示了自我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一个不愿被境遇所左右的知识分子,不能不说是对那个极度摧残人性和个性的时代弱的反抗。
注释:
1.(日)中岛敦.韩冰、孙志勇译.山月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7页
2.(日)中岛敦.韩冰、孙志勇译.山月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4页
3.(日)中岛敦.韩冰、孙志勇译.山月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08页
4.(日)中岛敦.韩冰、孙志勇译.山月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32页
5.(日)中岛敦.韩冰、孙志勇译.山月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21-122页
6. (日)中岛敦.韩冰、孙志勇译.山月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35页
7.(日)中岛敦.韩冰、孙志勇译.山月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87页
8.(日)中岛敦.韩冰、孙志勇译.山月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96页
于凤艳,文学硕士,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主要从事日本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