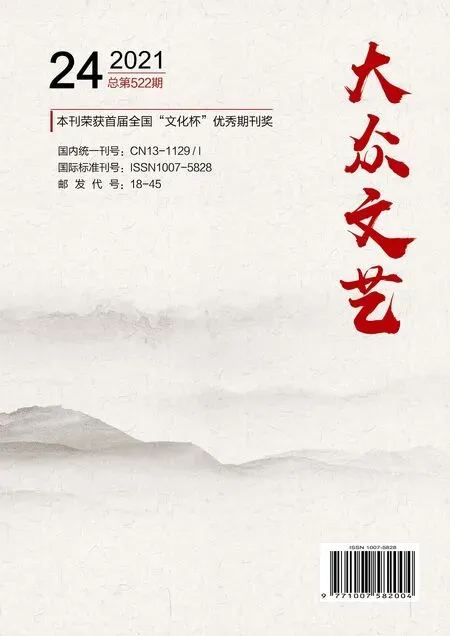从空间理论视角浅析《天堂》
李美玲 (青岛大学 外语学院 266071)
从空间理论视角浅析《天堂》
李美玲 (青岛大学 外语学院 266071)
美国著名非裔作家托尼·莫里森善于运用空间叙事的方法来传达非裔美国人寻求自我身份构建的强烈诉求,小说通过设置不断变化的空间位置,以体现非裔美国人当时居无定所的生活环境以及精神空乏的生存状态,并详述了非裔美国人不断尝试构建自己的“天堂”的故事。本文借助空间理论,旨在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三个方面来分析《天堂》的主题内容,从而探索出非裔美国人在寻找自我身份构建的方式。
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身份构建
一、引言
《天堂》是莫里森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部小说。小说的故事发生地点在美国南方黑人聚居区鲁比镇和女修道院。鲁比镇是黑人群体创建的一个充满“自由”的天堂,随着小镇上频频出现祸事,内部矛盾不断激化,他们便把罪恶的源头指向了修道院,修道院随后遭遇洗劫。作为非裔作家莫里森来说,空间一直是她关注的话题,小说中两个空间的位移,交融的发展过程阐释了两类人寻求自我身份的不同方式。
二、空间理论
20世纪中期以来,空间理论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在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出版,更是奠定了空间理论的基础,书中,列斐伏尔创造性地提出“空间是一种生产”的观点。这个空间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不同,不仅仅是空洞的物理概念,而是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空间。他认为,小说的空间可以分为物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三个方面。首先物理的层面是指位置不同,地域不同的地理空间;其次精神的层面是指小说人物由于事件的发生而在内心所产生的精神活动的思维空间,具有很强的主观意识性;最后社会的层面是指由人与人交流以及社会关系共同参与的社会生活空间。三者之中,列斐伏尔更重视社会空间的产生,他认为社会空间具有生产性,它不仅仅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的重复叠加,是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而再生的一种新的生活存在空间。
三、《天堂》的空间解读
1.地理空间
《天堂》中的地理空间主要表现为黑人聚居区——鲁比镇和距离此地十七英里的女修道院。从微观上看,重要故事情节都围绕在这两个空间展开。从宏观上看,还存在另外一个空间对比,即白人聚集区和黑人聚集区的对立空间。鲁比镇和女修道院仅隔十七英里,但是与白人聚集区却隔了九十多英里。由于白人和黑人之间地理位置的差异,他们少有交流,加之白人对黑人的固有的偏见,扭曲了鲁比镇上的黑人的心灵,酿成惨剧。
尽管19世纪60年代就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可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地域鸿沟仍然存在,黑人是被边缘化的角色,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鲁比镇的黑人祖先们只好被迫频频西迁,出现了空间的严重分化。斯图亚特在阿涅特婚礼的时候想到了早些年老爹外出的经历,一种支原体肺炎的疾病在黑文镇肆虐,老爹独自一人去六十五英里外的小城把医药品和生活物资运回黑文镇,途中迷了路,遇见了三个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被劝说不要去普拉·桑格尔城,因为那个城的城北边界处设立了一个牌子:黑人免进。这座小城公然表明了要与黑人划清界限的立场。他们不准许黑人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更不要说卖给黑人生活所需品。斯图亚特没有明白“‘黑人免进’在城的一头,十字架在城的另一头,中间是不受约束的魔鬼”。城中间的魔鬼实际上就是针对他们这样的黑人,时刻等待着吞噬他们。斯图亚特的妹妹鲁比在路途中生病,病情到了必须医治的地步时,却没有医院愿意医治这样的病人,白人和黑人的对立空间再次得到体现。摩根兄弟看着妹妹痛苦地闭上眼睛而无能为力,这就是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黑人们的记忆受到了创伤,心灵变得扭曲,他们开始试图建立一个纯黑人的生存空间,同样拒绝任何白人和浅肤色黑人进入,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地理空间,自此,这个纯黑人的空间就建立起来了,空间的外围是高高的城墙,把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开来。
《天堂》开场白是黑人男性先朝白人姑娘开了枪,原本女修道院是和谐的,教人向善的和平的圣洁的地理空间,而这里的女修道院演变成了罪恶和邪恶肆虐的空间,反讽了当时非裔美国人情感的麻木以及心灵的扭曲,同时也暗示了女修道院这个地理空间与鲁比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映射出修道院和鲁比镇中的人们寻求自我身份的不同方式。
2.社会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具有生产性。《天堂》通过对比两个地理空间,向我们展示了深层的社会空间差异。鲁比镇的存在是由于种族歧视而生,黑人在社会中没有话语权,被社会边缘化,无法融入白人的生活圈。所以鲁比的祖先选择了创建自己的文化圈。他们乐观的认为只要远离白人,便可以拥有话语权,重建家园。然而事与愿违,由于长期和白人生活在一起,他们的思维也早受其影响,“压迫”这个词早已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了,只要有了机会,他们必然也会压迫别人。另外,由于长期遭受来自白人社区的精神压迫,他们的心灵创伤早已形成,他们时刻准备着要报复那些白人。在这两个条件的促使下,原本要建立的“天堂”的梦想被一点点打破。鲁比镇上出现的新的权力之争,即纯黑黑人和浅色黑人的二元对立。
镇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黑人不允许与白人通婚,为了保持血统的纯黑性,甚至不能与浅肤色黑人通婚。罗杰·贝斯特被认为是第一个破坏了血统规矩的人,从此他只能做殡葬这样的活计;米奴斯被迫送回自己从弗吉尼亚带来的沙色头发的白肤色未婚妻;帕特丽莎嫁给比利·卡托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有着黑夜一般的皮肤。这一桩桩事情都显示了纯黑黑人和浅色黑人之间的对立,也印证了白人文化在黑人社区中的映射。
而女性,作为维持血统纯黑性的关键性人物,必须严格恪守本分,别接受来自小镇上每一个人的监督,不能做出有违小镇规则的事情来,否则将面临被人们排斥、驱逐的命运。马维斯忙着为丈夫买他最喜爱的牛肉时把自己的几个月大的孩子独自放在车里,最终孩子在车里窒息死亡,面对失去孩子的残酷现实,马维斯自悔不已,但她不仅没有得到家人的宽慰,反而受到了丈夫的奚落和指责,以及其他孩子的冷漠的眼神。一个冷漠无情,没有任何温暖和爱的社会空间压得马维斯喘不过气来,所以她选择逃离,来到了女修道院。在这里,康妮第一次问她的名字是什么,马维斯第一次感到了被人重视的感觉。在这个空间里的生活温暖阳光,没有压力,没有嘲笑,关系融洽,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中的生活来生活。
3.心理空间
空间理论既重视地理空间,又重视心理空间的参与,心理空间是指外部事件在人的内心里所形成的与真实世界相区别的构想空间。“文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展现个人的内心世界和个体的的潜意识活动,因此心理空间也就成为空间理论关注的对象。”(许克琪)在《天堂》中,故事结构虽以桔式结构呈现,但是其中女修道院中主人公的心理空间的情感发展方向大体是一致的,均经历了压抑、郁闷、闭锁、开放的过程。而鲁比镇男性权威人物的心理空间也经历着另外一种发展,即自信、压抑、暴怒、失落的过程。
不管是第一个来到女修道院的康瑟雷塔,还是陆续来到这里的玛维斯、西尼卡、帕拉斯等,她们在生活的一开始就被丑恶的社会所蹂躏:康瑟蕾塔在小小九岁的年纪就不得不屈从于脏脏的猥亵;玛维斯因为孩子的夭折而遭到周围所有人的质问和嘲讽;帕拉斯的喜欢的男友却与自己的母亲私通。经历不幸后,她们变得麻木,隐忍着不再与外界沟通,陷入了一种失语状态。她们的生活遭遇令人惋惜,然而她们并没有堕落下去,凭着自己的探索,在大家的帮助下,慢慢地苏醒了过来。女修道院就是她们互相取暖的疗伤之地,在这里,她们逐步与外界交流,慢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心灵逐步强大起来,这是一个逐步升华的过程。
鲁比镇男性权威的心理历程则截然不同。他们凭着自己的努力把一片蛮荒之地建成欣欣向荣的小镇。他们自豪于自己的成就,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远离白人社区,不允许混杂血统混入其中,抵制外来血统。其实质是故步自封。正如理查德·米斯纳牧师所言“分离我们,孤立我们——这始终是他们的武器。孤立杀害了几代人。那是没有前途的。”一时的繁荣并没有持续很久,几十年后,镇里频频发生诡异的事件:村子里的新生儿长成畸形,新娘在婚礼前一天突然跑掉等等。鲁比镇一时陷入恐慌的局面,摩根家族的权威受到质疑,他们选择逃避,暴力解决矛盾,最终以背叛的结局而宣告失败。他们自以为超越了白人,其实只是在模仿白人,模仿白人的文化,模仿白人的思维方式,最要命的是模仿了白人的意识形态。他们始终不能突破自己狭隘的思想,心理压力有增无减,其结局必然是走向消亡。
四、结语
莫里森描述了鲁比镇和女修道院截然不同的发展结局。从地理空间上看,鲁比镇的发展战胜了女修道院的发展,并将后者一举毁灭。但是从心理空间上看,最终的精神胜利属于女修道院的杰出女性。鲁比镇的绝对权威——摩根家族在一步一步的自我封闭中无限度放大仇恨,扭曲了心灵,没有成功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而女修道院的女性虽一度在缺少自由和爱的社会空间里迷失,但她们在这里相互支持,寻找自我,不仅治愈了自己,而且温暖了受到伤害的任何需要帮助的人,保持了自己民族的个性发展,最终将这种精神传播开来。至此,莫里森向我们阐释了黑人之间只有相互合作,以坦然、开放的心态认识自己,接受他人,才能完身份的认知与重建,共同构建自己的家园。
[1]马卫华. 论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及其文化表征[J].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14(9).
[2]史敏. 永不止步的身份追寻:<柏油孩子>的空间叙事解读[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8).
[3]托尼·莫里森. 天堂[M].胡允恒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7.
[4]王守仁,吴新云. 国家·社区·房子—莫里森小说<家>对美国黑人生存空间的想象[J]. 当代外国文学, 2013(1).
[5]武玉莲. 非裔美国文学中乌托邦的空间转向[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4).
[6]许克琪,马晶晶. 空间·身份·归宿—论托尼·莫里森小说《家》的空间叙事[J]. 当代外国文学, 2015(1).
李美玲(1991年—),女,汉族,山东莱芜人,硕士研究生在读,青岛大学,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