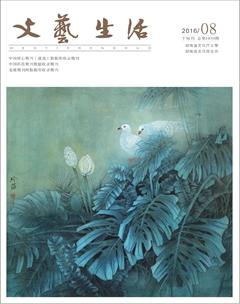异象灵见的可视性与不可视性
刘泓艺
摘 要:斯托伊奇塔于《西班牙艺术黄金时代的视觉经验》(Visionary Experience in the Golden Age of Spanish Art)中,主要选取16世纪下半期至17世纪末西班牙艺术发展黄金时代的绘画作品,试图通过检视绘画的早期语言,解读绘画机制背后的作用。着重论述且强调了“可视性与不可视性”“描绘非描绘性”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异象灵见;可视性;不可视性;清晰性;模糊性;注视;扫视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4-0062-02
16世纪下半期至17时期末这段时期,是西班牙绘画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是西班牙文艺复兴的极盛阶段。斯托伊奇塔在《西班牙艺术黄金时代的视觉经验》(Visionary Experience in the Golden Age of Spanish Art)一书中,引用了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艺术中反宗教改革的实例,此时期恰逢艺术的重要赞助者之一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兴起和衰落。通过对宗教信仰中想象的作用和地位的探讨,揭示了反宗教改革的精神性特征。着重论述了“可视性与不可视性”“描绘非描绘性”的重要性。
可视性,并非简单指可以看见什么,而是同时包含在某一时代背景下能够看到什么,什么是被遮蔽而无法看到的。不可视性,源于绘画的深层意旨或者画面投向我们的凝视的目光。《西班牙艺术黄金时代的视觉经验》中多次使用的“Vision“一词,原意为是”“视觉”或看见;托马斯·阿奎那对“Vision”提出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指视觉所看到的东西,第二层是通过想象力或理解力对其进行内在认知。在基督教传统中,往往被用来指上帝向先知显示的灵异现象,以及先知对此景象的见证。书中提到“耶稣变容”等事迹即“异象”,“Vision”中常同时包含两层意思,“异象”是客观的不可见维度,“”灵见“则指示先知见证“异象”的主观维度。①其中对基督升天和圣母升天的绘画及拉斐尔的圣塞西莉亚的论述,为可视与不可视的表现方式的构建和阐释角度提供了新的思考。
“叙述性的划分”一节中,以胡安·德·博古纳的《《耶稣在三个门徒前的变容》为例。画面上半部分基督的从容且肃穆,三位门徒被这一圣迹的光芒照耀,另外两人摆出朝拜的姿态。众人的目光皆向上方即基督投去,形成莫可名状的向上牵引的视觉张力,凸显了使徒们作为叙事环节的作用。于此,指示客观性角度的“异象”被直接呈现,从整体构图中不难发现在“异象”和”灵见”中,胡安·德·博古纳恰当地突出了后者的重要性。拉斐尔的《耶稣变容》显然比胡安·德·博古纳的《耶稣在三个门徒前的变容》表现出更鲜明的动势和戏剧性张力。拉斐尔以强化的方式,同时为画面上下两部分投去光线,上半部分基督的卓然光辉与下半部门徒和附体者们的晦暗动荡形成对比。下方众人的动态虽有一定的呼应,身形掩映,眼神彼此交汇,却无人注意到上方“异象”的发生。暗示着人群的隔绝和交流的不可能,以及人与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彻底断裂。②于观看者可见的“异象”,于门徒和附体者却是不可见的。以此观之,图象中异象灵见的可视与不可视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两个层次,一为画中人物的视角,二为观看者的视角。
“幻想性描述”一节中,弗朗西斯科·里瓦尔塔的《圣布鲁诺的愿景》和拉斐尔的《圣塞西莉亚》的比较,再一次呈现了不同的可视性与不可视性的构建方式。《圣布鲁诺的愿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为主导,以布鲁诺的身体动作作为主线。其周围有四位主教和两位僧侣。除其中之一名字尚待确定,其余五位均可辨。画面中心伫立圣奥古斯丁主教,他仰头注视着三位一体,脚边放置着主教(英国国教)的主教冠和权杖。画中的“异象“是可视的,且被赋予重要地位。圣布鲁诺个人神示的场景即对“异象”的“灵见”被事无巨细的呈现给观者,构成了了画面中的可视性因素。因为当局认为神示的经历不经由教堂而具有风险性,所以画中的权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天地之间代理人的作用。但这层作用表现得并不明晰。可视与不可视性于《圣布鲁诺的愿景》中,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分配。
而后,斯托伊奇塔强调“拉斐尔的作品是先于视觉绘画的,其绘画最初同时最重要的是听觉绘画:使圣塞西莉亚沉醉的是听觉而非视觉。”③ “出神”和“享见天主”在传统上一直被定义为“一种纯粹的智性目光和对上帝与生物充满甜蜜的激情。”④在里瓦尔塔的作品中,圣布鲁诺的想象被完整的呈现,且占据了画面中心三分之一的空间,拉斐尔的作品中无法确定圣塞西莉亚的目光最终停驻于何处。圣塞西莉亚陷入智性观照的情态,数位歌唱的天使出现在其上方的云层上。乐器代表的三种音乐类型,分别对应尘世、灵魂、天界三个世界,反映了新柏拉图主义关于音乐的思辨。“异象”被赋予令人瞩目的浓烈色调,视觉地位十分重要。而“异象”仅有圣塞西莉亚一人看见,她凝神仰望,成为天地之间沟通的中介。这一中介沟通作用,某种程度上较里瓦尔塔权杖的作用传达的更明晰,反映出新柏拉图主义积极的人生哲学,属于“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照”。⑤
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圣塞西莉亚》和巴洛克时期弗朗西斯科·里瓦尔塔《圣布鲁诺的愿景》表现出清晰性和模糊性的差异。《圣塞西莉亚》中众人物的身形边缘均表现出统一的清晰性,圣塞西莉亚手持的管风琴的最远端的音栓轮廓,依旧同最近端的音栓一样清晰可辨。衣服上的细小褶皱亦被一丝不苟的交代。在实际情况中,身体轮廓、衣服褶皱和须发等,显然是存在或多或少的遮挡和缺失。《圣布鲁诺的愿景》中人物的轮廓线则间或隐入背景中,衣服褶皱和须发的交代也避免了古典艺术绝对的清晰。撇开客观的完整性,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涉及都以对形体的完全展现的描绘为目的。巴洛克风格则避免这种极致的清晰,而会给人以遐想的空间。⑥
从符号学角度审视,以上已提及的拉斐尔的《圣塞西莉亚》适用于“注视”的视觉逻辑,拉斐尔的另一幅作品《基督变容》和“叙述性的划分”一节中提及的佩德罗·杜兰朵的《圣母升天》则适用于“扫视”的视觉逻辑。通常属于持久的、冥想的,却是对视觉注意领域带有某种冷眼旁观和超脱意味的行为,与跨越一种平静的即那个的扫视划分开来。⑦后者不试图排除观看的过程,强调的是观看主体在持续时间内的视觉。《基督变容》中绘画的时间是被规定的,而非主动展现的。门徒们和被附身者身体的动态在这一刻被凝固了。他们在通常的视觉经验中却不可能静止,也不可能由扫视所看见。拉斐尔避开了将各三位人物叠放曾两组的构图,因为这种构图易显刻板凝滞。拉斐尔采用了吉贝尔蒂在佛罗伦萨洗礼堂浮雕中的布局,同时加入被附体者的描绘,使画面更加宏大,富于变化。⑧但并非是一种全知的注视。佩德罗·杜兰朵的《圣母升天》中“表现了那些目击者们在很短的时刻之前的情态。关于观看者,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融入到画面中。因此他可以(并且必须)让自己凝视的目光,在墓穴的黑洞和圣母玛利亚的肉体以及灵魂升入的天堂之间轮流转换。”⑨这种目光在墓穴和圣玛利亚的肉体以及天堂之前切换,诉诸于观看主体在持续时间内的视觉,被画家预设在画面中。于目光的不断转移间,巧妙地隐藏了自身的存在,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个持续的观看过程。《圣塞西莉亚》则隐藏了一种静观超脱的注视行为,画家企图以一种呈现永恒瞬间的方式来表现”异象灵见”,观看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排除。
于可视性中揭示不可视性,不可视性中包蕴可视性,为了建立一种深入绘画的视觉经验。
注释:
①②⑤⑧尔达尼埃尔·阿拉斯(法),李军(译).拉斐尔的异象灵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8,6,66.
③⑨Victor Stoichita(Spain).Visionary Experience in the Golden Age of Spanish Art[M],London,Reaktion Books,1995-10-30.
④阿蒙.天主教神学词典(第5卷,第2部分)[M].第1887-1888栏.
⑥沃尔夫林(瑞士),杨蓬勃(译).艺术史的基本原理[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254.
⑦诺曼·布列逊(英),郭杨等(译).视觉与绘画 ——注视的逻辑[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