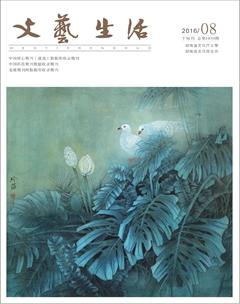论了凡诗词的空间叙事
赵莲花
摘 要:诗词呈现出“空间性”特征,不仅仅指文本表面上的建筑结构,还指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抽象的空间世界。在文本布置出来的“空间”里,了凡分别从言语的叙事空间、人与物的存在空间,以及自由的想象空间,构建诗词的空间世界。通过对了凡诗词做一个整体性的观照,借此领略到其空间叙事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诗词;了凡;空间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4-0001-03
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的表现形式带有语言表现形式的特征——时间的延续性。文学作品所呈现的形式,不仅在时间维度中展开,还表现在空间维度中。并且,这两个维度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任何文本都是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的结合。随着叙事学空间理论的发展,文学叙事作品的空间维度逐渐得到了重视,叙事文本中的空间元素建构在时间线索或时间链条的基础之上。
中国文化自古就侧重视觉与空间。因此,中国人的思维相对偏重“视觉思维”,或者说是“图像思维”。诗人生活在一定范围的空间之中,其作品所营造的世界是一个艺术的世界,“每一位诗人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万事万物的空间形态变化如大小、高低、方位、容量等等作出艺术的描写和反映”。因此,诗词多呈现出某种“空间性”特征,所涉及的空间并不仅仅指文本表面上的建筑结构,还在此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抽象的空间世界。
本文在前人对空间叙事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借用叙事学空间理论,展开对了凡诗词的解读与探析,探讨他在诗词中构建的空间世界。通过对“世界”“作品”(文本)“作者”和“读者”诸要素的综合考察,研究了凡诗词中这些要素与“空间”的内在关联。在了凡笔下布置出来的“空间”里,探讨言语的叙事空间、人与物的存在空间以及自由的想象空间。
一、言语的叙事空间
叙事离不开媒介,文学叙事媒介在中外理论著作中都有表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一章诗歌模仿的媒介中重点探讨了媒介问题,具体表述为“我所说的艺术中的模仿,是用节奏、语言、音乐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只用语言来表达的艺术形式”,“有些艺术使用了我提到过的所有媒介,即节奏、唱段和正式格律……但是,它们使用的方式不同……”。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原道第一”中谈到了叙事媒介——“言”(语言)的重要性,“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这两部在中外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作为最有影响的著作,都特别重视写作媒介——语言,并且都把“言”放在著作的开篇,足可见其重要性。语言文字作为文学的表达媒介,糅合了不同语码、话语习惯,以及认知模式,是汇集各种媒介的综合体。文学作品的空间形式正是以语言为基础,“这种言语的空间性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是通过使用文字而得到表现,加以强调和突出的”,诗词的语言尤其与空间形式密切相关。中国诗词以汉字作为使用媒介,而汉字又是从最简单的图画和花纹产生出来的象形文字。故而,中国古诗词很容易在形式上形成空间效果,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形式如宝塔,给人以直观的视觉空间形式,还有格律诗规定要五言或七言;词要规定词牌,比如《满庭芳》收尾必须是五言句押平韵,这些规定都是诗词组织本身需要的缘故,组织性的存在从形式上给了文字一个格式规定。
由于格式只是提供一个形式载体,可以把组织性看作是一种“物质存在”意义上的规定。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可以通过节奏的改变,或者句式的排列,甚至是修辞手法的运用,改变甚至中止时间顺序,在知觉上造成瞬间静止的画面,从而实现知觉上“同时性”的空间艺术效果。诗歌的空间构成依循一种与“时间逻辑”有别的“空间逻辑”,依靠空间的方位分布来组织字群、段落,所表现的则是由平行、并列、对等诸原则所产生的空间性秩序。一篇诗词里的字群、段落,并不是仅仅指向外界事物,也有内指、反射,从而形成彼此相互照应的关系。比如诗歌中的铺排,就是将一系列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或是事态现象,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句群,而这组句群在形式、结构和语气上基本相同。这种手法的运用可以通过诗词语言的陌生化技巧,达到营造不同空间的效果。诗歌中运用铺排等手法造成空间移动频繁,具有空间重现的效果。而这种空间效果,可以从形式上通过诗行之间,或者诗节之间的空白达成。文本阅读便成了在诗行或诗节之间穿行的空间行为。了凡在建构诗词大厦时,搭建了结构性隔间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比如他的词《满庭芳·西塘》:
柳挂寒烟,风穿雨巷,纵横十里连廊。拱桥高耸,船过水中央。河畔居前日月,烧香港外春光。鸬鹚立,艄头倒映,梦里老西塘。
悠长,天一线,石皮小弄,楠木花窗。有红樱,一枝横过白墙。惯对吴钩鼓角,曾经越甲旗枪。清波滤,千年旧事,滤不尽沧桑。
虽然这首词没有“宝塔诗”那样明显的空间形式,但是从组织上严格遵守了词牌“满庭芳”,以五言句押平韵结尾。了凡的这首词在字面形式上很用工夫,讲究技巧的同时,注重音律节奏。这组词里有许多景象与物象,没有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而是在同一平面上,用平行、并列等方法把它们一一罗列出来,形成了相互呼应,其运用的就是空间逻辑。词中借用语言的表现力来展示“巷”“廊”“桥”等客观世界的空间。然而,通过语言或文字所得到的空间认知相对比较破碎,具有片断性、非连续性的特点。正是这种空间展现的碎片化,使得全词的组织所依循的,已不仅仅是叙事的时间维度,还有更多的空间维度。
诗歌借助文字来抒情达意。然而,诗人在“言志”的同时,以色相给读者勾勒出场景,跳出诗的本位,具有描摹图画的作用。表达媒介由混合媒介构成,彼此间相互交叉渗透,尽管文学以语言为主要表达媒介,诗词中除了汉字本身的独特性之外,还借用其它媒介为自己灌注新的活力。语言文字是时间性叙事媒介的空间表现,这如同中国诗学中的“诗中有画”。一首诗的结构,除去叙述之外,主要是描写部分,而描写更多的是用语言绘画。故而,诗词就具有了图案式的空间效果。
二、人与物的存在空间
了凡在诗词里勾勒出的存在空间多表现为地志的空间,即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包括物理上的空间概念,以及人或物存在的形式空间,通过罗列词语建构这一空间,勾勒出的图像本身就属于“空间艺术”,其特点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先画后说,比如《山居》中的“云稀落日红,客去草堂空。独坐无人语”,先是勾勒出一幅黄昏独坐草堂图,在客人离去后再加一笔“隔山听晚钟”。了凡在《秋忘》中“水阔山迷乱,天高去雁多”的山水雁飞图,引发“浮云吹不散,弄影在清波。”的感触,还在《藏春》“细雨斜飞湿海棠”的雨中海棠图,发出“玲珑春色怎收藏?”的感慨;另外一种是诗词通篇全部是画,比如《秋暮》“水落江天冷,草枯林木稀。寒山吞一径,落日吐余晖。风抱青松舞,鸟追黄叶飞。铃声穿薄雾,寂寂老牛归。”描摹出了一幅完整的秋暮图景。
一个具体的、有特征、有个性的空间,是了凡在诗词中再现人与物存在空间的基石。他的诗词以客观存在的空间为前提,建构在现实中能够感知到的空间原型。比如《无题》中“野岸闲花独自妍,绿杨飞絮柳飞烟。不无明月西江影,时有清风上客船。”的空间依附物,以某种空间性的物件“花”“柳絮”等作为出发点,空间仍是这段文字中叙事逻辑的关键元素。巴舍拉在《空间诗学》中提出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在这首诗中的“野岸”“闲花”“杨柳絮”“西江影”以及“清风”,不仅仅是空间物件,还是人类意识中的孤寂与形只空间。诗词中勾勒的空间,不遵循因果关系和时间线索,空间结构呈现出并置、拼贴的特征。了凡在创作时以这种方式来组织事件,他的诗词就必然具有某种空间性。记忆(时间)被空间固化之后,成为稳固的存在。当然,空间浸孕在时间里而更加有活力,这种活力赋予人生“连续性”,并赋予生活和生命以价值。记忆固化空间的独特性,可以“复活”具体的空间,比如《与牧歌游东山》中的“东山”,地点在这里起到了激活并唤醒往事的作用。在所处的空间中,安稳存在的一系列定格,就像诗词中的这些地点成了“储存所”和历史情怀的触发地。从本义来讲,这些触发地是各种事件的发生地(空间),但从引申义上讲,这些地点(空间)又可指代容纳某类主题的话语或思想,并且成为这些话语或思想中的空间附属物。具有历史空间意象的地点,凝聚着某一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这样在情感上起着牵引和聚合的作用。因此,发生在这些触发地的事件,呈现出一种相互叠加和互在其中的特征。
了凡作品里的存在空间除了唤醒文本中的历史空间,还有借登高来拓宽视野。他的众多登台之作中的《瑞鹧鸪·登泰山》“九霄极目收寰宇,五岳独尊穷大千。”面对如此开阔的空间视野,除了给词的“笔调”、“气氛”增添色彩之外,对作者自身情感的表达也有着重要作用。开阔的现实空间和作者正当得意之时的浩大胸怀交融在一起,“指点人间天下小,只缘身在彩云巅。”已经分不清是物还是“我”了。每句词在本句内都是一环扣一环,各句诗词联缀起来又构成自足系统,前后相互参照,结成一个具有承接性的整体,“一旦这一事件是在一统一的时间系统中而不是作为各自独立系统的关系而出现时,时间知觉就让空间知觉取而代之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个的消亡,而是经过这种知觉的转换,空间知觉与时间知觉两者共存,空间行为在时间维度上的被综合起来。同时,这也说明好的“空间形式”建立在“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结合之上。由于语言的选择性和文本线性叙述等原因,空间在形式上所呈现出的状态具有未完成性。如果把文本看作是个开放的系统,不完备的信息往往开拓了文本表面所展示的物理空间,而这里的物理空间表现为人或物的形象空间,建造这个空间主要在于视域的扩展,以及激活想像空间。此处的图像与事物之间是不能划等号,人与物的存在空间不是指事物本身,而是人或物的形象或物像,这就需要图像去语境化。记忆中的影像是持续经验的剩余,记忆中的事件具有连续性和语境化。诗人在创作中,搜索记忆中的影像,用代表性的空间物象代替这些影像。因此,这些物象也具有了语境化和空间性。
三、自由的想象空间
诗词中的画面,借用语言文字这一媒介的所指,进而勾画或指代出来。空间建构在语言提供的物理空间“参照”基础上,扩展到读者的想象空间,并在空间维度中相继展开。诗词中指代的物象,在物理空间里没有连续性的联结,需要借助一个感知桥梁,出现在想象空间中。通过碎片化的空间画面组合,造成时间上的连续,同时又留有时间空白,给予更多想象的空间,连接文本内部和外部,甚至和其他文本,具有空间形态的延伸性。诗词的空间维度不仅涉及表层叙事,还带有文学、历史和心理多重因素。
自然空间的表述只是一个前奏,以景写心才是了凡诗歌的真正意义所在。然而,“心”的表达需要借助一定的空间,需要有物象存在来寄托。诗歌叙事所表现的空间,受到语言的选择影响。由于语言无法完整表述空间信息,这种局限性导致含糊的空间描写,叙述的详略和语言的选择性决定了叙事中空间重现的效果。《藏春》中的“细雨斜飞湿海棠,玲珑春色怎收藏?呼来燕子张双刃,好剪东风一段香。”中的朦胧境象,而这需要自由空间的想象来填补。这里“细雨”“湿海棠”等空间意象,在叙述过程中的次序不同,影响了存在空间运动的变化方向及轨迹。由此,文本之外的想象空间推移也随之受到影响,与推移相关的视点会影响叙事中空间的重构。超越文本的想象空间,与囿于文本想象空间之间,形成不同的关注点,两者在叙述过程中可以相互转化。然而,不同的聚焦会产生不同的空间效果。《深秋夜高楼凭栏一》“风长灯欲灭,人静夜清寒。弯月楼台外,摘星指掌间。”正是借视角转换,由楼台内部景象转入外部景象,给人以空间流动之感。了凡诗歌中的场景布局及空间艺术中图像空间,呈现对位关系,为探寻诗歌文本意义提供了形象化的感知空间和想象空间。诗人在诗词中勾勒出一个个虚拟空间,目的就是要在这个空间中寄托个人情感。从这个角度上说,想象空间也是对现实空间的一种描摹与超脱。
了凡的诗词借用语言媒介,以描绘的方式来摹仿世界,基于人与物空间存在的“参照系”,唤醒沉淀的记忆,从而激发自由的想象空间。同时,诗词也建构着人的精神情操与审美情趣。诗歌的语言选择使情节具有跳跃性,这些跳跃的部分也是诗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的空白部分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凤凰台上忆吹萧·枫桥夜泊诗意》中的“月落”“斜桥”“乌啼”“老树”“凝霜”“积露”孤零零地独立存在,它需要受众者的想象去填充更为具象的时间和空间内容。《梅雪缘一》先是由“相思”引出,再到外在空间中的“雪影”,又在颈联和尾联转入“君意”“妾心”“骚客”的人物心理空间,引发读者去探索人物心理深层的精神奥秘,从而开拓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诗词中所流露的细腻丰富的情感,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这里的“情”相比文本讲述的实境来说,是“虚”的,是不可描摹的,但是正是有了这“虚”的介入,诗词因而具有了想象的空间性特点。文字作为一种抽象度较高的表意符号,塑造的图像取决于读者的想象空间,对于想像中的 “事物”,是可以描摹出来的。《秋暮》里把静态的物象“寒山”“一径”、“落日”“余晖”、“风”“青松”、“鸟”“黄叶”、“铃声”“薄暮”,分别用动词“吞”“吐”“抱”“追”“穿”连接起来,营造了一种划破空间的动态美。
“空间的再现并不是众多单独场景的组合,而是由一系列流动场景建构的复杂、精细的空间复合体组成,涵盖了地志的、时空的和文本的多种因素”,言语的叙事空间,人与物的存在空间,以及诗词里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一起形成鲜明的空间层次感。了凡的诗词有较多的空间留白,给读者留以足够的空间想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作想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确定一个完全具体的地方。不过,这不是贯穿了观察者情绪的一种抽象的景观,绝对不是。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了凡诗词中的空间物象,不仅是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场景,还有像“丞相祠”“吴钩”等具有历史感的地点和物件,赋予诗词更多的想象空间。创作中的记忆和想象均具有明显的空间特性,文本设置的空间被填满了空间以外的许多意义。了凡诗词的空间叙事,从言语的形式空间,到人与物的存在空间,以及基于前者引发的想象空间,并最终生成这样的整体空间。
四、小结
应用叙事学空间理论,分析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将诗词置于世界文学批评的脉络之中,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对了凡的诗词开辟一种新的视域和趣味。“艺术品,与人类经验中所有其他物体一样,都是时空结构,而有趣的问题就是理解特殊的时空构造,而不是比喻意义上的空间形式,而是一个时空构造。‘空间和‘时间正两个术语只有在相互抽象为独立的、用来界定物体属性的对立本质时才时比喻性的或不恰当的。严格说来,这两个术语的用法是一种隐蔽的提喻,把整体缩减为部分”,诗词正是让特殊的“空间”,“一种表现的而非被表现的空间性”,通过文学语言这种特殊的时间性媒介自动地呈现出来。
了凡在建构诗歌的空间逻辑时,其作品在形式上有空间性,内容也有空间性。空间单位由语言传达出来,并且超出“这一世界”的特性,基于对文本的理解,以及个人记忆回溯的综合体验。同时,了凡的诗词扩展了置身在虚构世界里所感知的想象空间。他在诗词中借用不同物象,造成的视域转换是一个自然流动的过程,所营造的空间由一系列场景来回切换的空间复合体构成,涵盖了地志的、时空的,以及文本的等多种因素。本文通过分析了凡诗词中言语的叙事空间、人与物的存在空间以及自由的想象空间,对了凡的诗词做一个整体性的关照,借此领略到其空间叙事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张三夕.论苏诗中的空间感[J].文学遗产,1982(02).
[2]亚里士多德(古希腊),贺拉斯(古罗马).郝久新(译).诗学·诗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3]刘勰.戚良德(注说).文心雕龙[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4]热·热奈特(法).王文融(译).文学与空间[A].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M].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5]陈振濂.空间诗学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6]了凡.半坡烟雨半坡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7]鲁·阿恩海姆(美).郭小平,翟灿(译).艺术心理学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8]流沙河.十二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9]毕恒达.家的想象与性别差异[M].加斯东·巴舍拉.龚卓军,王静慧(译).空间诗学[M].台北市: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10]龙迪勇.空间叙事学[D].上海师范大学,2008.
[11]巴赫金.晓河,贾泽林,张杰,等(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2]W·J·T·米歇尔(美).陈永国(译).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