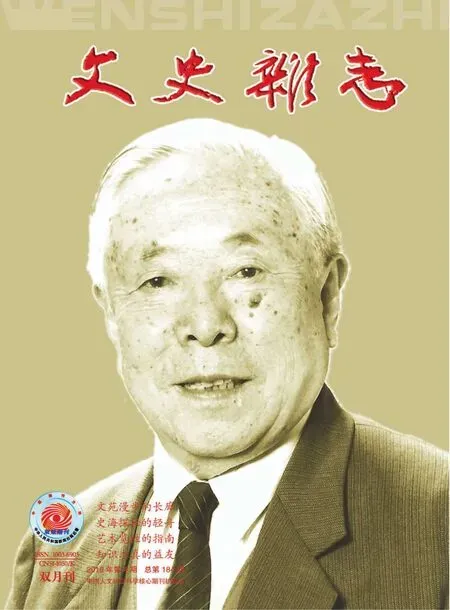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前期的战略抉择
墨 青
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前期的战略抉择
墨青
摘 要:惨酷的湘江战役过后,中共中央及时举行通道会议,实行通道转兵,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随后又举行黎平会议,再次转兵;终在猴场会议后突破乌江,在遵义召开了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走向成熟,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关键词: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

鲁迅先生(1881—1936)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等南方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前后经历两年时间。英勇的红军,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毅力,走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10余个省,经过了汉、苗、壮、彝、回、藏等约2亿人口以上的不同民族地区,徒步走了两万五千里。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鲁迅和茅盾先生满怀喜悦地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
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1]
毋庸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等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的结果,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的胜利。
一、通道转兵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1933年春,党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之后,“左”倾路线就在中央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左”倾领导人极力排斥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与分析。在军事上他们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又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阵地对阵地,以堡垒对堡垒,用短促突击的方法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到1934年4月28日,蒋介石军队已攻占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到了9月,苏区已很危险了。
此时毛泽东被排除在党中央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圈以外,只保留了一个中央苏区政府主席的行政职务。不过,他虽“不在其位”却坚持“谋其政”。他曾主张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2]。然而,“左”倾逃跑主义者,被敌人气势汹汹的进攻所吓倒,只想如何逃避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却不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叹息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3]
10月上旬,敌人占领了石城,逼近红色首都——瑞金。至此,除了战略转移以外,别无出路。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长征,留下项英、陈毅3万余人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战;红军主力86000多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于都、瑞金分两路向西前进。长征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这样开始了。此时,毛泽东疾病缠身,孤居于都北门外的何屋。他从这里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中央红军长征,当初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因此,红军长征开始时,并没有预计要走万里。蒋介石反动派得知中央红军西征消息后,在红军前进的要道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妄图阻击和消灭中央红军于湘南。而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又给行进中的红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一种搬家式的甚至是惊惶失措的逃跑,对于这样重大的军事转移行动,既不在党、政、军内进行动员,又不把转移的战略意图和战略方向告诉给广大将士,甚至不交给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讨论议决,致使战略转移忽东忽西,漫无目标,并且始终摆脱不了敌人,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从10月21日至11月30日,中央红军虽经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减至3万余人。
红军广大指挥员亲眼看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4]。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5]。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接受血的教训,不从战争的实际出发,而是继续指挥红军经湖南、广西边境的苗族、壮族居住的越城岭(即老山界)地区,向红二、六军团所在的湘西根据地前进。蒋介石唯恐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即调集大军前堵后追,使敌我兵力十分悬殊,我军处于进退维谷境地。面对这种严重形势,“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向湖南西部进军,往敌人布下的口袋里钻。刘伯承同志后来回忆说:“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采取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6]。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毛泽东对形势作出了深刻分析,坚决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把他的主张,向中央军委的多数同志,特别是犯过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进行细致而耐心的宣传,终使他们开始觉悟。于是,当中央红军在12月12日,进到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芙蓉地区时,党中央召开了一次临时性的时间很短的政治局会议,对作战方案及进军方向进行讨论。毛泽东被请回来参加会议,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政治局大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李德却坚持原来的计划,他在会上说:“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六军团建立联系。”[7]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不同意李德的意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通过了。“通道转兵”之后,中央红军还进行了整编,撤销了红八军团,合并了中央纵队,使部队得以轻装前进。

过湘江(黄镇画)

红军时代的毛泽东(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摄于陕北保安)
此后,中央红军开始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从而成为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第一个转折点。通道会议为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二、黎平和猴场会议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
通道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很快又踏上征途,于12月15日、16日先后进入贵州黎平县境。毛泽东、王稼祥和洛甫先前曾一致同意,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计划和方针。在匆匆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大家默认了这一决定。现在,军事压力暂时没有了,在黎平给养又比较充足,每个人都能吃饱肚子。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在这种情况下,12月18日晚,黎平政治局会议便召开了。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王稼祥、洛甫、毛泽东、朱德和林彪都参加了。李德和其他领导人大概也参加了。会议开得很紧张,发言人都提高了嗓门。周恩来几次发言,公开批评李德。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发表的意见。他正式建议放弃北进与贺龙会合的计划,而提出红军西进贵州,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挺进,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他强调指出,现在红军不再受到湘军的袭击了,黔军又有烟瘾成疾的致命弱点。因此他建议在遵义召开一次正式会议。黎平会议否定了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共产国际所派)提出的坚持去湘西的错误意见,肯定了毛泽东的决策,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定》,规定中央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同时指示二、六军团在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四方面军应准备发动新的攻势,以便当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钳制川敌。20日,中央红军调整战略方向,开始西进。
“黎平转兵”,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创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第二个转折点,它为尔后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
黎平会议后,红军继续向贵州腹地进军,于12月31日抵达距离乌江将近l00里的猴场。
当晚至次日凌晨,党中央在猴场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向川南发展,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结束了李德个人说了算的霸道作风以及他和博古所掌握的红军指挥权。而从湘江战役后到黎平会议,周恩来与李德之间曾有过的激烈争论,实质上也是周恩来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趋于一致的反映,是党的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所进行的斗争。猴场会议还采取组织措施,限制李德对中央政治局重大决策的干扰,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更进一步的准备。此时,周恩来“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8]。猴场会议后,红军分三路(江界河、茶山关、回龙场)强渡乌江,突破了敌人吹嘘为“重叠坚固,可保无虑”的乌江防线。1935年1月7日,红军解放了贵州北部的重镇——遵义。
然而,黎平决定带来的乐观情绪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消失了。红军情报部门离开黎平时报告说,守卫贵州的只有王家烈的四个师,这些部队都是大烟鬼,因而确实虚弱,不堪一击。可是,就在毛泽东进入遵义的当天,国民党的两个高级将领周浑元和吴奇伟率精兵也跟着进入了贵州,并迅速接管了首府贵阳。贵州军阀王家烈倍受鼓舞,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派遣他的第三师共七个团的兵力,去攻打彭德怀的第六师……
红军的情报部门很快掌握了敌人的这些调动情况。他们得知,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指挥这次行动,并且调动了湖南的4个师、川南的两个旅和云南的3个旅,共拥有150个团大约40万兵力。不仅如此,红军还发现,遵义地区经济落后;盛产鸦片,却没有多少粮食,很难维持一支不断扩大的革命军队。再说遵义地区三面环水(三条重要的河流——乌江、赤水在西边形成了一条曲折的边界,北边是滔滔长江),如果红军在这里驻扎下来,势必遭到围歼。从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是不能实现了。
三、遵义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与此同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引起广大干部和党员对“左”倾教条主义越来越大的怀疑和不满。他们都亲眼看到一个事实: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胜利,不断发展;而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下,却丧失了原来的根据地。经过斗争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由于毛泽东在党内作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有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悟起来,站到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立场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从1935年1月15日起,党中央政治局在遵义老城琵琶桥原国民党军的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当时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楼上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大致如下:

遵义会议会址(选自《历史真相②》)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王稼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洛甫(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博古(秦邦宪,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凯丰(何克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红星报》主编、改组中央后任中央秘书长)、伍修权(翻译)、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总计20人。(此名单据新华社1984年3月4日援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材料。另一说还有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参加,计21人。)

1936年6月红军大学成立后,红军将领在陕北保安的一次合影。图中有毛泽东、朱德、林彪、何长工、周子昆、杨得志、陈赓、贺子珍等(选自师永刚、刘琼雄编著《红军:1934—1936》,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3页)
会议是于1月15日晚7点钟正式开始的。在柏公馆楼上的一间长方形房间里,与会20人在一盏吊式煤油灯下团团坐定,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方向,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根据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七章的介绍,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发言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是正确的,但自己在军事路线的执行中犯有错误;不过他又力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承认政策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说,这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率,丝毫不想推卸责任。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毛泽东开会时原习惯于最后发言,这次他却紧接周恩来发了言,而且一发就是1个多小时,比任何其他人讲得都长。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说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政策(李德的“短促突击”取代了朱、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毛泽东反驳了李德认为失败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这一观点,说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伍修权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坚持认为军事路线错了,并指出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发言说,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即战士也是人,也要用双脚走路,也要吃饭、睡觉。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福建事变”中的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军队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而周恩来、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经主张和十九路军联合。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发言。他曾对聂荣臻说过:“到时候要把他们轰下去,把李德拉下台!”他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批评火力”持续了三天。会议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开始,每次持续四五个小时。与会者的措词越来越激烈,翻译伍修权也感到越来越紧张了。
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很多指挥员都指出长征缺乏思想准备的问题。他们认为,部队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因开小差而造成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新兵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往常执行任务不同,这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为什么必须作出牺牲。指挥员们认为保密工作做得太过分了,连很多指挥员都不了解情况,这样就影响了战斗意志和官兵们的士气。
洛甫和朱德坚持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发言,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9]
会议于1月17日晚结束。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了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观点。会后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由洛甫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而起草,在扎西会议上正式通过)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遵义会议根据战局的变化,对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向川南发展,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决议作出改变,决定红军渡过长江至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新的战势,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的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10]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正式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拥有最终决定权。随后,红军在转战途中,于2月上旬召开的扎西会议上,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对常委进行了分工: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习惯上也称为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在行军途中的3月12日,又组成由毛泽东提议,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称“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指挥。这便表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已经确立。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航,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11]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次大手笔,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坚持不懈地与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党内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四次会议一个接一个,一直贯穿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这一斗争中,毛泽东等有勇有谋,采取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方针和策略,将绝大多数同志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才取得了包括遵义会议在内的若干会议的伟大胜利。
特别是遵义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高屋建瓴的决策魄力以及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最终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因此成为红军长征的一个最具决定意义的根本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 年4月20日通过)所指出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诚如肖华后来在《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词中所吟到的:
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
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
……
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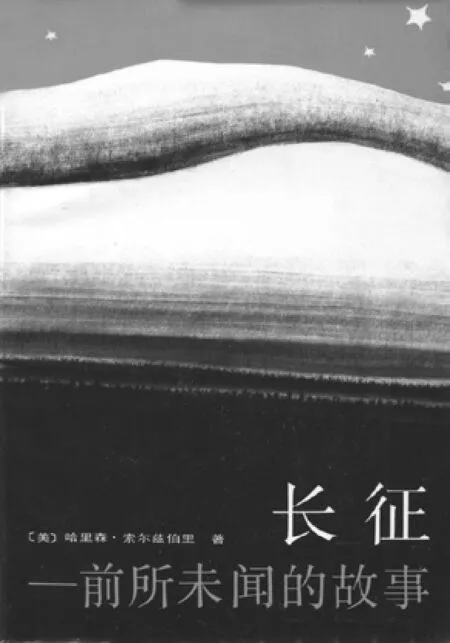
注释:
[1]鲁迅和茅盾先生致党中央、毛泽东关于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报,虽广为流传,但有人质疑其真实性。关于它的来源,据传是由鲁迅的朋友、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共产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的。1935年底,在上海的史沫特莱将红一方面军完成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告诉鲁迅。时鲁迅正卧病在床,仍在次日与来访的茅盾商议联名致电给红军,表示祝贺。后来茅盾在回忆中说确有此事,只是当时尚未见到鲁迅起草电报。这封贺电,录自师永刚、刘琼雄编著《红军:1934—1936》(三联书店2006年版)一书第219页。又查《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4页“附录三”,确有《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长达三四百字,其中关于“英雄(勇)的红军将领”一段大致就是师永刚、刘琼雄收录的那七十余字,内容有出入。《鲁迅全集》所收《贺信》的落款是“一九三六、三、廿九”。据《全集》对《贺信》的注释,其原载于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刊物《斗争》第95期(1936年4月17日),“系为祝贺红军东渡黄河对日军作战而写,起草人未详”。看来《全集》编者也对这封贺信的真实性难以把握,故而将其列入“附录”,以待进一步考证。
[2][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237页。
[4][5][6]刘伯承等:《回顾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5页,5页。
[7](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3—1939》中文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9]以上参见(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144页。
[10]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页。
[11](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