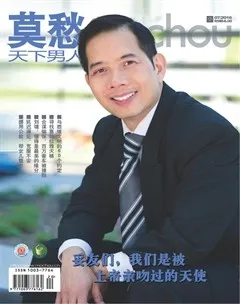寻找喜马拉雅天梯
豆瓣评分9.4分,很多人看完一遍,又再看第二遍、第三遍,根本停不下来,一部题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竟然可以媲美影院的商业大片,这部纪录片的出品人萧寒是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同时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让灵魂找到要去的方向
其实萧寒是笔名,他本名叫崔涌,是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副教授。
六年前,萧寒过着安稳的生活,但总觉得少了什么。骨子里,萧寒一直渴望一种更为安静、专注的自我表达。2010年,好像多年的积累突然到了某一刻需要喷发,他去丽江拍了一部小型的独立纪录片《丽江拉夫斯基》,纪录了七个生活在丽江的年轻人,七种人生,七段故事,不同的爱情观、价值观、人生观在此碰撞……
这部直面内心的纪录片虽然没有进入影院,但在网上获得了600万的点击量。自此,萧寒开始对纪录片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自己说,下一个十年,就交给纪录片了。那之后他就在想,寻找一个更大的更厚重的选题玩一把。
有人告诉他,有个故事一定会直指人心。讲故事的人是清华大学的老师雷建军,也是萧寒的好友。雷建军了解到,行走在青藏高原常常能看到路旁的岩壁上,有藏族人用白色颜料绘制的一个个小梯子。据说,这可以帮助人升到天堂,藏族称之为天梯。在拉萨有所登山学校,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培养高山向导为目的的学校。珠峰脚下的藏族少年在这所学校里接受四年训练,方可成为一个合格的高山向导,成为“天梯”。
高山向导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他们要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珠峰挑战者服务,铺路、修帐篷、背氧气瓶,有时甚至需要移开路上登山者的尸体。
正是高山向导这样的精神和信仰打动了萧寒。他们非常平凡,却站在世间最高处,给世人留下了动人的故事。
由此,萧寒与雷建军定下了拍摄《喜马拉雅天梯》的方案。他们想纪录这些藏族少年的故事,记录在氧气稀薄、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释放出的温情、欲望、失望、愤怒、勇气……当然,还有梦想。
这是全球范围内首部以超高清4K电影画质完成的极限纪录电影,拍摄过程中第一次将摄影脚架带上珠峰峰顶,第一次在珠峰海拔7000米以上高度进行特殊摄影,第一次将飞行器带上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完成航拍摄影……实际拍摄中存在很多困难:要把电池带在身上,在寒冷高海拔的地方,如何让电池多工作一会,揣在怀里,用暖宝宝,萧寒团队进行了各种尝试。航拍的飞行器不小心摔坏了如何解决,设备怎么背上去,这些都是烦人的问题。
为了跟拍登山向导的身影,拍摄组在珠峰大本营驻扎了两个月,萧寒的助理患上了中度肺水肿,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深切体验着高原反应。“我们把只爬过北京香山的摄影师逼成了登山运动员,扛着机器爬到了海拔7028米,从160斤减到了140斤。”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萧寒感慨莫名。
摄制组克服重重困难,以极高的技术难度和极强的毅力,捕捉了大量极致环境中的自然和人文影像,让最终拍出来的画面极具震撼力和奇观效果。
一开始,萧寒带着一种理想化色彩,当初以为100万元的拍摄费用就够了,当第二个100万元很快花完后,他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坑,但他还是无畏地跳了进去。当剪辑师最终停下手中的工作时,所有人的眼中,都有最复杂的情绪。这部片子拍了四年,拍摄制作最终花了1300万元。
纪录片里,年轻人不断做出选择,寻找方向;纪录片外,人们穷极一生,也无不在寻找一条天梯,能让灵魂和精神去到一个更好的方向。2015年10月16日,在众多热门商业电影的围攻中,《喜马拉雅天梯》不仅进入了国内院线,还获得了千万票房,登上了中国纪录片票房的“天梯”。同时它还获得中国首届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最具国际传播潜力大奖,并以中国区第一名的身份入围法国阳光纪录片大会亚洲展,BBC、NHK也都决定购买版权……
以匠人之心拍匠人
在宣传《喜马拉雅天梯》期间,萧寒再次接到好友雷建军的电话,带来一个让他动心的故事。当时故宫博物院正值90周年院庆,寿康宫将完成史上最强复原,两百多件曾经深藏故宫库房的珍宝,将重回寿康宫。因此,故宫想寻找优秀团队拍摄一部关于故宫文保科技部的纪录片,记录下科技部各个小组修复文物的过程。雷建军曾在央视拍摄过故宫纪录片《故宫100》,五年前就考虑过拍摄文物修复者的选题,因此便联合萧寒与故宫展开了这场合作。
第一次见到闭馆的故宫博物院的情景,萧寒记忆犹新。那是2015年的春天,北京城内柳絮纷飞,他看着空无一人的太和殿前广场,突然觉得自己与历史从未如此接近。那一天,他要去采访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青铜组的王有亮与高飞师徒,这段采访后来出现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第一集中,片中旁白说道:“古代中国‘士农工商’唯一传承有序延续至今的便是‘工’,文保科技部现在仍然沿袭着师徒制。”萧寒说:“王师傅接受的是最传统的修复工序,而高飞又是一个受现代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十分关注高科技的修复方法。他们被百年流传的师承制度紧密连接,师父倾尽所有教学生,学生任劳任怨帮师父,那种温情和现代科技的结合特别和谐。”萧寒身为大学教授,对现在社会日益淡漠的师生情有着切身体会,故宫里这种传承意味浓厚的师徒关系令他动容。
除了传承,另一个萧寒希望在片中表达与探讨的东西,是匠人精神。师傅王津修复的铜镀金音乐水法钟,原来的主人是乾隆皇帝,一个小毛病也许就得调上一天半天,这个过程还得反反复复。王有亮在堆满调色板的工具桌上调配青铜器的颜色,不顺利时一个颜色都要调上一个星期。这是个不能急的行当,与当下快速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他们的时间感与宫外的人们是不同的,干这行最重要的就是坐得住。镜头里,修复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磨性子。师傅告诉弟子的第一句话也是这句:只有耐得下性子,才能做好文物修复工作。
其实对于纪录片也是一样。萧寒说,这部片子也是“磨性子”的成果。在2015年4月正式开拍前,他们用了五年时间去做田野调查,一趟趟地去故宫看他们工作,熟悉人物,光是调查资料便写了十万字。
为了呈现出现代化的故宫,萧寒和他的团队在故宫里拍摄了近四个月。师傅们以为他们呆几天就会走,当时正值春夏,这群年轻人却天天都在。
与修复的师傅们同劳动、同吃饭、同聊天,这支拍摄团队不仅获得了师傅们的信任,有些还成为朋友。故宫里严格遵守朝八晚五的工作时间,纪录片的工作团队却不会在5点收工,只要师傅们不反感,下班后还要跟着。
于是镜头里,儒雅内敛、开朗外向、各具特点的修复师们展现了故宫的另一面。因此,一部青春化且让年轻人看得下去的纪录片便产生了。
让小众艺术进入大众视野
《我在故宫修文物》于2016年1月7日在央视九套首播,当时并未引起轰动。出乎萧寒意料的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网络火爆最先来自“90后”“00后”。
有一天,萧寒在网上注册了一个账号,想看看他的纪录片能不能被这些年轻人喜欢。没想到,刚注册成功,还未发布任何内容,就涌进来上百号粉丝,网友们纷纷表示不过瘾,要求导演赶紧出续集。有中学生留言说,自己是在视频网站看的这部片,那是他爸第一次让他看完整个视频,还说好好把它看完,看完再做作业。萧寒不由得感概,真正好的东西才能打动每个年龄层的人,因为人性殊途同归。
几部纪录片作品的成功让萧寒意识到,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大众渴望看到那些闪光的角落,和游走于主流之外的人生经历。以一双凡夫俗子的眼,一颗入世踏实的心,感受和记录世外之人的故事,便是萧寒在纪录片创作中得到的最大乐趣。虽然纪录片市场仍然属于小众创作,但萧寒已经渐渐感受到人们对它的期待。他说:“社会越来越浮躁,人们就会越来越渴望真实的经典的厚重的东西。”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钟健 124976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