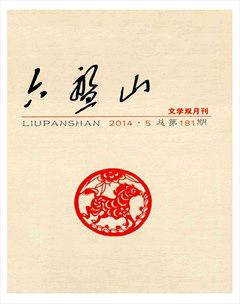千纸鹤
常越
白纸,在我的手中折来折去。妈妈问我还折这些有什么用?我没回答,继续折折叠叠。想你的时候,我就选白色的纸,折千纸鹤。每每听那哗啦哗啦的纸张在手中摩擦着发出声响,折出了白色羽翼的小巧灵动,我就闭上眼,它似乎就可以飞翔了。把它握在手心,握得久纸张潮热了起来,一展开,它就冷了。
两年前的初冬,下了雪,地上结满了冰,路很滑。大舅打电话哭着说,表弟夫妻俩遭遇车祸去世了。雪花旋转着密密层层地包裹住我的身体,如同飘落在寒风中孤单的雪人,四周是冷的,我的眼泪和着雪花飘落了一路。“亲爱的表弟,我知道你走了。”“去世”这个词太生硬,说不出口。我愿意说“你走了。”或许是因为:走了可以回来。就像小时候,你站在村口路边,怯怯地看那些下车的人里有没有我。
每逢假期,我从石嘴山坐上班车,回到乡村的姥姥家待一阵。大舅家和姥姥家在同一个四合院。只要我来,你就靠在门框边上,离我不远不近地站着,搓弄着衣角,有时候还踢踢门槛边的土坷垃。我就俯下身来看你躲闪的眼睛,刮刮你的鼻子,直到你笑了,才放了你。其他的表弟表妹们围拢起来问长问短,我总是等他们跑远了,再给你的口袋里多塞一块糖。那时候,大舅家条件不好,土炕上嬉戏着高高低低的孩子们。他盼着孩子们里能有个城市户口的,唯有你长得俊俏是大舅的心尖子。老远,看见我来,大舅就对表弟说:“看,那才是你姐,亲姐!你大姑妈才是你亲妈。”其他的表弟妹叫我二姐,你叫我小姐姐,我就爽快地答应。后来,大舅舍不得你,没有把你过继给我们家,你还是叫我小姐姐,那稚气的声音我听着心里暖。
秋收农忙的季节,我就成了孩子王。大人们顾不上给半大孩子们做饭,我们就到瓜田里摘些熟透的西瓜,在田埂上一摔两半,用柳枝当筷子吃得香甜。没多久,听到肚皮饿得咕噜噜地响,我就让几个表弟妹过来,坐在土坷垃砌成的瓜棚里讲故事。讲过两遍,你就惟妙惟肖地模仿我的语气复述这个故事。看我站起身点燃干麦草杆,驱除黄昏里密密麻麻的蚊虫,你就小心地把那些在七十年代视为珍宝的小人书,用大大的向日葵叶子包了几本,似乎是给它们包了碧绿的书皮。当我转过身,发现有的小人书上沾染了黏糊糊的绿色叶浆,不由得恼了,看你认真的样子越发气了,就把那些包了向日葵叶子的小人书往你怀里一推,让你先回家去。
天色越发暗了,我独自抱着一摞子小人书,在田埂间流水旁不敢快走,生怕把书掉在了癞蛤蟆的身上,脏得恶心。或许是看我面生,别村的男孩子们会尾随而来争抢。你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我面前,夺回那些撕扯坏了的小人书。好在乡下的孩子们大多质朴,慢慢熟悉了,相安无事。
过了些年,大舅家卖了骡子购置了拖拉机,又过些年卖了拖拉机又买了汽车,拆掉旧土坯房盖了崭新的砖瓦房。大舅的年龄大了,嗓门也越来越大。舅妈说现如今不兴做花布鞋穿……大舅在一旁听了说:“往后,鞋样没啥用,扔了干净。”舅妈年轻时做布鞋的手艺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鞋样也精致耐看。那些发黄的旧纸张,多是给我和姐姐做布鞋时用的。我觉得好看,问舅妈要来画着玩儿。舅妈笑笑不说话,把那些鞋样塞进了床垫最里面。你知道我喜欢,就偷偷拿给了我,惹得舅妈一顿打骂。听着你哭,吓得我好久不敢去大舅屋里转悠。没多久我发现,在你家屋檐下的燕子们陆续飞到姥姥家旧房子的屋檐下筑巢,生蛋,经常会从燕子巢里跌落下嘴巴还嫩黄的雏燕,掉在地上唧唧叫唤。你比我长得快,个子高出我一头还多。我就小声唤你把它们放回巢里。大舅看见了,呵斥你去给羊儿多喂些草,我会紧跟着去,听着小羊羔的叫声,你满眼都是欢喜。
乡下的孩子最盼过年。农村的惯例是家家户户要宰杀几只成年的羊,一大家子人过年慢慢享用。可是羊儿们凄凄惨惨的呼救声,我俩听得难受,就相互闷着不说话。大舅对你说:“喂羊儿你出的力最多,应该多吃羊肉。”你却说:“羊肉膻,不想吃。”大舅问:“你小时候,大姑妈买来的羊肉,你咋吃得那么欢?”你一脸凄楚,低头不语,转身就跑去喂羊,来来回回地溜达了好久。
成年后,你成为地道的庄稼汉,结婚生子,生活得平稳快乐,听说你依然不吃羊肉。我从石嘴山搬迁到了大武口,成了家有了女儿。慢慢地,我很少回姥姥家,难得见到你。见了面,却生分得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你走后,大舅不再大声说话,总是沉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头黑发全白了。老远地看见我来了,就颤着声,让你两岁的女儿叫我“干妈”,神情和语气就像小时候他让你叫我姐似的……
今年,村庄拆迁了修路,大舅搬进了城里的楼房。我离大舅家近了很多,可你却不在了。过了年,姥姥去世了。我知道,那个小乡村和姥姥家都没了。那一晚,我梦见雪后的乡村天气很冷,我刚要拉你的手,不知怎地就醒了,泪水滴湿了枕头,我把枕头慢慢地翻过去,再也无法入眠。
我想:你是行走在大千世界的普通人,但你有一颗真挚善良的心和一双温暖的手。我相信:天堂里会有彩霞映照的海水,会有繁星点点的夜色,也会有我为你放飞的千纸鹤。你会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