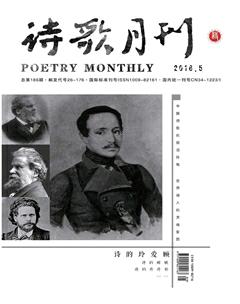养小之诗,逸乐之风
周东升,安徽霍邱人。主要从事现当代诗歌批评与研究。现任职于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
一、“我想我到达的地方比彼岸或者更重要”
边围在他的诗集《也算喜剧》序言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有哪一天,写诗不再会让我们心生傲慢和敌意,而是更亲和、更善意于人世,我想那可能就是真正的自由与自在吧。”读完他近期的诗歌,我想,他确是一位诚实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我真切地感到了一种贴近心灵的亲和感,一种与俗世(现世)和解的善意。在一个动辄超越、批判或惯于沉沦、玩世的物质时代,他带着一颗平常的赤子之心漫游、饮酒、赏花、听音乐,而我们那百无聊赖、司空见惯的琐屑生活,经过他的目光打量或诗笔书写,无不散发出情致盎然的诗意。从他的诗集里,可以信手拈来许多我们经历过却又常常漠然无知的事或物,比如:
夜在外面过夜/筝里,一个纤纤的美人沉睡——《听筝》
野径偶如褶痕/山脊上把玩沧桑。——《春山》
不远处/每一个水涡都有家史——《小雨》
一路东行,终于奇遇了桃树/这多值得炫耀呵——《郊野》
等等,不胜枚举。更重要、也更值得钦佩的是,边围说“我没意识到这是在写诗”(一念),他不是刻意,更非“为赋新词强说愁”,他的生活似乎处处弥漫着诗意,花花草草、小石小木本身就是诗,而他写诗既不像古人那样背着锦囊,骑驴四处觅诗,也没有现代诗人的佯狂怪异,他平静地工作着,生活着,写着诗,这种朴实的生活与写作以及这种生活与写作表里如一的诚实,不正是我们几千年来的诗教传统所倡导的吗?
诗歌写作原本不是急切与功利的,更多时候,它仅是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它也可以是人生的要义,但绝不会替代人生,喝酒当然可以写诗,写诗可以助酒兴;漫游当然也写诗,以诗增添人生的快意。但为写诗而喝酒、漫游、看花、赏月、谈恋爱,似乎本末倒置了。而这种倒置的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真不少见。结果呢,可能诗没写好,日子也没过好,人让位于诗,生活附庸于写作,内与外分裂,于是病态,于是癫狂……
晚清以降,急于脱困的国人失去了平和的心态,诗人也跟着“无端端地着急”,一代代走不出反叛、革命、刻意求新的魔咒,争先恐后地去推翻前辈诗人,迫不及待地花样翻新,开创新风。一会儿威廉斯、普拉斯、托马斯,一会儿拉金、策兰、布罗茨基,真是把写诗看得太重了,重于生活,也重于心灵,也因此把写诗变成了时尚,也变成了名利。与此相反,边围说得真好,“诗于我,是人生的种种修为方式之一种”。诗与人只能是精神层面的关系,超出于此,近于可耻。我以为,具有这样一种诗观,边围的诗值得信赖,值得细读,那纸上的心灵邂逅,不会被欺骗,也不会被那故弄玄虚的装饰绕得头晕眼花。
因此,当边围在诗中说“我想/我到达的地方比彼岸或者更重要”(《红树林》)的时候,我深以为然,并满怀敬意。
二、“二楼停着,在一楼之上”
读到边围的小诗《失眠夜》起首句“二楼停着,在一楼之上”的时候,我被这突兀的句子惊住了。二楼难道可以不在一楼之上吗?本来如此,天经地义,纯属常识,怎么就这样写出来了呢?且竟然不令人乏味!就此一句,实际上就可以见出边围在诗艺上的用心。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诗歌的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而是一种受到阻碍、遭到扭曲的语言,其能指并不指向所指,甚至只具备能指的意义。当我们按照日常语言来思考这句诗的能指背后的所指意义时,显然是跨出了诗歌的大门之外。诗人以陌生化的表述,将二楼定格在空中,以此暗示失眠者的意绪。“一楼之上”,传达出离开大地的悬浮之感,“停着”带来的不仅是静态的停止现状,还有从静到动的逆向联想,更有“失眠者”对这象征之物的反反复复的打量。而此句对熟视无睹的事物的凸显,也强化了读者对二楼的好奇与探求心理。简单的一句营造了丰富的诗意,这便是技艺。常言道,技艺是对诗人真诚度的考验,这是我信任、喜欢边围诗歌的又一个原因。
当然,这句诗惊人的原因还在于边围选取的视角十分独特。很多时候,他敏锐的触觉总是驻足于霎那之时、毫微之间,并于此打开或创造一个诗意缤纷的大千世界。诗人布莱克曾写道:“一粒沙子里有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有一个天堂。”边围似乎不是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里看沙、看花,而是在沙子和花的世界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个时空,因此他带来了那么多精致的意象,那么多细腻的体悟。看看这些诗题,就会令人着迷:《意外的小雪》《小住》《小游》《小旅店》等等,还有《关于梯子》《老书》……风花雪月与四季更替乃至粉末琐屑大约古今中外的诗人都曾写过,而一个人长久地专注于这样的微观世界,却可以算得上特立独行了。
单从标题看,边围似乎沉溺于咏物写景、即时歌咏,或以小见大、沉思远寄,或触景生情、感时伤怀,大约脱不了咏物之诗的常见写法。但若如此看待边围作品,未免先入为主了。“小”世界里的边围腾挪自如,无边无围,他可以古典地讽讬、兴寄,也能够现代地冥想、独语。他有时托物抒怀,有时又专意于诗趣。他的“小”不是时空的“小”,而是角度的小,一种与众不同的小,精致的小。例如《小店》:
一人,一狗,一藤椅/一日相守。∥一群苍蝇来了又走/一杯青茶热了再凉/一时也无话……
这现代乡村的小店在边围的笔下古风盎然,生活平静,但生机勃勃,时光漫长,而趣致不减。小偷也可爱,“捡些故事充饥”,店主(或他人)和善,不捉打小偷,却笑着说“一边去”。顿时,边围笔下的小店如世外桃源般地令人想往。《小店》虽小,却有着圆融、开阔的诗意想象空间。又如《小街》,也是在精致的构图中,工笔呈现小街的宁静、闲适。纤细的文字如处子的手在深夜拨动心弦,“不必轻跳,也就慢慢踱过,那素净的砖石,才最好!∥无人在半道歇脚,仅洋槐,隔三岔五地垂立于门边,似在把守旧日遗失的秘密。……”轻轻吟哦,如在小街漫步,沉浸其中,一念既起,万念俱息。边围即便在写大气象的时候,也还是着眼于小,着眼于精致。例如那首《宁夏之秋》,是对秋日宁夏风光的大写意。但诗歌起笔便写:
“树的沉默是世袭的”,真是神来之笔,多美的树啊,古老又古典,高贵又沉默,动人心魄!而“贺兰山在风中,翻阅它的晚年,此时,更像一个受惊的婴儿一样瞪大眼睛”一句,想象奇特,富于张力。古老而雄阔的贺兰山,在诗人笔下居然有如小小的婴儿,这也正合诗人一贯的审美风格和趣味。
边围的诗,在结构上也表现出“小”的精致。诗歌推进的过程中,诗人总会设计许多微妙的节奏变化,诗趣跳跃闪动,读之心神随之波动起伏。短诗《记于小寨》仅仅六句,起承转合,自然而然,却又隐藏着作者的苦心经营。“谁知,这纷扰的天桥上,也曾预演了多少迤逦情事”起句,“谁知”发端,有神秘之感,“纷扰”与“迤逦情事”构成张力,因无人知晓,使得这“情事”带上了个人化的神秘。但紧承的一句,“只是都抵不过流光”,诗歌很快摆脱个人化,迅速切入了“时光无情”的主题。接下来诗歌的意象类型发生突变,“勇士”出场,而“勇士”又因“天真”的“轻信”埋下悲剧的隐忧,“竟忘了”在语义上再次转折,尾句收合,又回到时光主题。小诗一共六行,三次转换,层层推进。而为了减弱转折带来的顿挫之感,作者两次采用跨行法(“还真有”、“竟忘了”),转折之中亦有行云流水之感。这种精心的布局之法在很多诗中都有体现。而作为一种技巧,这种转折、层递在诗节中也被广泛运用,细腻、出人意料,总是带来阅读的惊喜:
他们都想给生活化妆/而我只是美丽的小丑。——《小叛逆》
落叶透着芬芳/已不比往年殷勤/但翩翩摇曳时/分明多出几分媚态。——《吉日》
旁骛之心埋在昨日垒砌的沙丘里了/它也曾豪情过,只是我们更纯情——《淘气的日子》
一场小雨匆匆赶来,也未能/吵醒一次酣眠。——《四月》
空谷里,余音本再无去处/却偏偏灵动于古岩间。——《听笛》
“依稀就要去邂逅古道,恰逢了山岚/也不知哑柏参悟得透还是不透。”——《(游山》
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转折、跳跃,使得小诗起伏不平,摇曳生姿,有智趣,亦有情趣。
当然,“小”的审美、或“小”的艺术构筑了边围诗歌风格的一个向度的同时,也导致了边围诗歌在情趣、意境上不由自主的古典趋向。西安,这座哪怕初萌的嫩草也带着历史锈迹的城市,正是边围生活和工作的所在,他不免常常受到这古老气息的熏染,带着古人的悠然游走在古老的建筑之间,不经意便流露出那恬淡、闲适的古风来。他的那首《春夜,半醉而作》,半醉之后踏月游山,虽有“一同荒废这诡魅的梦境”现代人的“颓废”之感,但细细读来,也有着“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的古典气息。前文所举的《小店》、《小街》都是此类作品,而在边围的诗歌中,这类诗也可以随手拈来,例如:《晨起作》、《春山》、《冬日》、《郊野》、《春游半日》、《美好的一天》等。古典诗境的承继与借鉴,是新诗写作的冒险,因为古典太强大、太深广,诗人无法驾驭则会淹没自我,从而导致新诗写作的合法性的丧失。然而,古典同时也是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新诗早期对古典的拒绝,实则是不自信的非理性行为。当然,真正的拒绝是不可能的,正如叶维廉在《东西方文学“模子”的应用》中所说“下意识中传统的美感范畴仍然左右着他(诗人)对于外来‘模子(包括形式、题材、思想)的取舍”。时至今日,新诗身份得以确认之后,认祖归宗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传统之根基,喧嚣的新诗是无法“宁静以致远”的。这里,边围的创作,有意无意地又涉及了当代诗歌路线的重大问题,不过,虽有实绩,但非成败还不能匆作定论,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三、“如此崇尚快乐,这很浅薄吗?”
关于边围的诗,按照文学史惯常的思维方式,一定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边围的诗有逃避苦难的倾向,有纵情逸乐的倾向,有颓废自适的倾向;而少有时代担当的精神,少有教化众生的功能,少有讽世颂德的激情。在这政治热情饱满、功业之心昂扬的改革(或亟需改革)的时代,在这所谓多元化、实则无序的时代,这样的诗,恐怕不仅会受到主流群体的批判或漠视,也可能会遭遇边缘诗人暗暗的不屑。这一点,我想边围也有一定的现实体验,在几次电话交流中,我隐约感到诗人深心里的忧虑。他写有一首《快乐之诗》,既坚定,又有疑惑,第四节写道:
是的,我拈花的手指已无法自控,/我放电的眼睛也非全然空洞。/“如此崇尚快乐,这很浅薄吗?”
末句的一问,似乎正是对于“快乐”诗歌的价值追问,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乎诗歌路线的大问题。而这个问题既是老的也是新的,诗人柏桦曾多次谈到(他称之为“逸乐”之诗),在讲授“新诗的民族性”的时候,他说,中国诗歌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担当的传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金戈铁马、气吞山河如虎的传统,是屈原的、杜甫、陆游的传统,一个是风花雪月、园林散步、感叹生死的传统,白居易、李煜、宋徽宗的传统,这两种传统一重一轻,如同鸟儿的两只翅膀,不可偏废。但是,在文学史中,特别是五四现代性以来,大家只看到了屈原、只看到了白居易诗歌中的“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批判现实的传统,而轻逸的传统、白居易以歌诗琴酒为志业、“朝廷雇我做闲人”的逸乐传统遭到了严重的遮蔽。这两个传统原本是并存于文学史或古代文化中的,比如孔子有道德良心的一面,也有“割不正不食”的一面,但是人们却只重视评判性的传统及批判性的作品,这真是有悖于历史常理。(参见柏桦《东风·西风——中国现代诗歌专题研究》第三讲授课录像)。与柏桦先生相呼应的是著名学者江弱水的论述。他在《水绘仙侣》的序言中说:
面对大历史不断的天崩地裂,后知后觉的我们,必然认定那些“精巧化其生活艺术”、那些“美化文学”的行为,纯属错误,甚至罪孽。逻辑的推论也就是,当我们的好日子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把日子过好——
这唯一的哲学令我羞愧。
在道德律的文学政治中,
“一切逸乐的笑的可能和美的可能”都被排除了,剩下的只有道德的、批判的以及否决“非关政治”的旨趣了。在这样的认知语境中,自由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道德律令将排斥一切其他的可能性,包括逸乐、颓废、甚至单纯的爱情。就此而言,我深深敬佩边围在自己的诗歌“小”园地里的坚守,或许,正如前文所述,他所坚守的正是另一种传统——轻逸而快乐的传统,这同样是鸟儿翩翩飞来的一只翅膀。
江弱水评价柏桦先生的文字说,“柏桦的文字、精确、暧昧、流动着诱惑,属于不厌精细的‘养小类型。”这“养小”一词的创造性借用真是巧妙绝伦,形象地画出了柏桦诗歌中的人间烟火以及诗歌遣词造句的洁癖。“养小”一说出自于《孟子·告子上》:“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孟子好大义,小大对立,自然看重大,要养浩然之气,而饮食之人的“养小”也就不瞧在眼里了。但是,到了清代,深谙医术的顾仲编著了一本饮食著作,取名日《养小录》,并在序中,援引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语以证“养小”之合理。可见“养小”一词的贬义已经弱化了,并且逐渐衍生出精致、逸乐的引申义。如今江弱水用它来描述一种风格,一种快乐、精致的、甚至颓废的文学创作,倒是十分贴切了,而这于边围诗歌“小”的审美倾向也是那么契合。两年来,我一直在不断地在论坛跟读边围的诗,发自心底喜欢,但恕我愚鲁,很难言传他诗歌内蕴的美。我想,词穷之际,用“养小之诗,逸乐之风”来描述边围的诗风、并命名这篇短论,应该不至于冒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