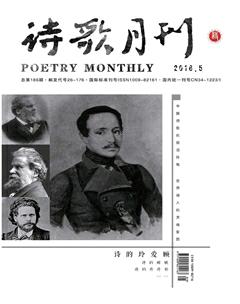苏黎 白鹤林 宋尾

苏黎,女,甘肃山丹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中国诗歌》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有散文集《一滴滋润》,诗集《苏黎诗集》《月光谣》等。作品入选《中国年度最佳诗歌》《中国年度诗歌精选》等多种选本。参加过诗刊社第24届青春诗会。
白鹤林,本名唐瑞兵,1973年生,四川蓬溪人。现为绵阳市文化馆创作编辑。1993年开始发表作品。有诗歌收录国内数十种选本,及译介到外国。著有诗集《车行途中》等多部。曾获首届四川十大青年诗人、全国鲁藜诗歌奖诗集类一等奖等多种奖项。
宋尾,1973年生于湖北天门,现居重庆。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
主持人语:
苏黎的诗让读者听到了“边塞诗”的遥远回声。陈旧的烽燧,酥油灯花,倾倒出月光的银壶,石缝间的穿行的蜥蜴,以及那里孤独的人,仿佛都替天空承担了些许份量。她的笔下不单有独特的风物景致,更难能可贵的是有心与心的砥砺。
白鹤林以简洁取胜,但往往有巧妙的并置。并置之法可打破机械的逻辑,有偈语之智,但弄巧成拙者往往失之干生硬、无厘头。可喜的是白鹤林手法圆熟,如《爱豹的少年》堪称代表作。
“那些荒芜的雨滴/在夜里明亮极了”。读宋尾的诗,时常有眼前一亮之感。他专注干对日常事物乃至无用之物的省察,有意规避老套的经验,带给我们的是令人惊奇的陌生感,恍如听到一个隐身人突然开口道出我们的悲欣。还是借用他的诗来说吧:“火车要穿过的桥梁和隧道/是固定的/但对旅客来说/无论拥有多少经验/都是盲目的”。
——余笑忠
祁连山下(组诗) 苏黎
焉支松
别的松树,都是把根扎进泥土里
一棵紧挨着一棵,长成林,长成森
根在地下相握,手在空中相携
而这棵焉支松,它与众不同
它独独把根扎在石头缝里
把头伸进天堂
它站在二千八百米高的山崖上
肯定是为了扯下一云朵的衣角
抑或是为了收敛更多的光芒
它挺拔而苍翠
它把孤独的肩膀,留给飞鸟小憩
它把空旷的胸怀,留给过路的风
天高云淡的日子里
它就放眼,和南面的祁连雪山
遥遥相望
在寂静的夜晚
它就把清澈的月光和星辰
邀进自己的年轮里流转
长城
风吹草波,高高的草穗上停着一只薄翅膀蝴蝶
请在我的铁匠铺里钳出那块夕阳;请给你走破了的马蹄
钉上铁掌。牧羊老人掴着毡袄在一岸头上斜躺
二坝渠的浑水里漂着一只青羊
尽管皮车的刮木响得揪住了秋风的耳朵
尽管最后那块夕光被谁扯起来揉皱揣进了胸膛
尽管黄昏这匹高头大马嘶鸣着一路跑来
那时的车队沿着长城
那时的车队穿过了城墙的一个豁口;那时的车队走进
了城墙
那时,一只蹲在城墙上的猫头鹰——两盏添满时间的
马灯
在风中,摇摇晃晃,把谁的骨头里的一声寒光照亮
秋日意象
一只花喜鹊,围着一座古堡
飞起飞落,仿佛一只手翻着历书
是要选一个黄道吉日:嫁女
旁侧,是一匹没人牵走的黑骡子
眯眼,打盹,偶尔一个激灵
拾蹄,就像打开了一扇门扉
风把干枯的玉米叶子,吹得
哗啦啦响,一直在响
雨水沤黑了的葵杆,站着整齐的列队
半块月亮:一把
银壶,倾斜着,倒出月光
也倒出一声声秋虫的忧伤
峡口古道
古道上有一只
畦哇叫乌鸦的女巫,尖尖的红喙
好像她举于额头拜谒焚燃的香炷
渐入山谷的是一阵皮车刮木声声
还有间隙的马嘶
还有钉满铁钉的大轱辘
给我岬角;给我药草;给我
露出棉絮,放在草垛上的
一双手套
一只挣脱铁绳的狗,舔着泉水
穹窿之下,半轮夕阳
立于地平线的拱门:
只一瞬间啊,我的心
似乎在里面,已
住了多年
山丹大佛寺
始建于北魏时期的山丹大佛寺
几经劫难,几经修葺
如今,九层木制楼阁,飞檐翘角
巍然屹立
坐西望东,依山而立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见的
是四角上的风铃声声
围着楼阁诵经的是一群鸽子
向北一公里,是祁家店水库
里面蓝天渡步,白云凫水
一些黑色的水鸟,就像小小的岛屿
依水的山上驻扎的是旧时光
向西,苍茫的戈壁上
落日,是一扇朱红漆门
走进去的是一队西行的骆驼
走出来的是一行南飞的大雁
向南,数百公里之外
就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
祁连山上的雪莲花——
是佛放逐南山下的座骑
星星,是串串蹄音
银河,是一声马嘶
月亮,是饮马的泉
太阳,是拴马桩
祁连山下
暮色下,一个尧熬尔人
系好了牛的鼻系后
又扣牢了羊圈的栅门
搅杆。奶桶
声声黑而沉闷的
狗嘤
月牙,镶在天窗上
星星,是一群唧唧喳喳的小鸟
夜色,迈着沙沙的脚步
酥油灯花下,对饮奶茶
你扑闪着的黑眼睛
是丛林中的一对鹿鸣
梨园口
我惊羡于山顶上那些石头的
怪异,我惊羡于
一只蜥蜴在石缝间的穿行速度
梭梭草,一如
阳光的一印印蹄花,长久地
徘徊于这片戈壁腹地
一个牧羊的人
倒提着自己的心事
消隐于那边的一条山谷
一只脱了毛的秃鹫
落到自己的影子上
默默地垂思
远处,白雪皑皑的祁连山
仿佛是立于远古时期的陶器
泛着瓷实的光芒
北麓
两头斜站着的牛
相互舔舐。山,也弯过了脖子
几个拾地耳的妇女
石头一样,在坳里撅着高高的屁股
古硖口驿道,一块“天现鹿羊”的岩画
像是谁打开了一扇小小的历史的窗口
谷底突然兴起的一股旋风
卷起了尘土,腾空而去
半山腰,一匹低头沉思的马
被夕光拓在了一个岩壁上
冬日雪源
一声马嘶
扯断了长路上的叮嘱
一声鸟鸣
顿觉天空的渺远
我在雪源,我在一处高地瞭望
冬阳编织着的光圈——
在雪源上幻化出斑斓的色彩
西山顶上
两座陈旧的烽燧,就像两个老人
隔世地相望
我在低头沉思
是一次情感与情感的触碰
是一次心与心的砥砺
我的双眼,俩盏盛满清澈的酒盅
对饮着——
觥筹交错
是寂静和旷野在干杯
是时光扑闪了一下,是一束泪花
灼疼了的伤痕
清晨:十四行
一群小鸟,草地的纽扣
拒绝张望
远处的雪山,摇曳了一夜的灯盏
拒绝说出
河流的波纹,多少个嘴唇翕动
坐在一个小山冈上
听不远处村庄里的狗叫、牛哞,和一声
长长的
马嘶
打开栅栏
云朵的羊群飞翔
而后,我替天空承担了
些许份量
白鹤林的诗 白鹤林
叶子
夜色早早降。陌生人
向我打听一条陌生的街
他说:街上出售一种叶子
而在另一条街上,城市的公交站台
挤满他乡的雨滴
八月在草原
天黑后,一只狗在车库里奔跑
速度中带着铃音。嗖的一声,消失
我忽然想起,八月在草原
那赛马带着彪悍的蒙古人,只一下
就从数码相机里跑远
想着没什么联系的两件事
我慢慢爬上曲折的六楼
午夜
饮酒之后,有人开启喉咙
解放满腹的火苗
天干物燥,寒风如阵阵官兵
搜刮午夜街区
在那流光深处,满城物欲
争相展露富足的腰身
夜行人
深冬之风催促夜行人
我穿过一日将尽的城市,和它
火热的斗争
在那幽暗的山峦与江水之间
黄金日渐稀少
思想何其珍贵
爱豹的少年
一个生病的人是谦逊的
正如沮丧
通常与感激比邻
这是否是说——
药,改变了我们内心的境遇?
但一个爱豹的少年,他能否
向自己的混沌之爱
奉献尚未腐败的肉身?
金箔
一整天,两个人为了一张纸
挥汗如雨
在木锤和墩子之间
只一口气,另一个人就把黄金
吹上了天
思想者
一辆又一辆胃胀的
公交车,奔跑在消化不良的
城市街道上
在每一个肥胖的清晨
“凡专注于思想者,
不宜空荡,适于狭隘。”
诗人
一场初春的雨,下在绵州城
像下在每一处的异地——
下在图宾根郊区。下在塞纳河畔
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
下在希拉穆仁大草原
或者,贵州甲乙村
让我想起,去年见面
而今还乡的诗人
风景
房间开着窗,这理所当然
但你
给它一幅铁栅栏
风景具有危险性?
飓风
江边的“海谷阳光”前
停一辆“风摩托”
送来一车白萝卜
我猜是——
“飓风”牌摩托,被经年的河风
吹掉一个字
最小的阴影
一只八哥
在广场草坪的阴影里
散步
我们坐在车上晒太阳
一只八哥
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它和广场、草坪、阴影有关系
和午后的阳光有关系
并与车保持着间接的关系
它一身的黑,像晴朗午后
一片最小的阴影
火车
火车旧了
拉着一车皮生锈的信
向彼岸奔跑
火车掉头开进梦里
我在七十岁前夜,忽然醒来
抖落一身的铁。或繁星
白夜
一池喷泉
在白夜的舞台,不息奔涌
耳朵多寂寞
幽暗草丛里,灯盏很零碎
接近银子的失明
我独坐桂花树下,听石头
排练歌剧
春闺
昨夜的狂风,像个粗蛮的酒鬼
猛推猛撞万家窗门
清展醒来,世界却早已是风平浪静
温婉山河秀气如春闺
那昨夜的酒鬼,想必已在后院呼呼然大睡
只愿长醉不常醒
一个来自草原的男人
这一天,我都在想
一个来自草原的男人
他个高,体壮,有满腹的荒芜
还戴一副黑边眼镜
这一天,我都在写
一篇与草原和绵州有关的博客
回忆昨夜的雪花、丰谷
以及,本地土特产浇灌出的
水银般的俗语。或歌声
这一天,一位诗人
他驾乘卫星导航的黑色马车
返回北方的旅程
诗集
(致海子)
晚间你的纪念诗歌朗诵会,在下午
我就于心中默默完成
或预演了一遍
我为你做了一本薄薄的诗集
一本纯手工制作的诗集
它仅由十九次死亡,和四个爱情构成
一本最小的《海子诗选》
在这个春天,只发行了三本
一本寄给查湾的村庄
一本赠予你二十年前的友人
一本留给我一一
你祝福过的每一个陌生人
台词
昨晚,他们才在车站依依惜别
仿佛不可知的旅程
会如黑夜漫长,不再相遇
今夜,他们已在一起沉默。或哭泣
用彼此的孤独
安慰百感交集的肉身
“那就顺着风吹的方向,水流的方向
走完我的人生之旅吧!”
很烂的电视剧里,偶尔也有
精辟得让你意外的台词
而且它往往出自既可恨又可笑的
配角之口
落叶与窗户
每一首诗,我都写两遍
一遍写在秋之落叶上
一遍写在幽暗花园的窗户
前者是未完成的便笺本
后者是所有失败之书的勘误表
宋尾的诗 宋尾
幼猫
它匍匐在一个烟摊前
它不会了解对面
菜园坝火车站里汇聚了什么
它也不关心
经过它的每个人
把这路上的一切
加起来,也不如那个小纸团
它盯着它,拨弄它
它在寻找那种被我们遗失许久的
从庸常事物里获得乐趣的技能
我像其他乘客一样登上大巴
它则会一直留在
被我们称作无用的事物之上
夜宿李庄
我喜欢这镇子
江水使它复活了。
黄昏后,我从当地人
之间穿过,如隐身人。
深夜,我从宾馆
溜出来,在黑黢黢的
屋檐上飞行,我
越过野猫,找到了
被他们省略的东西。
那些荒芜的雨滴
在夜里明亮极了。
夏夜的树
它们站在窗外
就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矛盾
我们只拥有
它的形象而无其他
我们欢欣时,它没有情绪
我们相聚时它们孤立
它们也是子女
是某种父辈
是故乡相信息的收集者
我们睡去,它站着
我们死去,它活着
在根茎上奔跑时
它也并不需要被谁看见
一天
乘坐地铁回家,
我没见到庞德,但见到了
他写的花瓣,还有“黝黑的枝条”。
那些脸孔,你知道
几乎一模一样的脸孔。
从解放碑走过,所有人
除开鞋子、衣袜,那里面包裹的内容
都是一样的。
我是说,我回到家打开电脑,
就像清早进到办公室一样。
我一直试图让自己看上去
像一个人,而非地铁里
某种黝黑的枝条,可事实
并不是这样。
我总是在黄昏
重复这些:
把上午再过一遍。
浏览新闻,图片,那些被我
疏漏的一些故事,以及
故事与故事之间的隙缝。
我会泡一壶茶,抽烟,
烟雾将从手边
飘出去,它们如此之轻。
晚餐后我在卫生间
让水流一遍遍冲刷着我,
但并不能使我变得干净。
只是这次,水声里我听到了
一千个人呼唤我的名字。
关掉水阀,那些声音戛然而止。
我暴露在裸体之外,
镜子里镶满水珠,湿淋淋的反光,
并没有我。
火车上的弟弟
下午三点,T258次列车
将他从菜园坝送走
他提着重重的包裹
满是与前程毫无关系的东西
却必须带上它们
就像回家
也不是他的目的
结婚或离婚
都是如此
沿路上
火车要穿过的桥梁和隧道
是固定的
但对旅客来说
无论拥有多少经验
都是盲目的
他屡次离开座位
去连接处吸烟
他想了一些事情
这几乎是肯定的
就像他从窗外
见到的一些图案
毫无意义,这也是肯定的
深夜,他被某些动静惊醒
暂时忘记了
之前因为焦虑
和思考过度带来的
一个转瞬即逝的噩梦
想起一位死去的朋友
活着更像
一件非自然的
强制性任务
要呼吸
要获取更多
欲望,一个轻巧的词
就囊括了一切
但不包含
对死的恐惧
它天天都在
死亡其实是这么一回事儿
当你不在了
你就在那儿了
纪念
这几个月
我走了一些
不知名的峡谷
到过几处山顶
以及一条废弃的古道
每次,我都带回
一些植物
种在阳台上
它们大多活了下来
分别长出死亡,梦境
和锈蚀的脸
我发现
它们的枝条
并不一定是绿色
与黄沙子谈话时所见
我们谈论诗的时候
三只斑鸠在窗前尖声鸣叫
它们天天如此
整个春天
这些语言不为我知晓
一如诗的无知
它们沉醉于
这尖锐的交谈
它们急切表达
每个偶然
它们如此热爱自己的天赋
爱着自己的命运
阳台外,一颗树
伸臂托起它们和它们的聒噪
那种姿态像是
某种被我遗失的想象
这颗皂角树,高大,肃穆
树冠淹过了房顶
却这么寂静
摄影家的角度
在我们眷念的地方
他不着一字
暗室里
他从显影液掏出
黑白的我们
还有屋顶那只老猫
它背后的小叶榕
还有你我
谈话的声音
以及它所能抵达的
最远处
阴天
重庆的阴天有一种
隐晦的压力
在此刻
它逼迫我们
预备迎接尚不存在的雨丝
而我们心底的欲望
被挤压出来
带着迟钝的反光
滞留在脸上
布告
走廊和围墙上
他无处不在。
这个人让我心悸
不是因为他
犯了这么大的事;
而是在布告上
我找到了遗失多年的
那张小学毕业照
那是我第一回
看见自己屈辱时
是什么样子。
每次路过他的画像
我总会凝视
他面庞背后的深渊
那里,一条蛔虫
幸运地爬出来
穿上新衣裳;
而另一条
一直留在粪的沟壑里。
入夜后
你必然也有
类似困惑:
某种你熟悉的事物
会突然变得陌生
就像晚上的城市
在眼睛里
多少有些变形
而你并不清楚
这种误差是如何产生的
就像我楼上的那个男人
并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他精明的妻子
并不比邻居
更了解自己的丈夫
很多年,很多事
都是这样
少年时,我
努力想要摸寻到
昼与夜之间的
那道分际
现在我知道了
很多事都是如此
往往并没一个
明确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