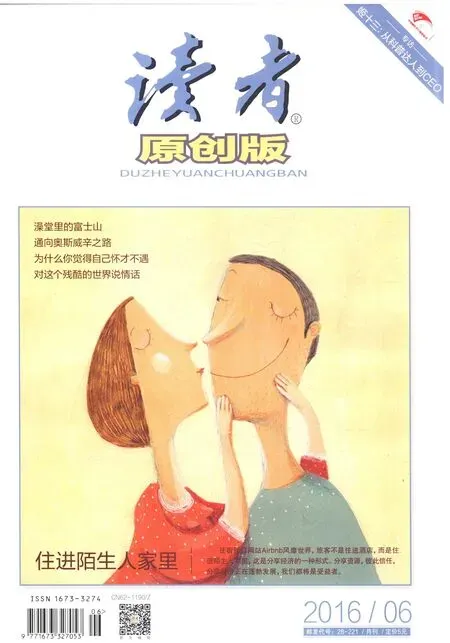少女的狂奔
文_白云苍狗
少女的狂奔
文_白云苍狗

小时候,天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针管子,那种打针的玻璃注射器让我向往到痴迷。
那个时候,我酷爱用一根长长的自行车气门芯、一个铁夹子和一个取掉圆珠的圆珠笔头做水枪。方法是把气门芯的一头打上一个死结,另外一头用一个吸满水的注射器头对准,堵上,然后使劲把注射器里的水推到气门芯里,于是气门芯就咕的一声胖了一截,像蛇吞进了整个的青蛙。随后我赶紧用铁夹子把气门芯鼓起那部分的前面夹住,不让它松气,然后把注射器拔下来,吸了水再推进去,这样反复几次,气门芯就整个鼓了起来,最后把圆珠笔头安上,这样一个水枪就做成了。
控制的机关是铁夹子,选准目标后,我就把水枪对准对方,松开铁夹子,水就喷了出去。要是我稍微贪心一点儿,最多30秒钟,水枪就瘪了,就得重新装水了。小时候,快乐来得简单,30秒的快乐让我很满足,而且乐此不疲。
那个时候针管子很少,即使我有两个表姨当护士,我依旧没有机会得到这个宝贝,只好到处搜集眼药水瓶子充当给气门芯充水的工具。但是眼药水瓶子实在用得不爽,一是它开口不光滑,跟气门芯对不严实;另外一个问题是它装水装得太少,这对着急去玩的我来说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于是,针管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最大的奢望,做梦都想拥有一个。
那个时候我脸皮薄,又被父母教育得“坚贞不屈”,对于想要的东西,最好是看都不要看,不能让别人看出一点儿羡慕、垂涎、贪婪、渴求之心,更不能张嘴去要。
于是,就算我有两个当护士的表姨,有在注射器厂工作的三婶,我最好的小伙伴他爸是注射器厂厂长,只要我开口,或者有一点儿贼心的话,这不过是唾手可得的东西。
但是,我始终很有骨气,就算再想要,也没跟他们开过口。
街上有个老光棍,跟他母亲一起过日子,他母亲已经耳聋眼花背驼了,有六七十岁了吧,全靠儿子从淮河挑水卖水为生。他家穷得叮当响,儿子又长得贼眉鼠眼一副猥琐相,所以一直没有老婆。那时没有自来水,注射器厂这种需要大量用水的单位就雇他来专门挑水,于是,我常常看到他进出注射器厂大门。
他家住在一个七拐八弯的小巷子里,隔壁住的是我爸公司的一个同事,我和他家儿子磊磊是小伙伴,有时候一起玩。他家对门是一户姓万的人家,这家有个女儿叫敏儿。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案件,一个小学老师强奸了多名女学生,美丽动人的敏儿是其中我唯一认识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强奸,但是我和同学都多次专门偷偷地去看敏儿,想搞清楚被大人们说得神神秘秘、无限惋惜的强奸后是什么样子。看了之后,我们都没有看出来什么区别,但是都装出看出来什么的样子,说:“哦,被强奸后就这个样子啊!”然后各自回家。但是我再走过敏儿家门前那条小路的时候,总会本能地避开她家的那边,绕一个弧形过去——心里觉得强奸是个不好的事情,要离远点儿。
放学路上,小孩子总是喜欢到处乱窜,专门走小路,我也不例外。一天傍晚,我从主干道拐到一个岔街上的时候,遇到了老光棍,他满脸堆笑地问我:“想不想要针管子啊?我家有,跟我去拿吧!”
我听到“针管子”三个字,人就痴了。我本来没打算走磊磊、敏儿家的那条小巷子的,但是听了老光棍的话后,我就乖乖地跟着他走了。这一走,就走了差不多500米,一直跟着他进了他家的大门。
一进门,他转身就把大门插上了。我突然害怕起来,转身就要走,但是显然已经无法脱身了,他拖住我就要把我往屋里拽,挣扎中,我看到破落的院子里,两间破房子,对面是一个老太太佝偻着坐在灶台前烧火的背影。
没有等我喊出来,他立刻放下了我。我赶紧就往门口跑,拔掉门闩跑了出去,胯下被他的胳膊勒得很疼。我没有立刻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惊魂未定。他居然跟了出来,手上拿了一个5毫升的玻璃注射器,说:“给你!”我居然真的下意识地接了过来,放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他进去之后把门又插上了。两分钟后,我举起右手,把注射器狠狠地摔在了那扇破旧的木门上,摔得粉碎。
我想了那么久的宝贝,从此再也没有让我牵挂过。
天快黑了,我飞奔回家,又怕又气,还在喘,没有人发现我和往常有什么区别,我也只字未提。后来我和好朋友娟娟隐隐提起那个老光棍是坏蛋,千万不要理他的时候,她暧昧地问我:“人家怎么坏了,骗过你?”
我看着她的一脸坏笑,才意识到,这个事情今后是死都不能再说出半个字了,要不然,我也会成为敏儿那样的女孩儿了。
若干年后,我当了护士,有一次下班前刷洗注射器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有个女孩子曾为了一个5毫升的注射器,差点羊入虎口,万劫不复。
图/丛 威
我说:“针管子我不要了,让我走!”他突然狞笑着喃喃自语:“让我抱抱你,让我抱抱你……”他一下子把胳膊伸到我的两腿之间,用小臂把我举了起来,我的脸就和他平行了。我看着他眯成一条缝的眼,气极了,压低声音说:“快放下我,快点让我出去,要不然我喊磊磊家人了……”他并没有把我放下来的意思,还企图往里面走,我狂抓乱踢,声音更大了:“我真的喊了,磊磊爸和我爸是一个单位的,他们家人听到了一定会来救我的!磊磊……”
——评长篇历史小说《白云苍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