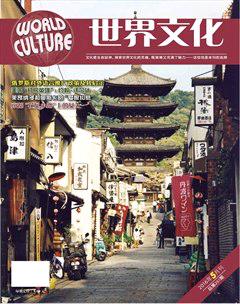耶稣的女门徒:抹大拉的马利亚
任东升+郑帆
《圣经》“福音书”里记载的女性人物不多,按照地位和重要性,第一位是圣灵感孕、生育耶稣、见证耶稣受难承受煎熬的“圣母”马利亚,第二位是在约旦河给耶稣施洗的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第三位应该是耶稣的女追随者抹大拉的马利亚。《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她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马利亚看见,却是不信。从耶稣复活后第一个向她显现,便可窥得抹大拉的马利亚宗教地位的特殊性。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圣经》“福音书”里被提及的次数之多,仅次于耶稣的母亲。饶有趣味的是,她的每次“出场”几乎都有耶稣“在场”,由于抹大拉的马利亚与耶稣较为接近甚至“亲密”的关系,手握画笔的艺术家们对其做了多元的解读,这些解读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圣经》文本对其进行了艺术想象,由此,成就了“抹大拉的马利亚”主题系列画作。
悔罪至深、忏悔至诚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圣经》“福音书”对抹大拉的马利亚第一次“出场”的记载是在加利利,她遇见了耶稣,耶稣当场从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鬼。此后她加入了耶稣门徒的行列,无论耶稣往哪里去,她都跟随着。最后随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耶稣受难时,所有男性门徒都不见了踪影,她仍守在十字架之下,并且观看耶稣的安葬,见证了复活前后的事件。然而,长久以来,抹大拉的马利亚一直以一个妓女的形象出现在基督教的传说中:作为基督教意义上的罪人,她向耶稣忏悔,耶稣接受了她的忏悔。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与那个曾给耶稣洗脚的妓女有关。“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忏悔”这一情节,历来是众多画家所钟爱的素材,暂不论这个情节的真伪,抹大拉的马利亚在不同时代,不同画家笔下,神色姿态各异,一举一动之间皆是内心世界的展露。

意大利威尼斯画派代表作家提香(约1490—1576)在1567年创作了《忏悔的抹大拉的马利亚》。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画家们用一幅幅画作表达着自己的信念: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神为中心,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这幅画中,提香将抹大拉的马利亚描绘成了一位“满眼泪水的妇人”。画中的她衣衫褴褛,长发披肩,遮住了前胸,她抬起头,仰望上苍,眼里噙满虔诚的泪水,右手放在胸前,口微微张开,似是在呼求着什么。画家的笔触圆润有力,笔下人物体态丰满,栩栩如生,观者似乎能感受到她的呼吸声。从画中的色彩上看,金黄色的头发、深棕色的背景、主人公白皙的肤色,色彩浓淡相宜,这些暖色与天空的灰蓝色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构图上,画面的左右两方并不对称,左侧厚重的岩石给人以迎面而来的压迫感,右面原野空旷辽阔,给人以重负已释,前途一片光明之感。画面右下角的骷髅上平摊着一本《圣经》,表明这一绘画素材与宗教题材的关联。女子的忏悔之泪、反差明显的色彩构图、浓烈的宗教氛围相得益彰,使主题更显得深沉凝重、刻骨铭心。此外,画面压倒一切的悲伤氛围,画面人物深切的呼求之态,以巨大的穿透力叩击着观者的心灵,令他们对这位女子产生一种不能抗拒的同情。正是这种独特的风格,深深地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人。
意大利的现实主义画家卡拉瓦乔(1571—1610)所创作的《忏悔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画框架,使观众仅从画面上根本看不出一丝宗教画的痕迹。画中的女子坐在一个矮凳上,矮凳旁还散放着一地珠宝,她神态宛若一个少女,两手向内交叠,头微微侧低,亚麻色长发散在一侧,露出白皙的脖颈,面容安详宁静,仿佛是在沉睡。画面中弥漫着悲伤的氛围,昏暗的背景里,少女双眼紧闭,独坐反思。观众仿佛能够听到她发自内心的忏悔与哽咽。这便是卡拉瓦乔将人物“平民化”的风格:色调朴素,勾勒含蓄,意味深远。

另一位代表画家是来自法国的拉图尔(1593—1652),他的有关“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个题材的画作现存有四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幅分别是《油灯前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镜前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因擅长表现夜里烛光下的人物,突出光线的作用,拉图尔又被称为“烛光画家”。《油灯前的抹大拉》一画中,抹大拉的马利亚在深夜独自坐在烛光前,上体微裸,两腿随意交叉,双足赤裸,一手撑着下巴,一手触摸着放在大腿上的头盖骨,微微颔首,凝视烛光,陷入沉思。《镜前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一画中,抹大拉的马利亚秀发披肩,端坐镜子前,头微微左倾,双手交叠,轻抚头盖骨,而她衣着端庄,长裙垂落地面。两幅画整体色调非常相似,深暗的背景,微弱的烛光,女主人公着连衣裙,上身乳白,下身枣红。在蜡烛的照射下,她犹如一尊雕像,轮廓清晰,安静凝重。可以观察到,抹大拉的马利亚神态祥和、内心静谧而虔诚。两幅画中都出现了头骨与烛光。二者寓意深刻,发人深思。头骨代表着肉体的生命终将化为白骨,暗示死亡的必然;而燃烧的蜡烛则代表基督的灵光和温暖将引导人们灵魂的方向,由此,烛火前忏悔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便成为弃暗投明的象征。
提香、卡拉瓦乔和拉图尔三位画家都处于文艺复兴时期前后,他们所创作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与以前的宗教画侧重点不同,他们的画作重点并不在于表达她的忏悔,而是表达文艺复兴时期对人体和人性的讴歌。因此,以上三位画家对于“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忏悔” 无意考究其情节的真伪,而意在通过描绘一个广为流传的情节,来表达对人性的尊重、对“知罪悔改”态度的深刻理解与弘扬。
抹大拉的马利亚与耶稣

抹大拉的马利亚可能并不是什么妓女,相反,她可能是耶稣在人世间最亲密的心灵伴侣之一,耶稣曾一对一地对她传讲福音,这是其他十二个门徒没有的待遇。她是《圣经》中第一个见到耶稣复活的人,这与传统上基督教认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是妓女的说法不相符。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真相似乎渐渐浮出水面,或可说,抹大拉的马利亚是未被正史记载的最得耶稣神髓的门徒,所有的误解可能只因为其不该生为女人罢了。《耶稣显圣》画中抹大拉的马利亚跪在复活的耶稣面前,她头披白色头巾,身穿素色衣裙,惊喜地仰望着复活后的耶稣,手下意识地向耶稣伸去,宛若一个见到许久未见到父亲的孩童。整幅画面的色彩相比以往的题材更加亮丽绚烂,似雨后乍晴,鲜亮夺目。
《不要触摸我》一画出自提香之手,整幅画以田园风光的氛围将主人公包围起来,抹大拉的马利亚见到复活后的耶稣,欣喜之余不由得把手伸向耶稣,而耶稣却拒绝了她的触碰,(据《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复活后对抹大拉的马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我们可判断为,耶稣可能仍处于一个过程中而不愿受到干扰)并高贵地抽回披风,这幅画便定格在这一瞬间。另一幅的题材也是取自“不要摸我”,从两幅画中女主人公的衣着、姿态、神色可以看出,抹大拉的马利亚对于耶稣是充满崇敬的,没有半分妓女的风尘之气。
抹大拉的马利亚与众人
“福音书”中记载抹大拉的马利亚用忏悔的泪水为耶稣洗脚,用密软的黑发来把脚擦干,有关这个情节的画作大概有四幅,现存最为清晰,但具体年代和作者已不可考。在这四幅图中,抹大拉的马利亚都是跪坐或匍匐于耶稣身前,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耶稣的脚,虔诚地为耶稣洗脚,她那浓密的长发被拨到一侧,垂落到耶稣的脚背上,虽然从画中无法看出抹大拉的马利亚究竟是不是用泪水为耶稣洗脚,但从她虔诚庄重的神色中我们仍可以感受到她那拳拳赤子之情,她的忏悔之泪想必也是温暖而热烈的。其中有三幅画中,耶稣周围有众门徒围绕,对于抹大拉的马利亚用泪水为耶稣洗脚一事,各门徒在注视的背后还有各自的思考,神情反应也各不相同。然而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抹大拉的马利亚丝毫没有紧张不安之感,面容一直安宁虔诚。透过这一幅幅画,抹大拉的马利亚对耶稣的忠诚与坚信表露无遗。
《耶稣受难》这幅画的作者和具体年代已不可考,画中的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抹大拉的马利亚紧抱着十字架跪坐在地上,仿佛依靠着耶稣一般久久不愿离开。我们可以看到,画面里只有两个女人,另一个女子便是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而耶稣其他的十二个门徒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有抹大拉的马利亚誓死追随,她一袭白衣,在灰蓝色背景的映衬下更显纯洁虔诚。天空由蓝变灰又向黑色过渡,在耶稣的头顶上一团黑色的漩涡开始出现,似是要将耶稣接走,而抹大拉的马利亚依然紧紧地拥着十字架,仿佛要追随耶稣一起离开。从以上的画作中,观者可以看出抹大拉的马利亚对耶稣的一片赤子之心,而耶稣复活后第一个向她显现也表现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基督教中的特殊地位,以往对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传统解读很可能是对她的“误读”,毕竟其他十二个男性门徒中没有一人能有此殊荣。

《圣经》记述,耶稣受难复活以后,显灵说:“无论在何处传道,都要宣扬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事迹。”塞?利奇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升天》形象地宣扬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图中的抹大拉的马利亚被众小天使环绕,手臂优雅地抬起,高贵圣洁,整个人驾着彩云腾空升起,画面中明亮的红色和绚丽的金色给整幅画增添了极大的动感。与以往的画作有所不同,《升天》中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已没有悲伤之感,相反,整幅画呈现出一种轻松明快的喜悦感。另一幅《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升天》已看不出以往的凝重氛围,相反,在湛蓝的天空的映衬之下,一群小天使簇拥着抹大拉的马利亚腾空而起,而女主人公面带微笑,双臂伸展,似是在拥抱。画中飘动的衣衫,女主人公优雅的姿态和美丽的面庞为这幅画增添了圣洁虔诚之感。
无论是被误解成一名妓女,用忏悔之泪为耶稣洗脚,还是身为最得耶稣教导神髓的女门徒,抹大拉的马利亚在画家的眼里无疑都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艺术形象。文艺复兴时期“忏悔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体现的是画家们对人性和人体的讴歌,洋溢着强烈的人文主义气息,而 “抹大拉的马利亚和耶稣”以及“抹大拉的马利亚和众人”则都在为这个虔诚的女子洗清罪名。最终这位耶稣忠诚的追随者在众天使的簇拥下升天,圣洁而美丽。在这个过程中的众多画作都在描绘着这个美丽的女子,她的一颦一笑也在牵动着一代代观众们的心。这就是大众阅读的影响力,它可以使抹大拉的马利亚成为一个妓女,也可以将其塑造成罪人,还可以将其塑造成一个虔诚的信徒。所有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不同的解读,抹大拉的马利亚更受关注,由此,抹大拉的马利亚作为艺术家的艺术源泉,成为一种文化资源,为艺术的发展释放着种种内在的潜能,丰富着艺术家人文主义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