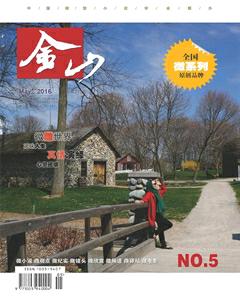玩的童年(外三篇)
顾坚
不久前在古运河畔散步,看见东关古渡牌楼前的小广场上有一帮孩子在打陀螺和滚铁环,感到十分亲切,让我想起了童年时光。
故乡在苏北兴化,那里的孩童把打陀螺叫做“打李逵”,如果哪个技巧好,陀螺久打(抽)不倒,便称之为“打不死的李逵”。李逵是古典名著《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以他的姓名称呼陀螺,可能是因其身躯粗夯结实,如同陀螺,而且勇猛无敌,久战不死,更符合陀螺游戏精神。李逵在家乡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就是兴化人,他笔下塑造的一百零八位江湖好汉如同亲戚一样常挂在大人孩子们的嘴边。
陀螺都是用树木削成的,大的可比成人拳头,小的高不盈寸,如胡萝卜头,纯粹根据材料规格和个人喜好制作。大有大的好处,抽起来威风,“叭叭”的脆响像开步枪,像放炮仗,而且斗李逵时容易把对方撞弹出去,不好的地方就是费力,抽的频率要快,适合身高力大的同学使用;小的好处便是抽打轻松,一鞭子抽下去能转好长时间而不倒,而且战斗时进退灵活,如同小兵张嘎这样的小英雄,瞅冷子袭击敌人两下,打不过马上转移开去。
我从小就擅长奇思异想,为了打李逵占上风,从陀螺的制作材料上打起了主意,居然想起用砖头。当时我才八岁,上二年级,下午学校放学后不回家,在教室檐廊的水泥地上磨制陀螺。一双稚嫩的小手要把半截青砖打磨成光溜精致的圆锥体,这是一项多么艰辛的大工程!但我没有畏惧,全心全意地磨制,每天都干到天黑。时隔四十年,我仍清楚地记得空无一人的庙宇改成的小学校里无比的寂静,薄暮中几十只蝙蝠在古庙驳蚀的挑檐下飞窜旋舞,我的小屁股坐麻了,我稚嫩的手指擦出了血珠,我听到了围墙外面母亲焦急寻唤我的乳名……四天后,终于大功告成。当我把呕心沥血磨制出来的作品捧宝似的拿到操场上亮相炫耀时,却很快如泄气的皮球一样,沮丧不已:砖质陀螺太沉了,重得抽不动,必须不停地抽打,转速还是上不来,而且太费布条——仅仅抽了几分钟,母亲用旧裤带为我做的鞭子便抽得丝丝缕缕的,好像年画上神仙爷爷手握的拂尘!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还很穷,不是所有喜欢滚铁环的孩子都能拥有一只铁匠打制的标准铁环的,不少孩子就想方设法使用其他材料做成圆环代替,如荆藤,竹蔑,粗铁丝。还有滚冬天用来捂手暖脚的铜炉盖子的。我们巷子里的马锁不小心把铜炉盖子滚进了小河里,他父亲在寒风中用罱泥的大罱子罱了半天才罱到了,回家拿鞋底把马锁的屁股打得青肿,上学的时候走路一瘸一拐的,可怜极了。保东挨打更有意思,他滚的是铜环,是悄悄把家里的马桶卸下一道底箍来,结果壮硕的母亲坐上去顿时迸裂,人一跤跌倒,满屋子的屎尿味。他父亲拿牛绳把他吊到树丫上打,鬼哭狼嚎的声音半个村子都听得见。
我们的童年,所有的玩具基本都是自己手工制做的。制做的过程就是寻找和发现的过程,也是锻炼大脑和培养动手能力的过程。我们的玩具跟工厂的流水线无关,跟塑料无关,跟电池无关……都是从自然中得来,百分百的“绿色产品”。我们玩烂泥巴巴,射纸火箭,斗铜板,拍(扇)火柴壳(纸匾,香烟壳,糖纸),打陀螺,滚铁环,弹玻璃球,跳白果,拿拇儿,格房子,叠罗汉,捉迷藏,打水仗……所有的游戏都是运动,都是比赛,都是战争的模拟。游戏锻炼了我们的身体,不断的输赢磨炼了我们的心理素质,集体活动培养了我们的团结协作精神,我们的游戏就是具有这样重要而美好的意义,这是单靠学校教育所不能达到和获得的。我们的童年很贫穷,我们的童年又很富裕,因为我们在游戏中长大,在伙伴中成长。童年是用来玩耍的,童年是用来发现和创造的,童年是用来自由和快乐的。这样的童年,才是真正金色的童年;有这样童年的孩子,才是真正幸福的!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了,孩子的玩具越来越多,游戏却越来越少。孩子越来越擅长伸手,却越来越不会动手了。孩子越来越孤独,却越来越不快乐了。戴眼镜的多了,“豆芽菜”和小胖墩多了,胆小自私的多了,在野外奔跑如鹿、会唱童谣的少了……这样的情形让我时常感到郁闷、担忧和恐慌。因此,当我无意间在东关古渡看到了儿时的经典游戏,亲切和振奋之情油然而生。我希望让孩子们回归到自由玩耍的童年,充满探索和创造的童年,在游戏之中懂得团结协作的童年,生机勃勃带有“野性”的童年……
斗铜板
小时候农村不少人家都藏有数量不等的铜板,比如“大清铜币”、“光绪元宝”、“十文”等,多为清代铸币。这些早就不流通的货币被老百姓当作压箱底的宝贝往下流传,往往也成了孩子们用来游戏的玩具。
斗铜板是孩子们最热衷玩的游戏之一。在泥地上画约一米见方的田字格,每个格子里标上1到10以内的四个数字(如:4,6,8,10),然后几个人站在离方格四五米远的一根划线后往田字格里投铜板,规定以投中最大数字格的人为输,其余都是胜者。输者付出的代价是“挨斩”。就是胜者轮流用自己铜板狠狠劈砸对方躺在格子里的铜板,直到把对应方格里规定的数字砸完为止。劈砸者把全身力气集中到膀臂上,扁薄的铜板刃面砸到对方铜板表面发出“叮叮”清脆的声音;若有失准头,砸出去的铜板能竖着栽进泥土半截深。在冬天玩斗铜板最能生暖,因为要使大力。这种游戏又最能锻炼臂力——我在县城读高中时,体育课投手榴弹最远的都是农村男生,这跟他们小时候玩斗铜板大概是不无关系的。
斗铜板女孩子是不玩的,一来因为力气小,二来因为游戏“太残忍”。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场面。胜者劈砸对方铜板时或喜笑颜开,或凶神恶煞,好像地上躺着的不是铜板,而是国民党反动派或日本鬼子或“地、富、反、坏、右”这样的阶级敌人,必狠揍之而后快;输者面容沮丧,目光紧盯自己铜板,期望对方力气不逮或有失准头,听到砸中的“叮”响时甚至脸上肌肉抽搐,嘴里发出“咝”声,心疼得好像砸在自己身上。斗铜板使用“十文”是最吃亏的,因为它比“大清带铜”和“光绪元宝”轻薄,不经砸。常斗铜板的孩子铜板上满是密密的麻点,端的是伤痕累累!等上面的字和纹饰都看不清了,就拿去跟大人换。大人也不生气,往往照换。虽然这砸得不成样子的铜板已经失去了收藏价值,但攒着拿给铜匠化个饭铲粥勺和品相完好的铜板是一样的——农村人修补铜器的原料常常使用的就是铜板。
跳白果
白果,即银杏的果仁,炒熟了剥食,又香又糯。但小时候对于我们来说,白果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玩的。
玩的方法主要是——跳白果。
跳白果,先要做个“寸子”。所谓“寸子”,就是用稻草或麦秆比着墙砖掐成的尺,长短在伙伴间商定,三砖到五砖不等。
有了“寸子”,大家把白果夹在两脚之间分散地跳出去,然后视各自所占地形的优劣夹着果跳着接近或躲避同伴。待哪位伙伴的果进入了你最有效的进攻圈子,你便把果跳向对方——力争最接近,如果两只果在“寸子”量得到的范围内,那你就把对方的果“吃”(即赢。输者可以用另外的果来赔)过来了。如果“寸子”够不到,那就等于羊送虎口。
所以,跳白果也就是赌白果。其实孩子们的很多游戏就是赌博,就是模拟的战争,这时的玩具就是赌具或者武器。游戏的过程必须全神贯注,斗智斗勇斗技术——有时候更要斗玩具的“技术含量”。
跳白果不能使用肥滚滚的新果,骨碌碌的无法把握停止位置,所以得用摇起来“喀喀”响的陈果,不善滚,容易停。有一种没有发育得好的果子,扁削得像粒瓜子,却是跳白果的极品,几乎跳到哪停到哪,在五十度的坡度上都能停住,我们叫它“巴瘪子”。所以我们看到挑货郎来了冲上去买白果时,多少双小手争着在果子里翻找,如果谁有幸翻到一个“巴瘪子”,那简直像捡到了金子!
挑货郎当然知道孩子买白果是用来玩的,所以总是把果子染成红绿蓝紫各种颜色,放在玻璃盖子的方格里,更加吸引孩子购买。一分钱两个或三个。我小时候诨名“瘦猴子”,身轻如燕,跳起白果来机智准确,总是能赢很多。我跟村里开代销店的二伯死磨硬缠讨来一只散装雪花膏的玻璃罐子,把赢来的白果装进去。没事的时候我就欣赏里面拥挤的花花绿绿,或把手伸进去抓出哗啦啦的好听声响,实在是无比享受。
经常跳白果的孩子腿部弹跳力强,我读初一时才十二岁,跳远就能跳四米九,跟我擅跳白果不无关系。跳白果有种特殊的进攻方法,就是夹着果直接朝对方目标撞去,两果相撞则“吃”对方,撞不上自己的果因为蹦出去老远也可保证安全。我现在仍记得,我把白果稳稳夹在双脚之间,人果合一,像枚精准的巡航导弹腾空而起,射中对方时的快感简直让人心悸,妙不可言。
打弹子
弹子,即玻璃球儿,分花弹和净弹两种。花弹是在弹子里面嵌入各种颜色和形状的图案,有像树叶的,有像弯月的,有像桔瓣的,迎着太阳一照,七彩缤纷,炫人眼目;净弹刚是不嵌图案的纯色,有绿的,白的,蓝的,看上去水汪汪的,因此孩子们又叫它“水球儿”。
打弹子似乎是男孩子的专利,极少有女孩加入其中,因为太“惹脏”。游戏时需单膝跪地,一手撑地,另一只手背贴地,手心朝上,用拇指和食指掐住弹子,连挤带拔把弹子射出去。有的穿开裤裆的小朋友甚至全身趴在地上,屁股撅到天上,小卵子都撂在外头了,玩得聚精会神,全然不在乎“走光”。一场比赛下来,人往往也成了灰球、泥球儿了。
打弹子的方法是用削铅笔的小刀在泥地上挖个酒盅样的小洞,称之为“府”,参加比赛的孩子们从两三米之外的一条划线往“府”里弹球。就像打高尔夫球一样,一次进不了“府”可以两次、三次……最先进“府”的孩子就成了“王”,占着“府”把别人靠近的弹子打开去,但终有失手不准的时候,只得和进“府”的伙伴并列为王,一起捍卫王座。直到最后一个孩子焦头烂额地终于进了“府”,一场比赛才宣告结束。打弹子的游戏类似于占领山头和捍卫阵地的战斗,非常激烈而刺激。
既然打弹子是场“战斗”,武器的损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打对方弹子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地滚球”,让弹子在地上滚动中击中对方,另一种是“悬空球”,用一只手托住另一只手,从高处射向对方,这难度很大,非得有高超的技术(眼力+角度+手劲)才能达到,两球相击时发出清脆的响声,真是惊心动魄。经常挨击的弹子麻坑点点,还有豁掉一块的,比赛时这样的弹子往往就不允许参加,否则手上是好弹子的人就觉得吃亏了。
六七十年代,孩子们更新弹子不是件容易的事。买一只弹子两分钱,但两分钱就可以买一包火柴或者一支不带橡皮头的普通铅笔了。大人们囊中羞涩,掏钱并不爽气。孩子却有办法。胆大的从家里鸡窝里摸只鸡蛋到供销社可以换得六分钱,节俭的从口中省出一只烧饼钱——五分,就可以改善装备了。至于那些胆子既小连节俭都无门的孩子,只好用烂泥做成泥丸晒干,或者采下一种叫“洋楝树”的果子,权当替代了,却也能玩得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