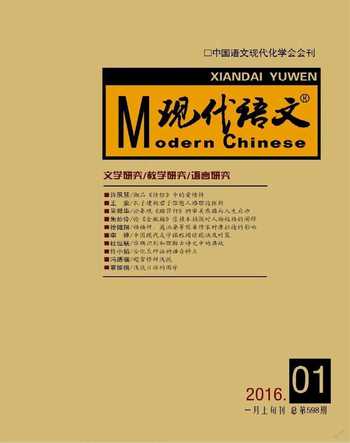是传记还是小说?
摘 要:《草泽英雄传——施耐庵传》中明确提出:《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是以历史上的张士诚起义为原型的,旨在赞颂张士诚起义的正义性。该书作者浦玉生先生以地理和人物形象为佐证,得出施耐庵把张士诚的农民起义隐晦曲折地写入《水浒传》中的结论。本文运用可靠的文献资料,对作者的上述佐证逐一加以考证,最终得出:作者的论述是牵强附会的。而所谓以张士诚为原型的说法是对历史上本就存在的宋江起义的故意抹杀。
关键词:宋江起义 张士诚起义 地理 人物形象 原型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国家级文化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旨在形象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这套丛书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现在首批十部作品已正式问世,而浦玉生先生著的《草泽英雄传——施耐庵传》一书,作为其中之一也已由作家出版社于2014年1月正式出版了。
展读此书,扉页上由丛书编委会所作的出版说明如是强调:该套丛书旨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系统和本正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文化成就”。作为一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其“创作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坦率地说,承担这样一个国家级的写作项目,需要承担的责任与风险是与得到的荣耀与信任一样多的。更何况此书的写作对象——传主施耐庵,由于距今年代颇久,学界对其生平籍贯履历种种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就在客观上增加了此书的写作难度。因为本着“主体创作的庄严性”,传记文学必须具备“文本内涵的学理性”,也就是“科学理性”。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标准便是“个人生平”的展现了。[1]
关于“个人生平”,英国的约翰· 德莱顿在1683年第一次使用“传记”时这样定义说:传记是“特定的人的生平的历史”。[2]1986年出版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给“传记文学”的定义是:“力图以文字重现某个人——或者是作者本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生平”。20世纪初《牛津词典》的定义是:“作为文学分支的个别人的生平的历史”。还有《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的定义是:“传记是在同社会现实、文化和时代的日常生活的联系中重造一个人生平历史的作品。”[3]
所以,传记文学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体现传主的“个人”与“生平”。但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传记文学的作者该如何体现写作对象的“个人”与“生平”呢?不妨援引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一段话来理解这个问题:“史家追述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4]这段话颇为精到地概括了历史文学中的形象化手法,与现代纪实文学的创作实践也颇为吻合。由此,不难得出,纪实文学应该“忠实地复现事实以实现纪实文学的认识价值,是纪实文学的生命所在”[5]。
所以,对于这部《施耐庵传》的写作,当然就要求作者能够完整、准确、客观地将传主个人生活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并力求做到“文与史”“诗与真”的统一。而倘若能将施耐庵生平经历尤其是其写作完成《水浒传》的整个过程加以准确、客观而又形象化、文学化的呈现,那么这无疑就是一部值得尊敬与传诵的作品了。但是,总揽全书后,不得不说感到非常遗憾。阅读中产生的最强烈的感觉居然是:这部位列国家级文化工程的著作,究竟是一部小说作品还是名人传记?恍惚之间,不得不以书中的一些疑问为线索,查阅相关的资料,以解决内心的困惑,并由此完成作为阅读者的“二度创作”。
作为传主的施耐庵,其一生最值得称颂的作为便是加工完成了这部流芳百世的小说巨著《水浒传》了。因此,浦玉生先生的《草泽英雄传——施耐庵传》,也是将描述的重点放在了这个关节点上。作者不仅写了施耐庵的少年老成、官场岁月、书会才人、军事生涯等几个人生阶段,为其著书立说进行铺垫,而且写到著书的行为对其以后人生乃至后世的重大影响,更写到其如何创作的具体情形,力求还原历史上的真实的施耐庵。但真实的情况是,关于施耐庵的创作《水浒传》的具体因由及其它种种,作者浦玉生先生以大胆的假设与主观的臆想为主导,终至于写出了一部虚构色彩浓郁而纪实成分不足的号称“历史文化名人传”的《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
就重点来看作者认定的施耐庵笔下的“水浒原型”吧。作者认为,《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便是以历史上的张士诚起义为原型的,此书旨在赞颂张士诚起义的正义性:“一部《水浒传》纯属是以宋江起义说事,而以张士诚起义为原型和背景的。”[6]作者的论据主要有二。其一是地理的佐证。
作者认为,关于宛子城、金沙滩、石碣村、蓼儿洼和鸭嘴滩,“施耐庵运用这些地名是与张士诚有关,与江淮地域有关,与施耐庵的生活环境有关。”[7]比如金沙滩。作者认为:“施耐庵在《水浒传》第十一回中写道:‘小喽啰把船摇开,望泊子里去奔金沙滩来。这泊子,乃是洪泽湖的泊子原型,这金沙滩在阜宁县一带有原型……”[8]在进行一番论证后,作者得出:“由此可见,施耐庵将江淮之间的地名风物,融入了《水浒传》。江淮地区包括洪泽湖一带的金沙滩、鸭嘴滩、蓼儿洼等搬移到梁山泊来……而这一带正是张士诚起义勃兴时期的行政版图。”[9]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洪泽湖真的就是梁山泊的原型吗?我们在《水浒传》中找到多处关于水泊梁山的描写:“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第八回)“自这南方有个去处,地名唤作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第三十五回)“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第七十八回)然而,小说中关于梁山泊的这些主要特征的描写,我们竟然能在元代早期杂剧家高文秀的作品《黑旋风双献头》中,找到类似的语句:“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被称为“小汉卿”的高文秀在《黑旋风双献头》这个水浒戏中关于水泊梁山的描写,只能让我们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它被后世的《水浒传》给借鉴了!但高文秀又何以对梁山水泊如此了解呢?根据钟嗣成《录鬼簿》中的记载,原来已归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之列的杂剧作家高文秀乃“东平府学员”。东平府在哪呢?就在梁山泊的边上。如此说来,高文秀很有可能是根据自己家乡边上的梁山泊的地理特征,创造出了作品中的八百里梁山泊。而明显晚于《黑旋风双献头》的《水浒传》,其中关于梁山泊的地理风貌的描写,就显然是借鉴了高文秀剧作中的相关描写。因此,梁山水泊的原型很可能就是真正的梁山泊。作者关于洪泽湖即梁山原型的说法明显就是牵强附会了。
其二是人物形象的佐证。对于《水浒传》中的“张”姓和“潘”姓人物的设置与表现,作者认为其中蕴含了施耐庵极大的深意。作者判断: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把张士诚农民起义隐晦曲折地写入书中,书中曾多次出现‘小人姓张‘张大哥等张姓细节。”[10]作者进而分析:“为何《水浒传》中至少七处写了张姓,而没有写其他李、王、曹等姓,说明施耐庵是有意识地将张士诚隐晦曲折地写入《水浒传》中。”[11]还有“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作者认为“隐士施耐庵有感于吴王张士诚的农民起义,这里的洪太尉与张天师都是影射张士诚的:一是用了张士诚投降元朝时的官职,二是用张士诚的姓。”[12]作者认为,张姓人物的出现就一定意味着作者对同样姓张的张士诚的曲笔表现与含蓄赞美。对于“张”这样一个大姓,在我们汉民族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本来就高,小说中屡屡出现本来也不足为奇。但作者这番认为,并将之作为一个反复提及的重要论据,就有些惹人深思了。小说本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生活中高频率出现的姓氏在小说中也高频率的出现,这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加之作为一部立足现实、强调反抗、争取自由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作家施耐庵在塑造人物时必然会高明地运用形象化、典型化的创作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而绝非简单化地张贴姓氏标签。因为典型化、形象化的手法应该是体现在人物性格、精神气质与理想抱负的塑造上,而非仅仅表现在一个“张”姓上,因为这实在是太皮毛的一种做法了。更何况封建社会文网严密。倘若施耐庵真的想为张士诚鸣不平,那么就更要以曲笔委婉道来,而绝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地一“张”到底了。至于以“太尉”的官职来影射张士诚的说法,与姓氏的影射原属一路。作者显然将封建时代的文人为规避文祸所采取的策略过于简单化了。那种“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隐曲表达,一定是文人保全自身的更高明的文字表达,也是更贴近实际情况的做法。
还有一个“潘”姓。作者认为:“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及其兄弟潘元明,在起义事业的关键时刻背叛了张士诚”,而“施耐庵是站在同情张士诚起义的立场上写《水浒传》的,所以在《水浒传》第二十五、四十五回中,写潘金莲、潘巧云两个淫妇的结局都是被‘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何以对两个潘氏女人如此狠毒?乃施耐庵影射潘氏二兄弟也。”[13]在论及水浒原型时,作者再次提及:“《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和第四十六回中写到两个淫妇,无巧不巧,都姓潘。” “在农耕社会,‘万恶淫为首,施耐庵笔下的两个淫妇,都是不得好死的。……都是剖腹剜心,掏出五脏,痛快淋漓之至。”[14]再次强调了:“施耐庵笔伐二潘在现实生活中是有所指的:直指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和其兄潘元明二人……”[15]倘若从艺术创作的手法来看,作家在笔下人物身上将自己十分喜爱或厌恶的对象投射其中,或加以赞美或加以鞭挞,确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问题是,作为原型的潘氏兄弟必须先行存在,尔后才能有作家的人物影射。也就是得先有潘氏兄弟投降的恶行,施耐庵才能在作品中借淫妇形象进行影射并加以鞭挞。倘若还未有潘氏兄弟的投降,而作家已经完成了淫妇的塑造,那么又何谈影射与批判呢?事实不幸确是如此。
根据《二十五史》之《明史》的记载,至正二十六年“辛卯,李文忠下余杭,潘元明降,旁郡悉下。”(卷1本纪第一)“潘元明以平章守杭州降,仍为行省平章,与伯升俱岁食禄七百五十石,不治事。云南平,以元明署布政司事,卒官。”(卷123列传第十一)“遂趋杭州,守将潘元明亦降,整军入。”(卷126列传第十四)可见,潘元明的投降朱元璋背叛张士诚,应该是在至正二十六年,即公元1366年。而潘元绍呢?《明史》有如下记载: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士诚复自立为吴王……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绍为腹心,左丞徐义、李伯升、吕珍为爪牙,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主谋议,元学士陈基、右丞饶介典文章。”(卷123列传第十一)“其将徐志坚败于东迁,潘元绍败于乌镇,升山水陆寨皆破,旧馆援绝,五太子、硃暹、吕珍皆降。”(卷123列传第十一)“二十七年九月……大将军达数遣李伯升、潘元绍等谕意,士诚瞑目不答。”(卷123列传第十一)可见,作为张士诚女婿及心腹的潘元绍,在兵败后于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终于做了敌方,即朱元璋的说客,去劝降张士诚,遭到了张士诚的拒绝。倘若以此来看,潘元绍的降明,比较明确的时间应该在至正二十七年,即公元1367年9月。
那么《水浒传》中的两个姓潘的淫妇,又是在什么时间塑造完成的呢?根据浦玉生先生《施耐庵传》中的《施耐庵年表》中的记述,在至正十三年癸巳,即1353年五十八岁时,施耐庵“《江湖豪客传》(《水浒传》)正写到第四十五回”。[16]其中关于淫妇潘金莲的命运已在第25回设置完成:“那妇人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胳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水浒传》第25回《偷骨殖何九送葬 供人头武二设祭》)潘巧云的结局也已尘埃落定:“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水浒传》第45回《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庄》)如此看来,两大潘姓淫妇的形象已在1353年基本塑造完成。再过13或14年,即1366或1367年,才有历史上的潘元明、潘元绍的叛变投敌。原型产生在后,虚构形象反而在前,这在逻辑上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因此,作者关于人物形象的佐证也是牵强附会、难以令人信服的。
以上述两点,大致可以判断,浦玉生先生的这部《施耐庵传》有些地方实在是写得有些牵强甚至是离谱的。这种艺术的虚构与加工根本背离了纪实文学的创作宗旨。尽管作为纪实文学,本允许有一定的虚构性,但毕竟还是要以真人真事为基础,虚构必须是有节制的。此外,还须论及的是浦玉生先生笔端的“原型”一词。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原型,特指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事实上,原型(archetype)又可称之为“原始模型”或“民间雏型”。这个词出自希腊文“archetypos”。“arche”本意是“最初的”“原始的”,而“typos”意为形式。[17]浦先生将“原型”的概念引入《施耐庵传》中,本意非常明显,是意在说明与强调:施耐庵在创作《水浒传》的过程中,尽管已经掌握了大量的史料和民间传说故事,但在具体的写作中,必然还是会有机借鉴自己所熟悉的风光景色和风土人情。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这是小说家创作人物时的一种典型化手法,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被借鉴的风光地貌人物故事并不能被一律称之为“原型”。根据“原型”的定义,只有那些“最初的”“原始的”形式,才能算作小说的原型。而《水浒传》中宋江的人物事迹,在宋李植的《十朝纲要》卷十八,宋张守的《毗陵集》卷十三,宋汪应辰的《文定集》卷二十三,南宋方勺的《泊宅编》卷五,宋李焘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八,《桂林方氏宗谱·忠义彦通方公传》,《宋史》卷二十二和南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百零八等诸多典籍中的记载都有力证实了:北宋历史上那位曾经啸聚山林、战斗力极强而最终投降宋朝的山东好汉宋江,正是《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原型。而小说中的梁山水泊,也是以高文秀杂剧中的那个水泊梁山为据创作的。而高文秀笔端的梁山水泊,又是以其家乡东平府边的水泊梁山为据创作的。因此,历史上真实存在于山东境内的水泊梁山就是《水浒传》中的梁山原型。只是由于时间的流逝、地貌的变化,今日的梁山已不复当年水波浩荡的景象。尽管沧海桑田、造化弄人,但谁又能因此质疑梁山的真实存在呢?因此,《水浒传》中的人物与地理,实际早有其各自的原型。以此观之,浦玉生先生的所谓“以张士诚起义为原型和背景”,反映了“张士诚起义勃兴时期的行政版图”的说法委实是有些牵强附会了。
关于浦玉生先生的这本《草泽英雄传——施耐庵传》,其中的错讹之处本文提到的仅为一二。至于施耐庵的生卒年、生平事迹等等,此书还颇有值得斟酌与推敲之处……
注释:
[1]章罗生:《纪实文学的门户清理与分类标准》,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
[2]奥尔多·H·邓恩:《英国传记》,邓特父子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77页。转引自章罗生:《纪实文学的门户清理与分类标准》,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
[3]转引自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4]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6月版,第1册,第166页。
[5]孙春旻:《纪实文学:寻找真实的坐标》,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6]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页。
[7]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页。
[8]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182页。
[9]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页。
[10]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11]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12]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1页。
[13]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14]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
[15]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
[16]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290页。
[17]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俞世芬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11121)